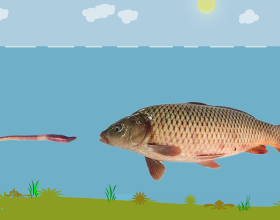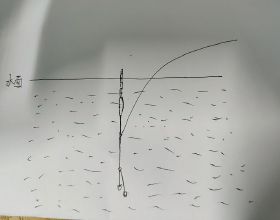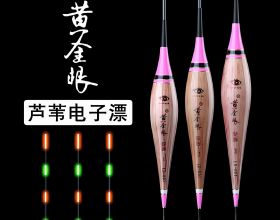民國二十年,天津《天風報》刊登出這麼一檔子事兒,說起來可真是可氣又可笑。
有位洋行買辦之家的大少爺,名叫常雙金,身為富家子弟,尤為講求派頭,整日裡穿金戴銀,吃吃喝喝,玩玩樂樂,好不逍遙自在。天津衛一般用兩個字稱呼這種貨色——孽障。
有一天,孽障常大少到了北門外的一家落子館聽大鼓書,臺上的小丫頭唱得帶勁,臺下的常大少哼得起勁,不是內行人,不會來捧場,常大少在大鼓書方面,稱得上半個行家。
就在常大少聽完了一段,扯脖子叫好,玩命拍巴掌的當兒,不知打哪兒飛過來一方香帕,也不知為嘛那麼寸,正落在常大少的臉上。這方香帕不一般,桃紅緞子面兒,繞圈帶金邊兒,一面繡鴛鴦,一面繡蝴蝶。嗅一嗅,香氣撲鼻;聞一聞,清神醒腦。一個字——好;再加一個字——妙!
好歸好,妙歸妙,這方香帕究竟是誰家之物?常大少來了興致,定要尋個真章。於是晃著賽麻桿兒的細脖子朝四外亂踅摸。突然雙眼定格——難不成是她!
抬望眼,細打量,二樓有位美嬌娘,正跟他對眼兒哩。嘿呦喂,“又鼓拎又丟秋”,她怎麼長得那麼好看,真真兒賽西施,似貂蟬,猶如嫦娥月中仙。如此一個尤物,可把個常大少爺看丟了魂兒。
樓上的美嬌娘對他嫣然一笑,朝他招了招手,那意思是請他到樓上說話。常大少兩腳好賽騰雲駕霧,飄飄然都不知道自兒個怎麼上去的。
先行禮,後寒暄,再把香帕交還。美嬌娘雙腮泛紅,眼含秋波,舉止儘管扭捏,卻大有投懷送抱之勢。雖不言語,卻也是無聲勝有聲。常大少久在風月場中廝混,自恃閱人無數,怎看不出她的心思。既然神女有心,襄王又豈能無意。
美嬌娘起身離坐,擺動腰肢,下樓而去。常大少隨之而出,喊過來一輛膠皮(黃包車),緊跟美嬌娘乘坐的膠皮,一前一後來至一座二層洋樓前。美嬌娘開啟門鎖,推門而入,又扭回頭對著常大少含羞一笑。
常大少會意,立即跟著到了裡面。雙雙上了二樓,進入臥房,正待寬衣解帶。突然,樓下傳來嘈雜的腳步聲,似乎有不少人闖了進來。
美嬌娘嚇得面如土色,慌忙對常大少說:“壞事了,我爺們兒回來了!”
話音剛落,就見一個身材魁梧高大,身穿戎裝的紅臉大漢出現在門口。紅臉大漢朝屋裡打量了幾眼,瞪圓了眼珠子厲聲喝問:“你是誰,為啥跑到俺家來了!”聽口音,這位軍爺是山東人。
崴泥了,讓人家爺們兒堵屋裡了。常大少“麻爪”了,好似磕了煙油子的蠍虎子,光知道打哆嗦,卻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這時候,四個頭戴軍帽,身穿軍服,打著綁腿,腰挎盒子炮的軍人氣勢洶洶地上了樓。看他們的打扮,就知道他們是紅臉大漢手下的馬弁。
紅臉大漢猛把大手一揮,叫一聲:“把這小子給俺拉出去斃了!”
美嬌娘趕緊為常大少求情,結果捱了紅臉大漢一腳,只能抱著雙肩瑟縮在一旁,再不敢吱聲。常大少跪地求饒,紅臉大漢並不買賬,四個馬弁如狼似虎,連拖帶拽地將常大少弄到樓下,將常大少一身名貴穿戴全都扒了下來,只給他留一條短褲遮羞。
就在這時,又有一位長官模樣的軍爺從外面走了進來,立即喝止住馬弁,問清楚原因之後,認為既然沒有形成事實,那也就不必要人性命。雖然死罪可免,但活罪難饒,留下他的財物作為懲戒。
常大少死中得活,千恩萬謝一番,只穿著大褲衩跑回家中。粗略一算,被扣下的鑽石戒指、金錶、扳指等不下數千銀元。他老爹問他怎麼這幅狼狽德行?他不說實話,謊稱遇到劫匪。他老爹不信,大白天的哪來的劫匪,非要他說出實話不可。
常大少畏懼老爹的威嚴,只得實話實話。老爹一聽,猛拍桌案,大罵兒子糊塗,那些人一準兒是拆白黨,設個套誠心讓傻小子往裡面鑽。於是趕緊給白帽衙門打去電話,要為兒子出口惡氣。結果等到白帽衙門的軍警到了之後,拆白黨早就跑沒影了。
這一招在“蜂麻燕雀”的招數之中,稱之為“美人局”,先用年輕漂亮的女子為餌,引誘浮浪子弟上鉤,然後再出現一幫兇神惡煞乘機敲詐錢物。招數雖然簡單,卻屢試不爽,如今的“仙人跳”,也是這麼一個套路。但話又說回來,騙子縱然可惡,可若是受騙者不貪心,又怎會吃虧上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