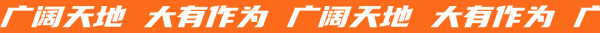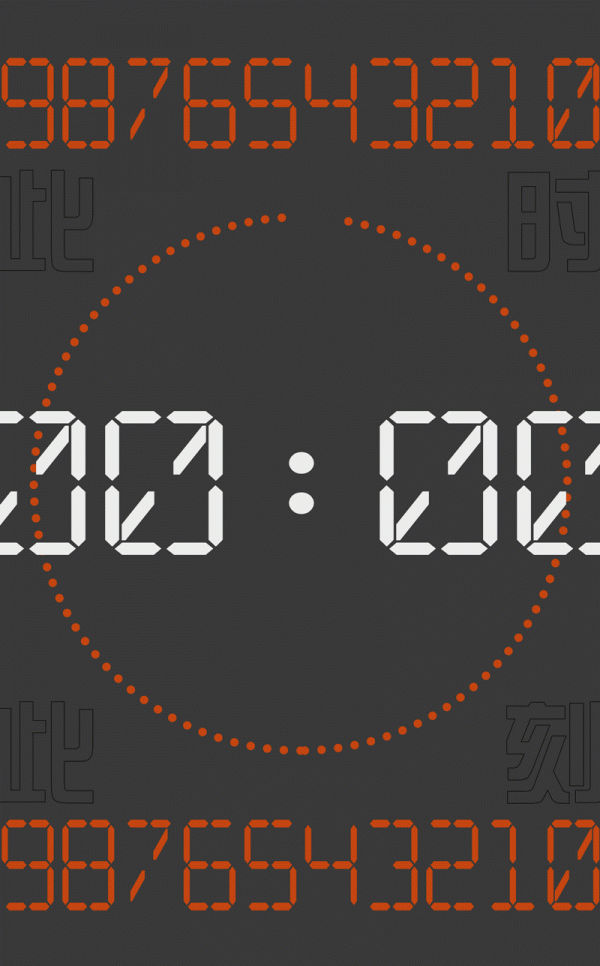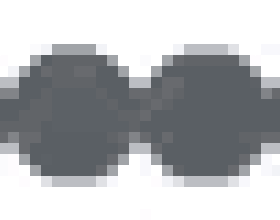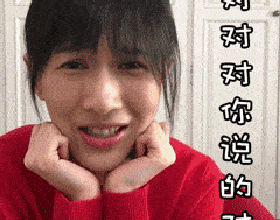西西比·買買提
1983年,羅大佑出了一首歌叫《未來的主人翁》,那年他29歲,離30歲還有1歲。
他在歌詞裡寫道:“每一個今天來到世界的嬰孩,張大了眼睛摸索著一個真心的關懷。”
我猜羅大佑有不少話想借這首歌說出來,關於他自己,關於那座島。
更關於一代人。
聽這張專輯長大的孩子們,不少也像那年的羅大佑一樣,即將、剛剛或者已經進入了而立之年,
在像歌中所唱的那樣成為了“電腦兒童”的同時,一些曾經的“未來的主人翁”們,在一腳踏進社會之後,依然做不了自己生活的“主人翁”。

中國人對年齡有一種超越其他任何民族的敏感,這是打孔老夫子那會兒就留下來的傳統。
三十而立,本來是孔子拿來講述自己心路歷程的話,卻被後世當成了一種準則。
雖然人生不是豬肉,不能一刀一刀按斤切,但是三十歲的確是一個人生理與心理成熟的關鍵節點,年齡的背後是各種暗含的社會期待。
一個以“你都是三十來歲的人了”為開頭的句子,後半段註定是對一個人的批評之語。
三十而立,立起來的人各有各的生活,立不起來的人卻有著相似的“困境”。
首要的問題是錢。
經濟不獨立則人格不獨立,連韋小寶都知道“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的道理。
但是不少小丈夫不知道是真的不懂,還是選擇性忽視,直接躺平啃老。
可上一代人靠著高儲蓄、低消費,省吃儉用,受苦受累積攢下來的家底兒,在這全球大放水的時代已經變得很薄很薄。
如果這個小丈夫恰巧是個戒賭吧老哥,那來自爹媽的錢不僅不能支撐他可憐的人格,他還會把爹媽一起拖進災難的深淵。
在經濟獨立上選擇棄權的人雖然是少數,但是卻有一大批人依然在商業社會的門口躊躇不前。
這就是依然抱著做題家思維的人。
當然做題家並不是一個貶義詞,因為從理論上來說,幾乎每個人曾經都是做題家。
做題家們未必如外界想象得那樣遲鈍,他們其實早已經窺測到了外面世界的殘酷,而沒有什麼比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完成一份有標準答案的試卷更簡單的事兒了。
相較於投身變幻莫測的市場,他們更偏愛“做題—聽老師的話—上好大學—找好工作”的直線型路徑。
前有高考十二年的吳善柳,後有上高十的唐尚珺,看似極端的現代版“范進中舉”背後,實則是一個群體心態的縮影。

當然,更不用說每年都拜倒在各路考研名師門下,準備二戰、三戰的海量大學生。這些對未來發憷的年輕人,還沒到而立之年,在心態上就已經無限接近焦灼的中年人。

如果僥倖畢業之後能擁有一份能維持自己生存的工作,他們似乎在經濟上就做到了獨立。可一旦需要靠父母湊的首付買房,高槓杆之下,看似獨立的人格立刻就要大打折扣。
即使自己晉升為人父人母,也不意味著自動成熟。帶孩子的重任往往又要分出大半交給上一輩人,然後一家子困在“有了兒子當兒子,有了孫子當孫子”的怪圈中,無法自拔。
此時人近中年,猛然回顧自己的青年時代,痛感當年的路走得還不夠筆直,而自己的孩子最好從孃胎裡就拿尺子把這條直線畫準,然後陷入瘋狂雞娃的程式裡,反覆迴圈。與中世紀買贖罪券的歐洲人有異曲同工之妙。
待到中年一過,發現身為985的爹媽居然培養不出211的孩子,於是對孟德爾的豌豆深表懷疑,爹媽看不上孩子,孩子瞧不起爹媽,相看兩厭。
這是三十不立者們的後傳,也是做題家們的史前史,彷彿今天的雲模仿昨天的雲。


一個人人格不健全這是心理醫生應該解決的問題,但一群人人格不健全則是一個時代的結構性問題。
現在市面上有個流行的觀點,認為八零後和九零初是最悲哀的一代。
悲哀不光是因為他們三十歲前大把時光都消耗在了學校,而是他們的青少年時期重疊了一個浪漫主義盛行的時代。
早些年的文藝作品就是最好的證明。
那時候沒人愛聊階級,少有人關心男女對立,《醒著的年代》放那會兒熱度肯定也不高。
那個時候大家最喜歡的是《泰坦尼克號》,是《拯救大兵瑞恩》,是浪漫的人性。
是《大話西遊》,是《情書》,是《愛在黎明破曉前》,是愛情大過天,愛情能忽略物質,愛情能夠超越階級。結婚沒房子是可以的,而且是值得歌頌的,討論門當戶對、彩禮等問題則是可鄙的。
可當這撥年輕人長大成人踏進社會,卻發現自己彷彿經歷了時空躍遷,世界的時間線好像錯了,怎麼一下就跳到《魷魚遊戲》的時代了呢?
其實浪漫時代從來就是個幻覺,每一代人也都會抱怨自己沒有趕上一個好時代。

有人覺得從前的日子是good old time,只因為那是個世界經濟的黃金時代,一個熱得發燙的時代。
所以佟大為們才能豎著polo衫領子大談理想,和女朋友發發牢騷;貧嘴張大民們才能過上“仨飽一個倒”的幸福生活。
就是俗話說的——錢好賺。
大水漫灌的時代,那些有幸提前走進社會的年輕人誤以為自己所選擇的,便是通向歌舞昇平的康莊大道,按部就班、追求穩定是每一個普通人應當相信的生活真理。
但當大潮退去,留給後來者的將時代紅利套現的機會越來越稀薄,人們終於意識到有些遊戲模式註定玩不下去了。
而死守著上一輪遊戲規則的人,看似還能衣著光鮮地在寫字樓中做一個精緻的白領,但是扒掉衣服卻露出來一群“在格子間裡深耕密植的農民”。
他們自己既是耕地的鋤頭、耙子,也是肥料,簡單的勤勞刻苦,很難再讓這塊地上創造更高的價值。
這很符合內卷最原教旨主義的定義。

當增長降低,而淘汰率大幅提高的時候,不願意跳出來的人自然會把這一切當成一場魷魚遊戲。
生存主義至上的表現自然就是求安穩,“當伏地魔,苟一苟就能活到決賽圈”是典型心態。
但是當所有人都匍匐前進,毒圈卻一刻不停地縮小時,掙扎之中總想抓住幾根救命稻草。
寄生在父母一代人身上是救命稻草,但是看起來既不體面也不道德。
財務自由是看得見、抓不住的稻草,年輕的玩家們精力、知識,視野有限,發財夢的泡泡在眼花繚亂的資產漲跌中轉瞬即滅。
“系統”可能也會被當成稻草,殊不知考公考編是窄門,而在系統中待久了還會生出幻覺,誤以為自己是系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手握微薄的資產,剛剛解決生理與安全需求的年輕人,面對遊戲規則的劇變,在心理層面上很難不出問題。
憤怒、頹廢、迷惘都是常見症狀,病急,難免亂投醫。
藥方子有時候是偶像,有時候是雞湯。
時不時再把×博、×瓣當作情緒的垃圾桶,發洩一番。
偶爾來一針“階級躍遷”,看似是興奮劑,實則是安慰劑,也是自我折磨的毒藥。
最後在遊戲、短影片、網購、奶茶與重口味外賣中收穫最終的平靜,就像工地大哥們依靠手中的廉價香菸與散裝白酒安撫自己疲勞的身軀。
第二天太陽照常升起,遊戲繼續。
虛弱的倖存者被舊規則所吸引,成為忠實的擁躉,被淘汰的人則是這個不斷膨脹的“遊戲宇宙”中的一點點增熵。
關於人群的性格與時代之間的關係,有人做過一張有趣的圖。

艱難的時代造就狠人,狠人創造美好時代,美好時代養出衰人,衰人搞出下一個艱難時代,週而復始,猶如無間輪迴。
乍一看確實像那麼回事兒。
時代的大問題當然可以交給時間來解決,但宏大敘事對個人而言往往意義甚微,一個人有限的生命也不足以對抗時代變幻的漫長週期,就如凱恩斯的名言:“從長期來看,我們都是要死的。”
重要的是別讓自己沉淪。
用王爾德的話講就是:“我們都生活在陰溝裡,但總有人仰望星空。”
用馬大帥的話講就是:
大街上的雜音和負面情緒太多,沉溺其中過度解讀往往如同墜入糞坑。
滿腦子book smart的“思想家”會告訴你,要反思,要總結。
富有street smart的“行動家”則會告訴你:掉進糞坑裡的第一件事是趕緊爬出來,而不是在糞湯裡一邊咀嚼一邊思考人生。
失掉勇氣的年輕人需要的不是一個寄託幻想的烏托邦,這隻會讓人變成卡夫卡式的甲蟲。
甲蟲式的青年不可能等來炬火,自願成為籌碼與工具的人也不是這個時代的主人翁。
在大風大浪裡學游泳註定是一件危險又痛苦的事兒,但一個人只有“脫離了母親的裙兜和父親的指令”,投身大潮才能真正獲得對舊時代說“不”的勇氣和能力。
那學會游泳之後呢?
是廣闊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