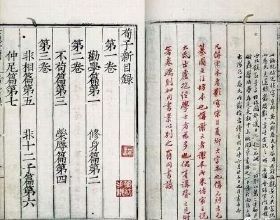“茶籽”是湘南一帶農村對油茶樹結的果實的土叫法,油茶樹是一種經濟林,屬於常綠小喬木,枝葉繁盛。常於夏季掛果,經秋季成熟,每年的“寒露”或“霜降”時節為摘茶籽的最佳時機。
那時候,我們村裡只有幾個生產隊有茶山,每到茶樹結果,青綠色的茶籽壓滿枝頭時,隊長就會組織各家各戶開會,決定每家出一個男勞力守山,以防止鄰近生產隊的村民偷摘茶籽。守山是每隔一段距離,安排一個人守住上山的入口,並且要不停地來回走動。父輩們照例是很負責的,他們仔細巡查著可能進山的每一條入口。我們小孩子則跟在大人後面,心裡升起一股強烈的自豪感,盼望著能抓到一兩個進山的“賊”,給沉悶而寧靜的氣氛增添幾分熱鬧的氣息,玩累了,就露天席地而睡,任由螞蟻和其他不知名的小蟲子在身上爬。
守山約莫一個月後,隊長莊嚴宣佈明天開始摘茶籽,於是,各家各戶就如同盛大節日般嚴陣以待,男女老少只要能動的都會上山摘茶籽,連讀書的小孩也會向老師請假,老師一般也不會阻攔。然而,出嫁了的女兒是不允許參加的,因為嫁出去了就不可以參與分茶籽了,村民們也相互盯著彼此已經嫁出去了的女兒,提防與孃家裡應外合偷茶籽,所以,那幾天,父母們會通知各家女兒不要回孃家,以免說不清楚。
當天晚上,早早地吃了“點心(方言,晚飯,一般都是中餐的剩飯菜)”就睡了,我們這些小孩由於興奮開始是睡不著的,然而睡著了沒多久,大概凌晨4點左右又被大人給叫醒吃早飯了,然後,全隊的人挑著籮筐,拿著編織袋或者提籃,打著火把浩浩蕩蕩地向山上進發,場面非常壯觀。到了山上,隊長一身令下,所有人就如同脫韁的野馬奔向成片的茶樹,往往是一家人佔領一顆或幾顆樹,別人是不能來摘的,否則,就可能引發矛盾或爭吵,甚至大打出手,因為,各家的摘茶籽量將直接影響到後面分到的多少。
中飯是在山上吃的,都是自家昨夜準備的乾糧,狼吞虎嚥的吃了一點後又忙於摘起來,一直到下午5點左右,所有人肩挑手提地把茶籽運回隊裡,稱重後集中堆放在保管室裡,一把大鎖鎖住了全隊人一天的收貨,第二天又開始重複。大概5天以後,山上的茶籽摘完了,小孩子就又回學校上課了,隊長宣佈“開山”,於是,早就守候多時的鄰隊村民和自家出嫁了的老少姑娘們便喜笑顏開地一窩蜂湧進山裡“淘寶”高枝上未摘盡的茶籽。
新摘的茶籽是不可以馬上就分的,必須經過半個月左右的堆積,這個過程叫做“漚果”,要等到青綠的果殼自然裂開就可以分給各家各戶了,隊裡會計根據各家人口的多少和摘茶籽的總量按照比例算出應分多少,然後大人就把自家的茶籽挑到禾坪晾曬,太陽越大越好。晚上,每一片晾曬的茶籽上都會睡著一個守茶籽的人。
幾天後,茶籽就可以選殼了,往往也是全家上陣,在一張大簸箕中間放著一盞煤油燈,全家人就圍著簸箕而坐,把果殼與烏黑的果仁分離,過程自然是及其單調而乏味的,於是,大人們就會把講了無數遍的故事再講一遍以吸引早就瞌睡得點頭如雞啄米的孩子們。
終於,選殼完成了,烏黑的果仁經過2天的暴曬就可以榨油了,早早地,大人們會做好一桌豐盛的飯菜款待榨油坊的師傅們,榨油是體力活,經過磨碎,蒸煮等幾道工序後,“富得流油”的茶籽粉末被包裹在金屬圈裡,整齊的碼放在榨油腔裡,一根一頭懸在房樑上的長長的木錘伴隨著師傅們的號子,有節奏地重重擊打著塞入一串包裹著蒸煮好的茶籽粉末的金屬圈旁的木楔,然後再一點一點的擠壓金屬圈,金黃透亮的茶油就冒著熱氣流入了油桶中。此時,大人們就露出了甜蜜的笑容,因為,在當時的鄉下,茶油可是上好的寶貝,不過,一般都是自家捨不得吃,除留下極少部分過年吃外,其餘都基本挑到集市上賣了貼補家用。
後來,村裡人都基本外出打工了,山也就沒人管了,再後來,山被賣給了一個果樹種植商,那些油茶樹都被砍了,換成了奈李等果樹,又過幾年,據說,果樹收成不好,種植商走了,現在,山也就荒了,漫山遍野,雜草橫生,連路都沒有了。
每次,在湘北工作的我回鄉下,經過那片山時,常常會駐足觀望,既是為了尋找童年的記憶,也是傷懷於我們祖祖輩輩曾經心心念唸的油茶樹,總覺得,雖然現在的生活質量提高了,但卻也離傳統越來越遠了,失去的就再也找不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