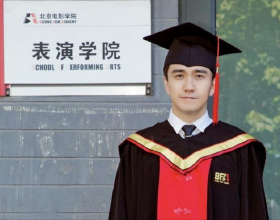冬季是煤炭銷售的旺季,這幾座山上大大小小分佈著七八個煤窯,來這裡運煤的卡車川流不息,在蜿蜒的山道上蛇一樣蠕動著。我們班新來了一個工人,父親認識他,叫酸明。個子又高又瘦,黝黑的臉上始終像是沒睡醒的樣子,整天眯眯瞪瞪的,和人一說話口水就拉的老長。
聽人說他的老家離這兒很遠,家裡沒什麼人,是個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主。他在這一帶下煤窯好幾年了,吊兒啷噹的不好好幹,要不是臨近過年了不好招人,窯上也不會用他。
沒幾天他和我混熟了,在我面前說話也不避諱了,開始口無遮攔,口水飛濺。他告訴我,現在他住在山那邊的一個小村子裡,給村裡的一個女人當“夥計”。女人也有男人,是個懦性子,三棍子也打不出個響屁的角色。而且他和那女人每天晚上都睡在一起,男人都不敢言,只要一開口便會遭到女人劈頭蓋臉的一頓臭罵,只能坐在房簷下大口大口地吸旱菸,彷彿要把所有的憤怒都化作那一股股的濃煙。
每天上班,他都會和我講述他的成就,但總也離不開那些荒誕汙穢的情節。他對我說那女的身子有多麼的軟和,爬在她肚子上有多麼的舒服。說著說著,口水已經溼透了半邊衣襟,說的我也有點蠢蠢欲動了。
在接下來的日子,我每天都在沉重的工作和酸明的汙言穢語中度過,沉重的工作我已經習慣了,汙言穢語成了疲憊的興奮劑。可怕的是這些汙言穢語已經侵入了我的身體,侵入了我的思想。有時候它們還會出現在夢中,一同出現的還有劉克軍的媳婦,嫵媚動人,我幸福極了……快樂極了……像是有什麼東西把我往裡面吸,我也使勁的往裡面鑽……突然間,身體陡地一顫,又彷彿跌入了萬丈深淵,我伸出手拼命地想要抓住什麼……夢醒了,我依然安好的躺在被窩裡,一切是那麼熟悉,只是感覺我好像尿炕了,手心裡滑溜溜的。
後來,這樣的夢做了好幾回,每次醒來,我都羞愧難當,像是一個沒臉見人的小偷。
再有幾天就過年了,煤窯上也準備放假,領工資那天,我見到了那個女人,是跟著酸明來的,短粗的身體將棉衣敞著,幾個熟人在和她時不時地開玩笑,她揚著佈滿黑斑的臉毫不示弱地向他們罵著,笑著。胸前的兩坨肥肉也在她的扭動下顫顫巍巍。我看到酸明把一疊鈔票交到她手裡的時候,她笑的那麼坦然,那麼幸福。
在那迷茫的年月裡,艱苦的條件下,淒涼的命運裡,跟他們講道德是多麼的可笑,多麼的蒼白。雖然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長久,但在當時認為他們是真的幸福的,是令人羨慕的。
很快,人們都陸續的撤走了,扛著行李,坐著卡車,山上又恢復了寧靜,只留下了一排排歪歪扭扭的窩棚和窩棚裡一堆堆破爛不堪的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