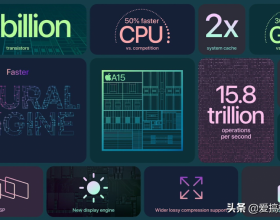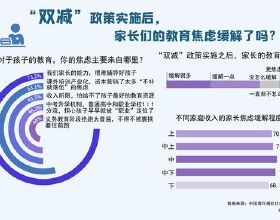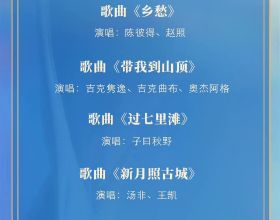那日,在縣城街道上購物,為圖方便,順便將車子停靠在一棟居民樓下的一層車庫前面,剛一熄火,一個身材短小面孔黝黑頭髮蓬亂的中年男子走了過來,他開啟位於我車子後方的車庫門,要將自己的摩托車騎出來。
我下車後在原地停了一會,尋思自己的車距離他車庫有好幾米,而且,車身一側還留出了一定寬度的通道,應該不會妨礙他通行。但不曾想,這個中年男子一邊發動摩托車,一邊因車子停在他的車庫前方而破口大罵,表情猙獰,話語刻薄。我正想上前爭論一番,但就在我與中年男子目光對視的一瞬,我在他的眼睛裡,讀到了特別的語言。
泛著血絲的眼睛,透出一種由來已久的兇狠,還夾雜顯而易見的憤怒,而且,分明是壓抑了許久而現在被一星火花點燃的那種。寫滿這樣語言的一雙眼,再搭配一頭亂髮,一張像刀子削過般的瘦臉,瞬間讓我打消了爭辯的念頭。我向他揮了揮手,迅疾移開了車子。
還記得早前看過的一篇關於“垃圾人定律”的文章,這個中年男子眼睛裡的語言,與文中的描述有著驚人的相似。與其爭辯,不如遠離。
某位哲人說過:一個人的嘴臉和靈魂,都寫在他的眼睛裡。由此看來,讀懂一個人,先得讀懂他眼睛裡的語言。
在講臺上站了這麼多年,早已習慣被幾十雙眼睛持續直視的感覺。想起剛參加工作的時候,課堂上被那麼多目光聚焦,內心總會有不同程度的侷促與緊張,如芒刺在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漸漸變得從容淡定,倒也不僅僅是因為年歲的增長賦予了自己更多承受壓力的能力,而是,我在逐漸熟稔課堂上收放自如的表演的同時,能饒有興味地捕捉任意一束目光,並沿著它,去讀懂臺下人眼睛裡的語言。
這或許和心理學有著某種關聯,但我並不願意這樣去解讀。二十年從教生涯,讀懂學生眼睛裡的語言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就好比一個靠手藝謀生的匠人,總有一天,他可以無須動手觸控,僅憑不經意的一瞥就能指認物事的癥結所在。當然,讀一個人眼睛裡的語言比指認某一物事,生動得多,精彩得多。
嘴巴可以說謊,但眼睛不能,更何況是高中生的眼睛。初為人師,之所以緊張不安,不過是因為自己的錯覺,以為講臺下的眼睛裡都寫著咄咄逼人的審視與質疑,當自己能夠去讀懂那些眼睛裡的語言,才算正式讀懂了真實而鮮活的靈魂,甚至比口頭對話來得更為直接。
講臺上一立,目光在教室環顧一週,在彼此眼睛對視的一刻,便可大致讀懂一些眼睛裡的疲憊與困惑,一些眼睛裡的迷茫與頹廢,也會在大多數眼睛裡讀到令人欣慰的語言,堅毅、自信、渴望、恭敬與執著,這樣的語言,彷彿好詞佳句寫出來的青春之詩。當然,有的眼睛表達的語言晦澀難懂,那是遊離不定的閃躲、迴避與不安。
讀懂眼睛裡的語言,也就讀懂了一個人的內心。雖然坐姿整齊劃一,表情千篇一律,但幾十雙眼睛所表達的內容有著天淵之別,你又怎麼能用一視同仁的方式去敷衍對待。用自己眼睛裡的語言去回應眾多眼睛的語言,便是此刻最好的對話方式。用目光傳遞對執著者的肯定與讚賞,對迷茫者的鼓勵與期許,對不安者的詢問與安慰,如此,就產生了“無聲勝有聲”的美妙效應。
對一個畫家而言,最難畫的的一個人的臉,畫臉最難畫的是眼睛。靜默時,一個人的語言全在於他的眼睛裡,沒有凝神聚力的揣摩與思考,要用手中的筆將之呈現出來,絕非易事。而讀懂一個人眼睛裡的語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源自內心的敏感,亦需要在漫長時光裡沉澱下來的識人經驗。而用眼睛有意地傳遞自己善意的語言,並讓對方有效接收,更是難上加難,需要突破年齡和身份的界限,需要努力用自己的心,去靠近另一顆心。
這個世上,毫不在意他人目光的人應是少之又少,你可以不理會他人的眼裡寫著什麼樣的心情,表達什麼樣的念頭,但你總會在一些人眼裡讀到這樣的語言:罹患疾病時親人眼中的關切,揮淚離別時愛人眼中的不捨,身陷困頓時友人眼中的鼓勵……這樣的語言如此美好,像黑暗中一束光,像迷失在茫茫荒漠中遇見的一枚路標。
如果有一天我們對視,你的眼睛裡陡然表達出驚訝、讚許與祝福,抑或不屑、厭惡與漠然,我想,這一定不是你慣常的表達,而是在某一個角度對我準確而客觀的解讀,那麼,此刻,我讀你眼睛裡的語言,實際上,是在讀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