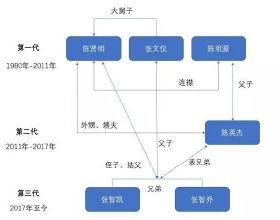那天我目緒了紅被眾人送去醫治,一群人把紅圍了起來送往醫院,伴隨著紅撕心裂肺的哭喊聲。我看見人群經過的地面上有鮮紅的殷跡
第二天清晨,白送信給我時,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就在前不久的幾個鐘頭,紅的老鄰居因一塊土地的歸屬問題與紅家起了衝突。那塊地向來都是紅家的。那個老混蛋早已眼紅許久,昨天正午,那老傢伙喝了點酒,又來到了紅家,依舊是爭吵那有關劃分的事。在與紅父母爭吵的過程中,因被指出無理取鬧,惱羞成怒的他一氣之下掏出了藏在外套內口袋裡的彈簧刀,趁其不注意向紅父母兩人先後瘋狂捅去,這一幕正好被剛剛放學回家開啟房大門的紅撞見,從小無憂無慮,天真的少女哪見過這種場景?當場嚇的揹著書包逃竄。而這位殺人犯呢?第一反應就是拋下屍體去追趕,以至於後來仁和警方到案發現場時,現場還是慘不忍睹的。
“他絕對該下地獄,上天不會寬恕他的。”白氣憤的大聲說著。整個人看起來好似一座爆發的默拉皮火山。“那個賤人在即將追上紅時,紅由於之前的呼喊,一些人聚了過來。老不死見已不能抓到她,竟然把彈簧刀朝她狠狠扔了過去。那個變態也被後來的人制服住。當時我正在醫院給科爾巴大夫送信,我看到被抬進醫院的紅腿上有個三四釐米的口子。鮮血正湧湧不斷向外流,地上甚至都成了一條血線”!白努力向我比劃著。
聽完整件事情發生前後的我也被震驚到了。但我努力保持鎮定,用從容地語氣告訴白:“他一定會收到懲罰的,仁先生會好好修理他”。
仁是世界的判決者,有人說他長生不老,因為他的年紀無人知曉。根據前書記載,3800多年前似乎他就已經存在了,那會仁個頭如同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卻生性殘暴,裁決事情的方式極其暴力,在某起盜竊案中,他在抓捕到驚慌失措的犯人時直接將其撕為兩半,事後也沒有任何人敢當面指責他。當然,這只是書上的描述,在我出生後第一次看到仁,他早是個通情達理,語言友善的大高個,卻莫名讓人不敢輕易靠近。他絲毫沒有書中描繪的那樣野性。唯一跟寫滿字的紙上描述相同的就是讓人感受到很有壓迫感。仁先生住在最北邊的一座山上,那是邊界最低的一座山,仁的鐵屋便在上面:他幾乎不回家——他太忙了,忙到每天都要處理各種案件。
“但願如此”。白聽完我說的話,眉頭輕輕舒展。
一年半後,審判的結果終於出來了,這次的審判時間久到讓人發慌,以至於讓所有人都相信這位殺人犯一定會被剝奪生命。然而,令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老鄰居僅僅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這樣的結果讓大部分人都不能接受。
白在知道審判結果的第一時間就通知了我。結果出來後,我懵了。怒火開始在內心復燃。通知那天是他的休息日,我清楚的知道這一年半的時間裡白是有多關心這起案件,每次給我送信時都會和我分享案件的最新情況,事情在他的口述中我大概知道此案過程中雙方是一直爭論不休的。
“你知道的,先生,最終的處理也太差了,我從來沒想過這麼差勁”。白那張未褪去稚氣的圓臉嘴角微微抽搐。我覺得白說中了我心。
我決定帶著白去找仁理論。
當我和白找到仁時,仁正在處理前不久發生的一起盜竊案。他把臉揹著我們,正低頭看著整理的筆供。
“先生,你可以跟我們聊一聊嗎”?我語氣盡量保持平和的朝著仁後腦勺問道。
“有什麼事直接說吧,我現在忙得很”。仁依舊低著頭。
“是這樣的,先生,對於剛剛不久您審決的紅父母被殺案。作為旁觀者的我和很多人都覺得很不公。請問您真好好去對待、審理了嗎”?
仁突然回過了頭,睜大那雙充滿血絲的眼睛打量了我和白。緊接著用冷淡的語氣拋了回來:“那件案子啊,我覺得我審判的沒有任何問題。那個老人是在犯完罪後自願認罪的,根據他的口述,那天中午他僅僅是因為土地的歸屬不太滿意而與紅父母討論那塊地,在這個過程中,紅的父母態度惡劣,還動手動腳,甚至拿出彈簧刀有意傷人,是他自己把刀搶了過來。因此這件案子跟其他社會影響嚴重的殺人案不同,這是為了維護自己生命安全的犯罪,犯罪人犯罪後自首,說明他有認罪懺悔的心態,整案站在犯罪人角度犯罪動機和手段並不是特別卑鄙。老人的口碑在周圍一直都很好......除了紅家,憑這些完全可以斟酌減輕量刑。”
聽到仁的回答,憤怒,就像怪獸一樣吞噬著我的心:“你在開什麼玩笑?這畜生被抓前還把紅的腿弄出一個大口子?這是自首嘛??他自己掏出的彈簧刀怎麼成了紅父母拿出的,你簡直是在胡說八道!如果仁夫人來審判的話,事情絕不會是這樣的!”
聊到這,不得不再跟提一下仁夫人,從名字就顯而易見,這是仁的妻子,仁夫人住在大陸最南端,她像仁一樣不怎回家。她也與仁一樣很忙,但她並不裁決事情,只是負責每天大陸上發生了什麼。再把一些需要裁決的事列成一個表,每天仁都要去她那領取表格來進行當天的工作。仁夫人的善良是出了名的,整個大陸的人都知道,很多人都沒見過仁夫人,卻常常喜歡拿這位美麗的小姐作比喻。她會經常接納那些剛出生就被拋棄的小狗小貓,經過精心裝扮培養送給喜歡寵物的人,再或自己養。她時常會自掏腰包來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紅小時候生的一場大病仁夫人就出資了,為此紅父母的感謝讓周圍的人都知道,紅父母告訴了白,白告訴了我。仁夫人就在居民的身邊,只不過很多居民沒見過罷了。12歲那年我曾有幸見過仁夫人一面,那天可能發生了一些特殊狀況,表是仁夫人主動來給仁的。不過這件事已過去很久,現在再回憶,印象中只記得仁夫人擁有一雙清澈的藍眼睛,除此之外便毫無印象了。
“你說的這些,是從紅那裡聽過來的吧,這位老人是殺人了,可小女孩的話並不都可信,他在送往醫院後被診斷出了精神失常,這些話都是之後的事了,紅曾在好幾年前就被檢測出了精神分裂,之後她父母的說法是康復了,但現在好像是復發了,亦或其實根本一直精神都有問題。案子完結她就要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療,至於鄰居不小心傷害了她,是因為他想跟女孩解釋,卻因喝醉了酒摔跤讓刀片飛了出去。不管你怎麼說,對於這次判決的結果我是不會改的。好了,快走吧,別妨礙我工作。”仁依舊臉色不改,之前的視線也從我們身上再次移到他那張破舊,薄薄的筆記本。
我對於仁的回答已經無語了,我不知道以前那位高大,通情,喜歡聽取民意的法官去了哪裡,現在站在我面前的讓人感到只是一具幾米的空殼。
我感到有點陌生。
“白,你不說些什麼嘛?你...."我想尋求白的幫助,剛想開口便看見白眼睛朝我眨了眨。我明白,他是示意我先不要再當面講了。
到了私底下,我不明白前不久十分惱怒的白為什麼突然在仁面前變得沉默寡言,難道都是假的,白是裝的?看著我著疑惑的盯著他,白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眼裡射出了幽冷的眼光:“您一定很好奇我為什麼剛才不說話吧”?
我點了點頭,剛想開口,見他擺了擺手:“只要仁不同意,不管怎麼說都沒用不是嗎?這件事情的結果實在太荒唐了,我在判決之前每天晚上睡覺都要躺在床上想,怎麼樣的刑罰才能讓這個人渣痛苦至極,將他撕成兩半?這樣太野蠻了、將他槍斃?這樣太便宜他了、再或殺了他們家兩口人?也不行,這件事跟他家人沒有關係.....輾轉反側在床上睡不著,曾想過很多次這件事的後續,卻從未料想過以這樣的結尾收場。不過,我相信他會遭到報復的,一定會的”。
說完,白便轉身離開,只剩下呆愣住的我。
晚上到家,我又開始思考起了今天的事,我很不解為什麼仁處理這次案件會變成這樣,在我的記憶裡他應該善解人意,富有感情的。今天的他卻讓我感到截然不同,我突然想起今天在與仁對話時,我似乎在他後腦勺下面一點看見一個口子,口子...沒錯,我看見了一個口子,我依稀記得那口子不大不小,當時因為只想著案子的事,沒怎麼在意,現在想想,是有點不對勁,不過那到底是個什麼呢?白今天也是很詭異,他說的那番話讓我毛骨悚然,我有預感,他不久後要行動。
第二天清晨,白沒有照例給我送信,我站在門前等著白,半小時、一小時、兩小時過去了,白依舊沒有來,我依舊站在門口。早飯時間早過了,都要到午飯點了,我仍像個木頭人一樣在那不動。又不知過了多久,我看見兩個小夥子抬著一副擔架,幾個身穿警服的人圍在旁邊,朝我走來,等距離稍微拉近,我逐漸認出在擔架上的人。
擔架在我面前停了下來。
他在擔架上躺著,臉色蒼白無色,沒有了之前的精氣神,活像骷髏。汗水就像散落的珠子一樣從他的額頭緩緩竄出,他的表情看上去很痛苦,整張臉擠在一起,身體好似蜷縮在一起。我緊緊握著白的手,發現他手冷的嚇人,“你這是怎麼了,我的朋友?”白感覺到了手掌的溫度,吃力的張開眼睛:“我做到了,先生,我成功替紅報仇了,我相信紅一定會開心,那個老蒼皮遭到懲罰了。我把他殺了,真解氣,但我......可能.........也要............去見上帝了。”說完,這位年輕人再也沒有力氣回覆,嘴巴微微張著,卻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就到這吧,他需要休息”。擔架旁的一個警官開口了。“他在今天凌晨偷偷翻牆闖入一名老人家的庭院,趁著夜色並未有人發現,悄悄來到庭院內未上鎖的屋子裡,用彈簧刀殺死了房子裡年紀最大的一名老人,這位老人好像跟前不久附近的一起命案相關....不過這不重要,隨後他丟下武器逃跑了,不過在中途被其他的家人發現認出他是送信的郵差,在認出他後,這位老人的妻子到廚房拿出菜刀捅傷了他,他被捅吃痛後連忙翻出圍牆又因為帶傷重心不穩摔了下去,隨後東竄西竄,又跑了好久,老人家屬報警後,我們沿著圍牆下的血跡慢慢跟著,排查了一路,在半個小時前才逮捕了他。仁先生說前不久他見過郵差,郵差曾向他諮詢之前關於老人犯下的一起命案,他指出這是個帶有目的性的暴力報復事情,像這種案件性質相當惡劣,必須嚴肅儘快處理。這件事情馬上就會有個結果的。”
男人說完,我緩緩拉開一點鋪在白身上的白毛毯,白腰上的衣服破了開來,一道清晰的、深深的劃痕傾斜在白的腰上,傷口的血已經凝結了,鮮血凝固了白的襯衫。“他非要來見你一面,我們看他這麼虛弱,呦不過他,就帶他來了,現在他也完成了自己的心願,我們要帶他走了。考慮到他跟你關係這麼密切,在之後的日子裡,我們會請你來警局一趟做次筆錄,希望你能配合我們”。話音剛落,擔架又開始緩緩向前。
我鬆開手,起身站了起來。看著那張稚嫩、蒼白的圓臉離我越來越遠。
202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