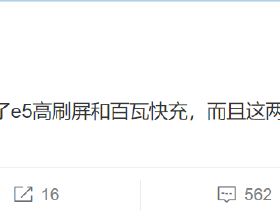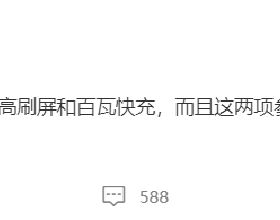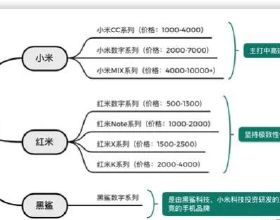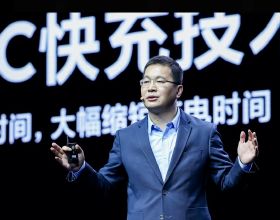收銀員小秋
一個週末清晨,突然收到日本某公司的電話。負責人提醒我說明天來辦理相關手續的時候別忘了帶上印章。在花了幾小時試圖找出上一次用還是好幾年前的印章未果後,我意識到重做一枚是不可避免了。好在兩站路外有一家週末也營業的印章屋。在交付了700日元(約合人民幣41元)並等待了10分鐘後,一枚刻有我漢字姓氏的簡單印章隨即完工。隔天到了營業所,另一位不同的員工看到我拿出印章時充滿笑意地說:您還真是細心。其實為了順應各界對於廢除印章的呼聲,我們現在光靠簽名也可以完成手續了。在一種類似“來都來了”的心態下我還是選擇了蓋印,並且相當用力。即使我知道光靠這點力氣大概是永遠無法摧毀一個公司或者整個日本社會強大的官僚主義。
可能正是因為像這樣被繁雜的手續攪到不寧的怨聲已經彙集到了一定程度,就連日本政府也很難再坐視不理。在去年9月被任命為“行政改革擔當大臣”之後,河野太郎就把廢除不必要的行政手續作為自己最主打的政策。其中,印章成為了一個重中之重。在上任一個月後的記者會見上,他就宣佈了政府計劃廢除目前約一萬五千件需要按印的行政手續。但在這一改革的真實效果被民眾感知到之前,他就先受到了來自各方的反對聲音。印章產業的強力反彈當然是預料之中的,而來自企業、公共機構等本應是該項政策受益者們的不滿則多少有些意外。以小見大,網路時代的印章作為一個“不合時宜”的存在卻依然頑強的事實,大概是日本科技產業整體所面臨問題的一個縮影。但如果我們能脫離一種線性進步觀的話,或許也能重新思考關於大小技術和各色工具在一個社會中現實的存在和發展方式。
權力與管理:日本印章小史
和許多其他的器物或制度一樣,日本的印章文化也是從亞歐大陸傳來的。今天可以確認的最早的印章誕生於6000年多前的中東地區。但此後對於日本更為直接的影響則主要來自於中原。中國本土的印章文化發端於戰國時代,而日本國內現存最早的印章則是公元57年由後漢的光武帝贈送的“漢委奴國王”金印。 雖然於今天的福岡縣出土的這一國寶真實性仍存在不少爭議,但它所包含的被“贈予”的態度無疑暗示了一種原始的“先發”國家對“後發”國家的權力姿態。日本真正開始系統性地吸收印章文化則要等到公元7、8世紀。以隋唐制度為模範的政權在701年正式對公文書裡“官印”的使用做出了明文規定。而一些擁有特權的高官也被賦予了刻制“私印”的特權。
但很快,日本本土的“國風文化”開始興起。和楷書漢字慢慢被草書式的日語假名所取代一樣,在檔案上蓋漢字印章的行為也被以圖形和符號為主的“花押”蓋過了勢頭。印章文化再次復興則要等到鎌倉幕府時代,和禪宗一起傳來的作為書畫附屬物的宋元文人印開始大受歡迎。但無論再怎麼發展,中世日本的印章總體上在一個很有限的範圍內傳播。它和庶民的生活基本上沒有任何聯絡。最早作為外部更高文明象徵的印章此時演化為了作為內部更高階層的權力代表。
印章的利用開始大規模在百姓間滲透始於江戶時代,背後有兩個重要的結構性因素。首先,奉行鎖國政策的幕府一個重點防範物件是西洋基督教的傳播。政府要求民眾在基層管理機構進行身份登記並簽署不信教的協議書,而在識字率還低下的彼時,用來代替在檔案上簽名的就是一個個簡單的印章。第二,在近400年總體上和平的大環境裡,日本國內的商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就對在每次交易中參與方的“信用”擔保提出了要求。在地方行政單位進行過登記的個人印章就成為了一個最好的對策。與此同時,透過公認印章所準確掌握的每一筆交易細節也為幕府對於財稅的徵收提供了最大的保障。
就像不少歷史學研究已經揭示的,被譽為日本“現代化起點”的明治維新實則繼承了許多來自江戶時期的遺產。這一論斷在印章這裡也成立。1873年,新政府把之前就盛行的在交易時需要刻印的規定法條化。而對於偽造或者盜用他人印章的懲罰也幾乎是比照了前例。另外一個有意思的點是1885年日本的現代內閣制度正式成立,每一個閣員在簽署政策檔案時需要額外提供自己的花押而不是印章,此一習慣延續至今。透過和普通民眾姓名章的差異化,現代官僚所享有的特殊社會地位和權力也又一次在“按押”這一細小的舉動中得到了體現。
印章制度的“異化”
其實早在明治時期,關於印章是不是已經不合時宜的討論已經發生。之前提到印章之所以盛行的一個原因是它可以解決因為民眾低下的識字率而導致的各種手續中的不順。但在受教育率已經得到大幅提高的明治時代,它的這種合理性就已經喪失了一大半。更進一步說,靠簽名來驗明正身的實踐早已成為西方社會的一個慣習,這更給了主張全面西化的一派廢除印章的重要口實。但在反對派“軟性的”對於傳統文化保護的主張以及“硬性的”印章產業的利益支援下,簽名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只是獲得了和印章差不多接近的法律效力,更不用提徹底取代後者了。隨著時間的發展,這種因為“路徑依賴”所產生的制度異化可謂是愈演愈烈。

面對傳統印章被廢止,越來越多的日本公司開始推出更具設計性的印章來吸引消費者。圖為城山博文堂推出的人氣產品貓咪印章系列。來源:oricon news
河野大臣所宣佈的一萬多件需要印章的手續將被廢除其實告訴了我們兩件事。第一,到目前為止至少還有那麼多的環節沒有印章就不能完成。第二,它們其實壓根就沒有必要。在今天的日本社會,印章大體上可被分為兩種。一類印章被稱為“實印”。它們需要在地方政府的相關視窗進行登記,並具有完整的法律地位,在諸如不動產交易、遺產繼承等場合這些印章不可或缺。而另一種則是所謂的“承認印”。這種沒有經過登記的印章其實只代表了“本人已熟知上述事項”,而根本不具有任何的司法作用。事實上,如果你的名字不是生僻字或者你不趕時間的話,在隨便哪個日本版的“二元超市”都能用便宜的價格買到一個即刻能用的印章。畢竟,“承認型”的印章上所雕刻的只有“佐藤”或“高橋”之類的姓氏而已。由此,日本的印章文化陷入了一種“誰都可以被證明,誰都又不能被證明”的尷尬境地。
當印章自身從一種“手段”變成了“目的”之後,由此引發出的一系列特殊的使用規則更是到了讓人皺眉的程度。一個經典的例子是某日本銀行巨頭的前員工曾爆料,公司在蓋章時有個規定是印影不可以保持端正的豎直,而需要向通常是蓋在自己左邊的上級的印章略微傾斜,以示尊敬。此外,在因為新冠疫情有越來越多公司選擇了在家辦公的方式之後,不管是對外的談判還是對內的溝通都可以透過網路來遠端完成。但不少日本公司的員工至少每週必須要去公司一趟,因為他們不得不在實體的紙面上完成“按印”這一無法被網路替代的步驟。正是這些本末倒置的行為讓民眾對於印章的批判達到了一個高潮。網上甚至出現了一批被稱為“印章警察”的群體。和早先在日本緊急狀態中出現的只要有人稍微鬆一下口罩透個氣就破口大罵的“自肅警察”一樣,這些“印章警察”只要發現有企業還在規定員工按印的訊息時就會傾巢而出,把諸如“造成了日本經濟停滯”的大帽子蓋在它們頭上。
也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菅政府所推出的改革企圖才有了強大的正當性。根據NHK的一項測算,在廢除了印章之後公共機關面向每一個民眾的服務平均至少能省下10分鐘。而與之相伴隨的電子化更能在一年間省下3000萬日元的經費開支。
“鑲嵌”在社會和文化中的技術
在各種“大義名分”的旗幟之下,河野大臣和菅政府對於印章發起的猛攻看上去展現了自己的決心和執行力。但正如社會學家們經常提及的“鑲嵌”(embeddedness)這一概念所提示的,印章這一“技術”在長時間的發展中已經和相應的社會及文化結構產生了不可切割的聯絡。沒有考慮到這些現實問題而強推的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讓人不禁打上一個問號。印章和既成利益集團聯絡的一個例子就是在日本的國會內部存在著一個“守護日本印章制度・文化”的議員聯盟。它和由印章界各企業所組成的團體“全國印章業協會”有著密切的聯絡。在這一可類比於美國國會遊說團體的組織中,最讓人驚訝的一名成員正是旨在推動電子化進展的IT政策擔當大臣竹本直一。雖然他一直強調印章文化和電子化並不矛盾,但在政府廢除印章的強勢姿態之下,他最終還是選擇退出了這個議員聯盟。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對於廢除印章的抱怨還來自這一政策邏輯上的受益者。根據日本媒體的報道,不少企業表示雖然需要印章的交易環節的減少確實讓員工負擔有所減輕,但它同時造成的問題也不可忽視。財經雜誌《週刊東洋經濟》就此問題推出過一篇十分有啟發性的報道。該報道的作者指出廢除印章的正面效果基本是面向公司內部的,而它的負面效果則是由公司在和外部企業打交道時所產生的。更進一步說,問題的核心還是在於日本的宏觀產業結構。雖然一些人人都叫得出名字的大公司左右著經濟活動和社會輿論,但單純就數量來說日本公司的九成以上仍然是中小型企業。它們對於包括無紙化辦公在內的技術轉型的意願無疑要小得多。作者提供了一個明瞭的資料:在主要由大企業所參與的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中,成員公司中的97.8%已經完全實現了遠端辦公的環境整備。但相比之下,員工數在50-300人之間的企業其遠端辦公的匯入率僅為28.2%,而50名以下員工的小公司這一資料只有14.4%。換句話說,也許我們腦補“一個大公司的員工通勤一小時,再走去五樓以上的副總裁辦公室只為了蓋一個章”這樣的場景會覺得離譜。但如果把它換成“住在職工宿舍的下屬走到宿舍隔壁的公司,並把契約書遞給工位緊挨著自己的社長請他過目”的話,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中小型公司沒有動力來實現包括廢除印章在內的資訊化辦公了。
報道的作者更是進一步提出印章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日本經濟身處泥沼的“替罪羊”。回溯歷史,我們會發現幾乎時隔十幾年就會掀起一次對於印章文化的大批判。但那麼多年過去了,印章仍然堅挺地存在。所以,問題的關鍵並不在印章本身,而是它背後潛伏的官僚作風。反過來說妄想著透過廢除印章就能實現徹底的經濟轉型也是完全行不通的。這讓人想起了Zoom視訊會議因為疫情剛開始風靡之初收到了許多日本企業關於哪個分螢幕是“上座”的詢問。這一比段子還讓人哭笑不得的現實說明,如果企業的結構和文化沒有根本性改變,無論多“先進”的技術都不太可能帶來變革。
另一個相關的例子是傳真機。在新冠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日本的保健所仍然用傳真來相互聯絡和彙報病情的新聞著實讓世界跌破眼鏡。差不多同一時間的一個新聞是日本的超級計算機“富嶽”蟬聯了效能表現世界第一的排名。兩者的對比更是讓人一頭霧水。能回答這個問題的還是技術本身的“鑲嵌性”。其實河野大臣曾經表示,在印章之後下一步要廢除的就是在公共服務中被廣泛使用的傳真機。但這一宣言在釋出沒多久後就被撤回。就拿彙報病情這一個例子來說,如果要對系統進行全面升級就需要統合大型公共醫院、小型社群診所以及衛生部門等數個異質的環節。但戰後的日本政府無疑缺少相應的資金、權力或法理來實現這個目標。再有,在歐美國家曾數次發生的因為駭客入侵而造成患者資訊流失的事件也讓日本的民眾和醫生團體對更新換代的意願被大幅削減。而如果真的能實現每個診所都匯入計算機的話,全世界醫生似乎共享的難以辨認的“書寫體”又要怎樣和網路系統實現相容,可能又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東京的業者以“河野太郎”為主題設計的印章。在間接傳達了不滿的同時又把這一“逆風”轉變成了宣傳印章文化的機會。來源:東京印章協同組合。
但頑固如日本印章業也體會到了一種變革必將降臨的危機感。好在從業者看起來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麼擔心。一方面之前提到一定數量的需要印章的手續仍然得到保留,其中既有房屋買賣這種強制性的規定,也有婚姻申請這種帶有紀念色彩的可選擇性環節。更重要的是,挖掘印章這一工具正面的文化維度是從業者從很早就已經開始鋪墊的。比如在東京的印章屋就發起了一場姓名印章設計大賽。而比賽的主題被不無諷刺地定為了“河野太郎”。最後23位手藝人呈現了77枚毫不重樣的設計,向大家展示了手工刻章的魅力。其實河野大臣在宣佈廢止印章後很快也在推特上曬出了自己的書畫印收藏。由此,他所採取的其實是和前文中IT政策擔當大臣同樣的立場,即網路化和印章文化其實並不矛盾。另一方面,不管是作為日本各觀光地保留專案的“蓋章接力”還是近年來在世界範圍內都越來越受到歡迎的日本手賬文化裡的裝飾性印章都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政府方針所帶來的損失。

印章也隨著近兩年來的日本文具熱在世界各地受到歡迎。圖為手賬名店traveler’s factory的印章產品。來源:公司官方推特
總而言之,不管是傳真機、印章又或是超級計算機,任何的技術都不是“客觀地”發揮著推動人類進步的作用。圍繞著它們所展開的社會和文化維度是一項技術能發揮正面或負面作用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門田誠一、『はんこと日本人』、大巧社、1997年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