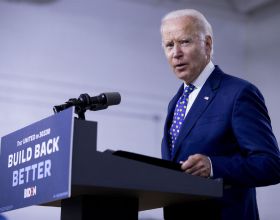屈照林題
……大家為他鳴不平。他一笑:“那資格能當飯吃?我是來幹革命的。紅軍、八路,不都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能證明我跟著共產黨走,就行!”
永遠的老班長
——追尋一位晉察冀軍區 “老模範” 的蹤跡
·張福榮
我緬懷的人是一位革命資格很老的班長。班長、“將軍”、老倔頭,說的是同一個人。他就是原255醫院的老軍工張德臣。
說他是班長,有根有據。檔案上記載,他是“三八式”。但按實際情況,他從1937年初開始,已經在聶榮臻領導的部隊裡背圖紙、做飯了。戰爭年代,一天到忙打仗,那時沒檔案。
建國初期建檔案,憑著記憶,湊整去零,誰也沒當回事。誰知日後還要講資格!大家為他鳴不平。他一笑:“那資格能當飯吃?我是來幹革命的。紅軍、八路,不都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能證明我跟著共產黨走,就行!”結果,直到1955年部隊大裁軍,他由軍轉工,還是個大頭兵、“炊事班長”。
說他是“將軍”,部隊上下都信服。從當年的晉察冀軍區,到後來的255醫院,誰都知道,他見官大一級。只要犯到他手裡,甭管官大官小,準保一頓“尅”。
打仗那會兒,一位團長吃飯掉了幾粒小米飯,讓撿起來吃掉。團長大大咧咧滿不在乎。他氣壞了,沒鼻子沒臉的一通“剋”。正巧,司令員路過,給他豎了大拇指,“在後勤伙食這塊,你就是‘司令員’。遇見浪費的,你就這麼‘剋’!”。
後來,醫院進城到了。一位從上級機關剛下來的副院長,私自到後廚倒香油。他當著眾人面“剋”的副院長臉上一陣紅一陣白。
全院人員都知道,“犯錯別讓他遇上,就是‘將軍’都不好使。”一位捱過他“剋”的部隊領導,離休後,寫信給他:“職務上,我是你的領導。但思想上,我得向你學習!”
說他是“老倔頭”,我聽的故事可不少。抗戰那會兒,他火線送飯,行軍鍋被穿了幾個眼,肩膀上被掀下去一大塊肉。部隊打了勝仗,召開慶功大會,分割槽政委王平親自給他戴紅花,發證書。他一扭頭,將立功證書撕了。問他為什麼?他理直氣壯:“那麼多戰友犧牲了,我還活著,立什麼功!要立功先得給烈士們立。”為此,他先立功後背處分。
他作戰勇敢,做飯精心,領導多次想給他提幹,他死說活說都不幹。以後,提級、長工資,甚至組織出面給他說媳婦,都被他推脫。哎,年輕時,人們叫他“老倔”,上了年歲晉級了,成了“老倔頭”!這些情況,我都是聽說。
書歸正傳,還是說說我的親身感受吧。
一訪老班長
第一次,到255醫院出差。我起了大早,在醫院的環形路上走走,熟悉環境。清晨,太陽初露,空氣清新,鳥兒歡唱,行人匆匆。迎著太陽,一老一少從對面走來。老人架著雙柺,趔趔趄趄,卻頑強地一步一步地挪動著。跟在身後的年輕小夥,幾次要伸手攙扶。老人猛地一掙,便把年輕人的手打了回去。
初春的晨風,依然冷得扎骨,咬得肉疼。他,一身已成古董的抗美援朝的舊棉裝穿在身上,雖然完全褪了色,但卻漿洗得乾淨整潔。陳舊的解放棉帽戴在頭上,護耳帽帶隨風上下飄擺。老人時而停下,從口袋裡掏出毛巾擦擦額頭的汗水;抬頭看看前方,接著又走。眉宇間,露出不屈不服的神色。
原二五五醫院大門
時進改革開放,跨度30多年。這樣的軍裝,早該進展覽館了。好有特色的穿著,好有性格人!
他是誰?醫院政治處楊文學幹事告訴我:他叫張德臣,是個老紅軍,原來的醫院炊事班長。年過七旬,退休不休,義務在醫院找活幹。看到有人浪費,他要管;看人違反規章制度,他要管;看人做出有損黨的聲譽的事,他要管。大家叫他“管得寬的老倔頭”!我心頭一熱,頓生敬意。
找了個下午時間,我拉起楊幹事。走,看看張班長去。張班長住在醫院家屬院,與醫院僅一牆之隔。這裡是唐山地震後的新建築,佈局嚴謹合理。寬敞的道路兩旁排列著整齊的樓房,高高的白楊樹站立在樓間、路旁,憑添了幾分生機和威嚴。院裡很靜,看不見人影。
我們三轉兩拐,就來到張師傅門前。這是一排排紅磚樓房中的其中一棟,張師傅住在一樓西側的一間獨單裡。屋門敞開一條縫,楊幹事帶著滿臉的燦爛和攪拌了蜜糖的一串串話語,招呼著:“張班長、張班長”,“嘻嘻、嘻嘻……”推門進了屋。我緊隨其後,心裡不免有些緊張。
房間不大,打掃的乾乾淨淨。屋中的陳設很簡單,被褥疊放的整整齊齊,衣帽掛在牆上,完全沒有獨居老人的邋遢和異味。一杯冒著熱氣的水放在桌上。杯子雖然陳舊斑駁,但上面的字卻清晰可見,“獻給最可愛的人”。眼前的一切,告訴我,房間的主人過去是、現在依然還是一個兵!
老人坐在床上,帶著老花鏡,手裡拿著一條打著補丁的秋褲,正在一針一線地認真縫補。一雙大手青筋隆結,像飽經滄桑的老樹,虯枝盤曲,粗壯有力。那看似僵硬、乾枯的手指,一旦捉住針,頓時變得十分靈巧。隨著針線的行走,十個手指的肌肉在一動一動的彈跳。彷彿每根肌肉都在訴說,所有的毛孔都滲透著激情。一針又一針,針腳縝密,漏洞一點點縮小,老人的額頭上冒出一層層細密的汗珠。
楊幹事介紹了我們的來意。老人抬了下頭又低下了,只顧忙活著,並不理睬。楊幹事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訕著,聲音依然甜蜜著,臉上依然燦爛著,嘴裡依然不時地“嘻嘻”著,老人依然無動於衷,並不答話。我們自找椅子坐下。
我仔細端詳著老人。頭髮稀疏,已成灰白色。頭頂已經完全光禿。由於偏瘦,更顯得頭骨凸出。面頰上鑲嵌著深深的皺褶。一位十分普通的七十高齡老人。如果走在大街上,他與來自山區的老人毫無二致。誰會想到,他是位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八年入黨,曾經叱吒風雲的老戰士!
趁著老人端杯喝水的空,我急忙說:“老英雄,我們看您來了。”老人停住了送到嘴邊的水,透過眼鏡的夾縫中,甩過一撇不屑地眼神和僵硬地話音:“我不是英雄,也沒那個資格。那些犧牲在戰場上的戰友們,他們才是英雄……”老人開了腔。這是難得的機會。我急忙補上一句:“您從戰爭年代就是老模範。當年的《晉察冀日報》曾幾次報道過您的事蹟。建國後,您也一直是模範。我們向您學習來了……”沒等我話音落地,老人彷彿甩來一根棍子:“沒啥可學習的,都是我該做的事。”聲音中透出生疏和拒絕的寒意。說著,又悶頭縫補起來。我還想說點兒什麼,看看老人並無興致,只好作罷。
我環視著間十幾平米間小屋,遺憾地發現在邁入現代化的今天,這位為黨的事業奮鬥了近半個世紀的革命功臣,“幾大件”卻是一箱、一櫃、一個半導體、一座小鬧鐘……當我的目光落在您空蕩蕩的雙人床上時,一絲悽楚襲上心頭。老人終身未娶,一直是形影相弔,孑然一身呵!
我們坐了一會兒,見主人並無待客的意思,頗有些尷尬,便告辭出來。臨走,楊幹事撂下話:“要換煤氣罐,您可招呼我。別客氣。我年輕,身體棒著呢!”
對門住著高姐一家。高姐四十多歲的年紀,也在醫院食堂工作。夫妻倆都是熱心腸。一個單元住了多年,聽聽老鄰居會說啥?高姐為人熱情爽快,一聽我們的來意,立刻亮開她那唐山女高腔,開啟話匣子:“老爺子這麼大歲數了,還是保持著老紅軍、老八路的作風。衣服髒了自己洗,襪子破了自己縫。我們兩口子總想幫幫他,他只要能動,從不讓幫忙。他有時在食堂打飯,有時自己做飯,捨不得吃好的。我們包個餃子,蒸個包子,讓他老嚐嚐。他推來讓去,還說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老爺子生活忒節省。他一分錢都掂量著花……”
高大姐聲調平和,臉上浮現著敬佩、憐惜的複雜神情:打飯,他買最便宜的菜,剩下菜湯充水喝,捨不得買碗湯。夏天,他捨不得吃根冰棒。冬天,他捨不得買煤取暖。噢,那是住平房,屋裡沒暖氣的時候。屋中,只點著三瓦的小燈泡,三個月只用一度電。一雙解放鞋補得走了模樣,一頂舊軍帽戴了近40年。一位多年沒見面的老戰友來看他,雖然天色已晚,老爺子卻不肯開燈。我以為燈壞了,讓孩子他爹幫助修修。老爺子和客人都說,“不讀書,不看報,還是關著燈聊天好……”老爺子自己生活上節省,工作中也處處給院裡節省。他上班那會兒,食堂的一盆小米飯餿了,他一個人偷著吃了八天。
老辦公樓
部隊剛進城市時,住在撫寧縣,燒煤很困難。他拿起砍刀上了山,一年中砍來了幾萬斤山柴,硬是一年沒買煤燒。後來,部隊遷進唐山市,燒煤很方便。但為了節省開支,他天天去車站揀煤核。風風雨雨20年,揀回的煤核能堆成山。
高大姐突然用手捂嘴,呈喇叭狀,聲音漸低,顯得有些神秘:“老爺子脾氣有點怪。前幾年,院裡蓋了新樓房。為分房,大家爭得臉紅脖子粗,都覺得自己房子分的少;老爺子也爭得臉紅脖子粗,嫌自己分的房子多。他分三室、兩室都夠資格,卻偏偏選擇一室屋。他說,住多了浪費。嗨——好人!”說著,頭在微微搖動。看得出,對老人的怪異,她有些不理解。高大姐介紹了好多情況,直到該做飯才剎住車。
兩天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我回到機關。 不久,醫院傳來一個揪心的訊息:“張班長病危了”。他戰爭年代頭部受傷,留下了病根。現在年齡大了,病情時常發作,立即住院搶救。
院領導趕來了,醫生護士們趕來了,就連大院裡的孩子們也趕來了!張班長雙目緊閉,呼吸急促地躺在床上,醫護人員在緊張地搶救著,院領導守護在一旁。儘管做了說服工作,但樓道里還是站著許多幹部、職工、家屬、學生。過了一會兒,張班長睜開了眼,看著四周人們,最後,眼神落在政委趙康軍臉上。他不顧醫護人員的阻攔,費力地翻動翹起身子,從枕頭下掏出個綠布包,抖動著雙手一層層開啟。
展現在大家面前的一疊疊嶄新的十元一張的人民幣。張班長吶吶地說:“這……是3000元錢……我把它全部……交黨費。”趙政委一把握住張班長的手,淚水止不住地從眼裡湧出來。張班長的嘴角露出一絲微笑,又昏過去了。
當晚,院黨委召開緊急會議,議題是“張德臣的錢怎麼處理?”
不知為啥,大家一開口,話題就跑到張班長几十年來平凡而感人的經歷上。從1955年張德臣由現役軍人轉為部隊職工,定為四級炊事員,每月工資61.5元。以後幾次調整工資,每次都評上他,他總是把名額讓給生活困難的同志。他自己在生活上克勤克儉,對國家、對同志、對群眾卻慷慨大方。
三年困難時期、邢臺、唐山地震期間,他曾五次捐款捐物,多達5000餘元。同志中遇到過不去的坎,他也解囊相助。一位戰士因為母親病重沒錢買藥急哭了,他得知後,立即把身上僅有的70元錢掏給了這位戰士……按照當時的物價水平,他的工資,一個月可以買100多斤豬肉。但,他每次打飯都買最便宜的飯菜。只有逢年過節、來了客人,才肯買點兒肉,包頓餃子吃。他穿的衣服,都是舊軍裝,縫了又縫,補了又補。
張德臣的捐款,在當時可稱為“鉅款”,都是從一根冰棒、一碗湯中節省出來的。追憶往事,黨委成員一致認為,張班長年大體弱,需用錢的地方很多,這筆錢黨組織不能收。領導同志把決議告訴張班長後,他沉思片刻,說:“反正這是黨的錢,組織不收就買成國庫券吧。”組織上代他買成了國庫券,張班長卻把它存進會計室,一直沒去領取。
蒼天有眼, 好人張德臣又一次活過來了! 張德臣病危和購買國庫券的訊息傳遍了全院,也傳到了親友的耳朵裡。他的表哥從外地趕來,一見面便埋怨他:“過去你積極,我支援你,因為大家都積極。可如今,人們心眼活了,你留著錢害怕扎手?”張德臣對這位有30多年黨齡的表哥說:“到啥時候,共產黨員也要積極,也要進步。只顧自個兒,那叫群眾瞧不起!”接著,兩位老黨員談起了各自入黨時的情景,談起了老黨員的責任,越談越投機。不久,張德臣的一位遠房侄子找上門,轉彎抹角想把這筆錢要走。張德臣拒絕了侄子的要求,並告誡侄子說:“如今黨的政策好,只要肯動腦筋、出力氣,不愁富不起來。要是光想著天上掉餡餅,就是佔這個金山也得受窮。”
初次接觸,我被張班長的忘我情懷感動著!生死界限,意識殘存,唯有一念中正、執著。張班長,你就是我心中的崇拜的英雄!
二訪老班長
隨著對張班長了解增多,我更想和他多聊聊。當再次來到255醫院的時候,我又一次拜訪了老人家。
正值盛夏。考慮到老人家午休,待太陽照到西山牆的時候,我們才登門。天氣悶熱,樹上的綠葉耷拉著,無精打采,蟬兒高一聲低一聲地唱著。幾隻蜜蜂,圍著窗臺上的兩盆鮮花飛來飛去。張班長家的窗戶和屋門敞開著,一掛竹簾掛在門上。樹蔭遮窗,溫度舒適。
我們撩簾進屋。見張師傅上身裸露,精氣神很好,一手拿著收音機靠近耳邊;一手搖著大蒲扇使勁在搖。收音機的聲音不大,老人一邊聚精會神地聽著,一邊一顛一拐地在屋中踱步。我仔細觀看,張班長中等身材,身體結實。雖已70高齡,但腰不彎背不駝。由於常年勞動的原因,身上面板飽滿,肌肉清晰顯露,根本不像一個垂暮之年的老人。唯獨走路有些費力。
一回生二回熟。見我們進來,老人投來友善的目光,招呼我們坐下,順手拿個毛巾,擦了擦額頭上的汗水,自己也坐下來。為怕直奔主題冷了場,我先從聊天開始。聊天氣,聊作息,聊身體。我話頭一轉,問老張師傅:“聽說前段時間,您頭暈的老毛病又犯了。一次比一次厲害。這病根是咋落下的?”一陣靜默之後,老人沉思著,訴說著——“那時,我剛入伍時間不長,身強力壯,做勤雜工作,都是隨指揮部行動。部隊住下,我負責站崗警衛;部隊行軍,我負責背圖,就是作戰地圖、各種檔案。有一次,部隊夜間在山區行軍。半路上,與鬼子漢奸的大部隊遭遇了。敵人仗著人多,把所有路口都堵死了。我們趁著夜暗突襲。山區地形複雜,到處是一片漆黑。我們衝破敵人的包圍,必須攀登岩石峭壁。敵人的機關槍像火蛇亂掃,我腿上中了彈,滾落懸崖。我昏迷一天多,醒來後,頭上是血,左腿骨折,衣服上都是血嘎巴。聽了聽,山裡靜極了,沒有槍聲,也沒有人影。我摸摸身上,因為捆得結實,地圖和檔案還在。心想,地圖和檔案在就行,首長指揮戰鬥還等著用呢。我一定得找到部隊!當時,頭暈著,腿瘸著。能站起來時,我就找根樹棍拄著,一蹦一顛地走。走不動時,就在地上爬。餓了,揪幾把山草,渴了捧幾口山水。第四天,終於找到了部隊。我把圖完好地交給分割槽首長。首長特別高興,拉著我的手一個勁地搖,還說:你是一個忠誠的戰士!也就從那次之後,我落下了頭疼頭暈的毛病,腿腳也有些跟不上。後來,我不再背圖了,分到了炊事班。我是幹革命來的。只要是革命工作,幹啥都行。部隊讓幹啥,我就幹啥!”
“聽說,當年您做的小米飯以沒有沙子而聞名整個晉察冀軍區,聶榮臻司令員曾慕名來品嚐。您還上了報紙,榮獲了“模範炊事員”的稱號!”
說起淘小米,老人興奮起來,眼睛裡放著光,眉毛在抖動,兩隻手在下意識地翻動,連嘴角也在用力地扭動著。他彷彿又回到了當年歲月……
星光下,亮起的那盞不示弱的小燭燈。當年,小米里沙子多,又值連續惡戰,每每是停下來便吃飯,吃罷飯就開拔。這哪還有淘米的時間?戰士們只好直著脖子,容忍沙子和小米一起下肚。見此情景,張德臣愧疚的淚水“吧嗒”“吧嗒”地滴在小米上,好似要衝走米中的沙子。於是,每當戰士們在夜幕的掩護下,抱槍倒頭而睡的時候,他就俯身燭光下,夜夜淘米忙。經常是一淘一個通宵。戰士們說:“咱吃的小米飯粒粒皆辛苦,餐餐情意長呵!”有誰知,張德臣的肚子裡卻裝滿了鍋巴、刷鍋水和野菜……
晉察冀軍區三分割槽舉行了淘小米大賽,各路英豪聚在一起,比賽技藝。一人面前一盆米,一桶水,還有鍋碗瓢盆和臨時開挖的野戰爐灶。看誰淘得又快又幹淨,還必須省水。賽場外早已裡三層外三層站滿了圍觀助戰的指戰員和老鄉。哨子聲一響,張德臣就進入了狀態。淘小米,一般是單手操作。將小米勺在瓢中,加上水後,均勻搖動,讓水帶米流出,將沙子沉澱。只見他兩手配合,一手持瓢,一手拿碗。小米沉在瓢中底部,流水澆在上邊。此時,一邊晃動,一邊澆水。水流成銀線,帶動著金黃的小米泊泊流出。流暢地如織女紡線,如車水流出的清泉。沒有停頓,沒有間斷。盆中的米在不停地減少,小米中的沙粒沉澱在瓢底,淨米被水滌盪著流進鍋裡。這一進一出,小米換了模樣,原來牙磣的令人難以下嚥,現在新鮮閃亮。上鍋一蒸,香氣撲鼻。在近百人的比賽中,張德臣獨佔鰲頭。
頒獎時刻,政委王平親自把大紅花戴在他的胸前。不久,晉察冀報登出三分割槽小米飯大比武訊息。“這天,小米飯剛出鍋。我端起裝滿小米飯的飯盆要出門,一雙大手伸過來,說:給我,我來端。我一抬頭,一看是聶榮臻司令員,連忙說:司令員使不得,使不得!司令員認真地說:“你做飯,我端飯,官兵平等嘛!”接著又說:張德臣呀,我聽說你做的小米飯沒沙子。今天,我是專門來吃你做的小米飯。”
司令員來到戰士們中間,一面招呼大家吃飯,一面自己盛了一大碗,大口大口地吃起來。司令員高興地說:“張德臣的小米飯名不虛傳。要在全區部隊推廣!”
“聽說,做飯不易,送飯更難。每一次送飯都要穿過槍林彈雨,闖一次生死關。您總是說:我是共產黨員,讓我去!您能說說火線送飯的事嗎?”
—— 那一仗打得真激烈呀!部隊據守高山險要打阻擊。鬼子漢奸像蝗蟲般地蜂擁而來。炮彈的爆炸聲連成一片,密集的機槍子彈像颳風一樣,一遍遍從地皮上吹過。樹木折斷,岩石粉碎,濃煙烈火騰空而起。日寇封鎖了上山的道路,部隊山頭上堅守,已經一天多沒吃飯了。先後派出兩名炊事員到陣地上送飯,都犧牲了。
那時,張德臣的傷口發了炎,人燒得暈暈糊糊。正不知白天黑夜,指導員急促地踱步驚醒了他。他似乎明白了戰事的緊急。一翻身,他打起精神下了床。“狗日的,小日本!我今天這條命……”他揣起兩顆手榴彈,背起飯袋搖搖晃晃地衝了出去。他繞路走了另一條隱蔽小道,沿著山縫攀爬。轉過一個埡口,離陣地不遠了。他突然遇見了幾個從後山悄悄摸上來的鬼子。他判斷,鬼子要搞背後偷襲。他大聲喊著:“小鬼子摸上來了,小鬼子摸上來了……”邊喊,邊向相反的小路上奔跑。鬼子見陰謀敗露了,氣得一齊朝張德臣開了槍。張德臣躲在一塊巨石後面,待鬼子靠近後,接連甩出兩顆手榴彈。炸得鬼子懵頭轉向,藉著爆炸的煙幕的掩護,張德臣飛快地跑了。突然,他倒下了,啊,又站起來了又倒下了,又站起來了!“開飯嘍!”他和往常一樣笑盈盈地把飯送到陣地上,戰士們端起飯碗才發現滴滴鮮血已把小米飯侵染。這時才看到,行軍鍋被子彈鑽了幾個眼,張德臣腿上、胳膊上掛了花。
由於天熱,沒穿衣服,老人身上傷疤十分清晰。前胸、後背、胳膊上的傷疤有五六處。左胸前的一處傷疤,距離心臟部位很近。老人指著一處處傷疤數落著,這是打日本,那是打老蔣,那是抗美援朝,每一處,都有著不平凡的經歷!
“該吃飯啦!”楊幹事第三次催促,把我們從歷史拉入現實中。和老人聊了快三個小時了,老人雖然精神亢奮著,但畢竟年歲不饒人,該休息了。我們依依不捨地告辭出來。
醫院院內假山
晚霞象火焰一般燃燒,遮掩了半個天空,太陽就要落山了。附近的空氣似乎特別清澈,像玻璃一樣;遠處籠罩著一片柔和的霧氣,天地間沒有了烈日下的浮躁。綠樹下的陰影變淡了,增添了幾分舒適和愜意。
路上,腳踏車車鈴叮噹,行人們邊走邊談,我還沉浸在剛才的談話中,思緒還在歷史長途中行走,一個念頭反覆在腦海中出現,人們還能看到昨日的天空嗎?腦海裡反覆出現這樣的話:“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三訪老班長
期間,我對張德臣的事蹟做過報道,曾先後發表在《解放軍報》《戰友報》和《共產黨員》雜誌等報刊電臺上。
但瞭解越深迷局越多,要走入老人的內心世界,絕非易事!可惜,那時我已離開報道工作。但只要有機會,我就去看看老人,和他暢聊,做些深入探討。
那次,因為參加全軍演講比賽準備演講稿。我又來到255醫院。抽出晚飯後的空閒時間,我再次來到張德臣家。時近傍晚,正是晚飯時間。家家戶戶已經亮燈,勞做了一天的人們圍坐桌旁,香甜地吃著喝著,空氣中飄散出飯菜香氣,傳播著家家戶戶的溫馨和幸福。
我敲開了張班長的家門。屋中有些昏暗。乍一進屋,眼睛有些不適應。我定了定神,才看清張班長正靠坐床邊養精神。見我進來,老人急忙開燈。一隻燈泡垂掛屋中,散發著昏黃的光線。屋中比較昏暗,能夠看出人的輪廓,但五官有些模糊。老人有些歉意地說:“燈不太亮,反正也不讀書不看報,能看清楚就行了。”是。光線暗點兒,眼睛舒服。因為知道老人的脾氣,我附和著。您這一個月得省不少電吧?“我沒算過。這些年,有電錶。那些年,電隨便使,我也是這樣,能節省儘量節省,習慣了。”您一直保持著老紅軍、老八路的作風,省吃儉用、艱苦樸素。現在社會上時興“一切向錢看”,講究能掙會花,覺著再提艱苦奮鬥跟不上形勢。您沒想著改變一下嗎?聽了這話,老人雙眼圓瞪,鬍子撅起來老高,大聲說:“他說他的,我信我的。我就不服那個氣,那麼大國家發展一般齊,就沒有貧困的了?就是日子過好了,這艱苦奮鬥的作風也不能丟!這是精氣神。我就不信,都好吃懶做,鋪張浪費,國家能發展好?從古至今沒這個理!”
停了一會兒,張班長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反問:“咱是黨員。黨員不能光想著自己,還得替國家想,還得幫助日子不如咱的群眾。你說是不是?”我連連點頭。老人家有主見,一旦理想信仰紮下根,風吹雨打難動搖!我採訪過多名軍隊老同志。多數人家掛著年輕時的英武照片和立功喜報。這不僅是對歷史榮光的珍惜,更是時時自我激勵的好教材。但張班長家裡卻沒有。我便問,知道您先後多次立功受獎,當年的《晉察冀日報》宣傳您是“老模範”。您能不能把光榮史料拿出來,讓我瞻仰學習?“我從來自己不照相。打仗時和進城後也照過幾次,那是記者給照的。我也沒留照片。”他接著說:“快別說立功證書的事。一說,我心裡酸酸的,不是滋味。一九四一年,打曲陽時,因為火線送飯,部隊給記了個大功。我找到領導去‘說理’,戰士們打仗流血犧牲,記個功是應該的。我送飯算個啥,功,我不能要!領導一定要給,我一怒,把立功證書撕了。為此,受到了批評。以後,領導三次給我記功,我就找領導‘辯理’:我張德臣參加革命是為老百姓謀幸福,壓根就沒想要功。我一起當兵的好些戰友,剛才還好好好的,一仗下來,人沒了。他們沒過上今天的好日子。這個功,我能要嗎?要說功,犧牲的戰友最有功!”我默默地點頭。老人的話有一定道理。他認準的理,九頭牛也拉不回。我能說什麼!
據瞭解,從那以後,張班長又立了三次功,再沒見他鬧。原來領導悄悄地把立功卡片放入了他的檔案裡,他根本不知道。
立功,您不要。當幹部,您為什麼也不幹呢?憑您的資格和表現,當個師團級幹部也不算高呀!我又問道。 “說資格麼,還有個小插曲。前些年,清理檔案時,和我一起來到部隊上,參加革命的時間都寫的是1937年1月。可我的檔案中卻誤記為1937年9月。大家說,這一字之誤,差別可就大了。‘七·七事變’前參加革命的,享受紅軍待遇;‘七·七事變’之後參加革命的,享受八路軍待遇。鼓動我去老首長,開個證明,把參加革命的時間改過來。我才不費那個勁呢!紅軍、八路軍都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只要證明我這些年是跟著共產黨走就行了,時間改不改的不吃勁!”
都說“一個不想當將軍計程車兵,不是好士兵!”可您,偏偏不想當將軍,卻既是好士兵,又是老模範。這是咋回事?
“打仗那會兒,首長們幾次和我談起過當幹部這事。我沒答應。我不是拿大。你瞧瞧我這腿。傷好後,走路一高一低的,跑不快呀,咋帶兵?再說,我這頭,兩次摔傷過,不知道哪會兒犯暈。戰鬥打到裉節上,它暈了,部隊誰來帶?首長聽我說的不是沒道理,就這麼放下了。
“建國後,首長又和我談了幾次。說如今不打仗了,讓你當幹部,看你還有啥話說!我說,組織上別再惦記我。如今國家要建設,要發展,需要有文化的年輕人領著幹。我年紀大了,別安排個職務擋著年輕人進步,還是算了吧。部隊整編時,領導又找我說,老張,你資格老,又是出了名的功臣模範,再不安排,我們都無法交代了。這回就應了吧。我火了:資格又不能當飯吃,別以為我資格老就得安排個職務。我革命不是為當官。”
據瞭解,1955年,是部隊第一次大整編,按規定這次不當幹部就得退伍。張德臣堅決服從了組織決定,轉為軍工。但脫軍裝時,人們看到他眼睛裡噙滿了淚花。
常言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而您不愛財。不僅將存錢多次捐給國家,支援國建建設,幫助困難同志排憂解難。聽說,每次遇到調工資時,您總推讓。現在,您每月的工資有多少?
“1955年,組織上準備給我授上尉軍銜,月薪90多元。我不幹。轉軍工時,就比照著這個待遇,要給我定工資。我無妻無子,只有一個老母親,用不了那麼多錢。我情願每月拿61.5元的工資。那錢就不少了。在醫院工人中,我還算高工資呢。後來,遇到過四次調級機會,我雖然夠調級條件,但調級名額有限。國家經濟還不富裕,還是緊著生活困難的同志先調吧。到1984年,我再不同意調級,領導說啥也不幹。組織上硬給我調到69元了。錢多少算多?生活夠用就行了唄!”
您功不要,獎不要,官不要,錢不要,房子也不要,甚至連媳婦也不要。熟悉他的老同志介紹說,打仗那會兒,住在村子裡,老鄉給他介紹過物件。但沒有不透風的牆,首長把他找了去,說現在是戰爭時期,拉家帶口的不便於行軍打仗,再說,這樣會給群眾增加負擔,找媳婦這事不如打完仗再說。就這樣,張德臣的吹了。仗打完了,他都四十多歲了,仍不娶媳婦。首長和同志們急了,張羅來張羅去,他總是推脫,不和人家見面。有一次,又給他介紹了個姑娘,好說歹說同意見面了。可走到半路上,他忽然又跑回到燒火間,說是想起了一個新的改灶節煤方案。就這樣耽誤來,耽誤去,至今還是獨身一人。他這個人哪都好,就是少了點兒人情味。
您終身未娶,到底是什麼原因?是因為身體受傷,不能結婚,還是有什麼別的原因?
“剛進城不久,我還年輕,首長和同志們給我介紹過幾次物件。可我是炊事班長呀,那時國家有困難,醫院日子緊,食堂錢少副食少,既要保障好幾百口子休養員、工作人員吃飽吃好,還要儘量少花錢,每天的伙食不好安排。花錢得一分分地摳,吃糧得一粒粒地省,我哪還有心思考慮個人的事!再說了,搞物件就得結婚。添人進口,要吃的,要住房,醫院有困難呀。咱是黨員,得給部隊分憂呀!我總想,過幾年,等國家建設好了,說個媳婦還困難嗎?就這樣,一拖二拖就耽擱了。一年年的年歲越來越大,我又一次摔傷,腦子的病加重了。一犯病,人事不知。我就想,這媳婦不能娶了。把一個病人往人家姑娘手裡砸,盡是給人添麻煩,何必呢!咱得將心比心是吧。自己一個人過,挺好!”
醫院新貌
我知道,歷任院領導對張德臣格外關心,全院幹部戰士對他十分尊重。每次犯病,院裡都安排他住好病房,捨得用好藥,派專人進行護理。院領導經常來探視。好幾次,他在病危時候,院領導班子成員輪流守候在他身旁。為了生活方便,院裡還從家鄉把他的侄子叫來幫助照看。
那您有沒有不方便和後悔的時候?
剛才,老人高高揚起的頭底下了。人沉默著。我知道,這句話觸到了老人的痛楚。過了好一會兒,老人像回憶,又像在自責:“誰讓你不娶媳婦呢!領導勸了你多少次呀,你就擰著勁。怪誰呢!哎……”看得出,老人追悔莫不及。
我的心隨著老人的情緒變化,一下子抽緊了。像打翻了醬油瓶一樣,五味雜陳。老人家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能說出這樣的話來。不知道經歷過多大的困難和磨難!一個硬漢,並非沒有虛弱和柔軟的時候;一個把一生交給黨的事業的人,並非沒有個人需求。他們和常人一樣,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著這樣和那樣的想法。但,他們不同於常人的是,在決定取捨的時候,會擦乾淚水換微笑,挺直脊樑站成山;會把困難和痛苦、重擔和責任扛起來,永遠無愧自己的信仰和追求!
老人抬起頭來,臉上落出了微笑。解嘲說:“我這是怎麼了?真是老了……”月亮升起來了,灑下一片銀色。院中的樹木花草影影綽綽。張班長家儘管燈光昏暗,卻一直亮著,窗簾上印出一老一少兩個身影。這是新老兩代間的訴說,充滿坦蕩與真誠;這是新老軍人間傾訴,勝利的軍魂在延伸;這是老一代共產黨員對年輕共產黨員的示教,革命的血脈在流動在傳承……
四訪老班長
每一次,看望老班長歸來,我腦子裡總是裝滿了問號。共產黨人應該是什麼樣子?為什麼他會幾十年如一日的堅守信仰?一連串的為什麼,時時出現在我的腦海裡。一個個肯定,又一個個否定,謎一般的人。於是,還想著下一次拜訪,再作進一步探討。
醫院新貌
因為工作崗位的變化,我從機關調到天津一家部隊醫院工作,再見張班長已非易事。
幾年後,一次開會的機會,我又一次來到唐山255醫院。趁著午休的時間,我趕緊去看望張班長。一進樓門,我急切地向張班長家張望。門關著,沒有一絲聲響。我敲了幾次門,沒人搭話。我正在踟躕之時,對門的高大姐開門出來。一見是我,熱情地招呼道:“您來了。”我急忙說明來意,高大姐告訴我,“張班長已讓侄子接回老家了,回去養老了。從那次您來後,時間不長就走了。走了好幾年了……”頓時,我呆住了,心中悵然若失。我真希望這不是真的。真希望那個一瘸一拐的身影再次出現!
我在院子裡尋找。飄落的樹葉,灑下一地金黃。有人在用掃帚“嘩嘩譁”地掃了一堆又一堆。我定睛看,那不是張班長。原來,退休後,這些活都是張班長包下的。他說,我幹了,可以少顧一個打掃衛生的人,多給醫院節省點兒開支。
我在大樓裡尋找。從樓下到樓上,窗明几淨,地板亮的照見人影。有人蹲在地上,仔細擦拭著。我仔細看,那不是張班長。假如,這些建築有知,一定會講述,當年張班長自封“義務保潔員”時,每天打掃衛生起得比太陽還早。
我在醫院的飯堂尋找。大廳中,香氣四溢,鍋碗瓢勺在歡快歌唱。廚房裡忙得熱火朝天,餐桌旁勞動後的人們在盡情地品嚐著美味食品。他們中,缺少了一位怕浪費,將剩飯剩菜裝起來,熱一熱再吃的老人!
張班長,你在哪裡?歲月依然,歷史早已翻開了新的一頁。我問一位年輕同志,知道前些年張德臣、張班長嗎?炊事班的。他搖搖頭,沒聽說過。我問一位中年同志,知道炊事班老班長張德臣的事蹟嗎?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個“老模範”。我問院領導,張德臣的老家在哪裡?他回家後的情況怎麼樣?沒有答案。領導換了一茬又一茬,盡是外來的,自然不瞭解醫院的過去。偶爾,遇到幾位退了休的老醫生、老工人。大家一致稱讚“張師傅是好人”,但說起他為什麼會這樣?大家都表示“不理解”。真的!他太離譜了。奮鬥了一輩子,圖的個啥?“他沒文化,沒文化追求就少!”“他頭腦簡單,一根腸子,想法就少!”“按現在來說,他思想有些僵化,落伍了跟不上形勢!”……我不能說這些看法錯誤,因為我也無法說服大家。
一晃30年過去了。張班長的音容笑貌,他的經歷和他的故事,一直裝在我的腦海裡。總會引發我的聯想與深思。年深日久,閱歷加深,我對張班長的為人,有了新的認識。
張德臣出生在天津北郊區的一戶貧苦農民家,從小沒上過學,確實沒有學歷。他雖然沒有文憑,卻有著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深厚積澱。他一生崇尚節儉。中國古代聖賢認為:“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有德者皆由儉來,儉則寡慾;君子寡慾,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慾,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這樣的做人道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深入人心。正是明白這樣的為人之道,張德臣才注意日常養成,事事節儉。誰能說這樣的德行沒有追求?他要比那些拿著高文憑,坐在高位上,卻幹盡貪汙腐化醜事的人,乾淨的多,高尚得多,可愛得多!他把一生都獻給了軍隊,獻給了國家,獻給了他人,自己卻索取的很少很少。由此,就認為他頭腦簡單、一根腸子嗎?真是大錯特錯!什麼不簡單?就是戰場上的戰情,瞬息萬變,你死我活,生死常在毫釐之間。而立於不敗之地的是,機智勇敢,靈活應對。張德臣歷經百戰之多,火線送飯出生入死。俗語說:“要捉住狐狸就得比狐狸還狡猾。”一個頭腦簡單的人,能夠應付這樣複雜戰況嗎?顯然不能!戰場上,張德臣能靈活應對。而面對個人利益與部隊利益、國家利益、他人利益,卻總是奉獻最多最多,索取最少最少。這是源於他心中的信仰。誰在前,誰在後,他始終如一,一成不變。“我習慣了。”一句簡單的話語,包含著多麼深的內涵!他節約是習慣,工作第一是習慣,幫助他人是習慣,為國家和部隊著想是習慣。這種習慣就是做人知深淺,知底線,嚴格自律的精神!他對個人需求的標準是,越簡單越好;對理想和信仰,致力追求,忠貞不二!這種精神,恰恰是中華民族歷代聖賢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一切,張德臣做到了,而且無愧於歷史,無愧於後人,無愧於共產黨人的稱號!如果把張德臣的言行舉止,看作是跟不上形勢,思想僵化。我倒要問問,作為共產黨員、國家主人,需要緊跟什麼樣的形勢?應當怎樣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錯誤地看待形勢,把揮霍浪費、大吃大喝、極端個人主義奉為時髦,甚至還有的挖空心思,不擇手段地追求權力與金錢。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張德臣依然堅持艱苦奮鬥、勤儉節約,不做位子、票子、房子的奴隸,利益面前先人後己。這是什麼精神?用他的話說:“我是黨員!”他自覺地用黨的宗旨、黨的作風、黨的紀律、黨員的模範作用約束自己。始終保持著很高的定力!
張德臣,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定力,遠遠高於那些身居高位的貪腐者。那些口是心非的蠹蟲,恰恰是在隨波逐流中迷失了自我,失去了共產黨員應當堅守的思想道德底線。
高山仰止,我無法不敬佩、崇敬一位老紅軍戰士、老共產黨員!他使我相信,有的人生來就具備賢者基因,就像高品位的富礦一樣,本身就具備真品多雜質少的特性,再加以開發,就是純度很高的精品。張德臣的本身深藏著許多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經過革命隊伍的教育、鍛鍊、考驗,他身上的品質更加閃閃發光,耀眼奪目!因此,那些,貪官在他面前無不自慚形穢,就連許多修養不夠的黨員對他的行為也難以理解。這正說明黨員思想道德層次上的差別。
“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張班長革命一生,按資格和貢獻,他應該進幹休所養老,為什麼回老家了呢?他的老家在哪?
早年,聽說他是從天津市北郊區(現在的北辰區)跑出來參加革命的。具體在哪個村?不知道。他早年失去父親,離家多年,唯一的親人、母親早已先他而去,老家已沒有直系親屬了,回去後誰來照顧?要知道,他工資不高,身有傷殘,過去多年的存款,除了支援國家建設,就是幫助有困難的同志,自己手頭並無積蓄。他對國家和別人無私奉獻,社會會給他應有的回報嗎?為國傾其所愛之人,理應得到關懷;為眾人抱薪之人,不能使其凍斃街頭。這是起碼的社會良心!我想知道他到家後的情況,我一介平民無力幫助,只有心中惦記他!當然,我相信,他回家後會受到良好的照顧。我雖和他非親非故,萍水相逢,但30年來,我時常想起他。想起他,心裡就發酸發痛。他是革命隊伍中的英雄模範,是把一生無私地獻給共和國的老黨員,是一個無兒無女的孤獨老人。共和國的基石上,有他灑過的血;共和國的城牆上,他是一塊堅實的磚。我們今天的幸福和歡樂,來源和他一樣的那些革命先烈、革命前輩的恩惠!
“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我無以為報,作為晚輩、戰友、一個有良知的人,我一直想去看看他。即使他人不在了,哪怕在他的墓碑前送上一束鮮花也好,以盡心意,略表哀思!
張班長,如果您九泉下有知,聽一聽“東方紅”的歌聲;看一看“革命英雄紀念碑前”的鮮花;伴隨“神舟號”遨遊太空,俯瞰萬里河山。我想欣慰地說,張班長、以及和您一樣的、所有共和國的英烈們、革命的前輩們,人民不會忘記你!實現“英特納雄耐爾”的宏偉理想,薪火相傳,永遠在路上!
張福榮
【作者簡介】張福榮,1972年底入伍,1974年開始從事報道工作。1978年任69軍宣傳處新聞幹事。1980年被聘為戰友報社特約記者。1982年任軍區後勤第八分部新聞幹事。1997年轉業到天津市檢察系統工作。2014年退休。
感謝戰友新報公眾號支援,文圖由作者授權刊發
屈照林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