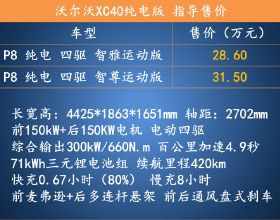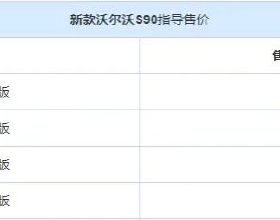我們知道,酷刑一直以來曾長時期地伴隨著各國的社會發展歷程,但縱觀人類酷刑中,我們不難發現,每一個國家各個時期,遭受酷州的人都是少數。像偽滿洲國這樣有如此廣大的人群遭受酷刑,如此眾多的人被酷刑折磨致死致殘,在人類社會歷史上實屬罕見。
在偽滿洲國,僅發生在1943年的“巴木東大檢舉”慘案中,日偽就搜捕愛國志士662人,加上平時抓捕的共計有千餘人,他們都遭到了酷刑折磨。據敵偽檔案記載:巴彥、木蘭、東興等三縣刑訊致死者60人,拘留中死亡者21人,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佔三分之一以上。
日本酷刑的施用物件範圍之廣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凡是被他們逮捕的從事反滿抗日活動的共產黨員、東北抗聯幹部戰士、國民黨和共產國際的情報人員、抗日義勇軍首領和士兵、普通群眾、蘇軍和外蒙古的戰俘,全都是他們的用刑物件。
對前清、民國時期的社會政要、名流,雖然稍有顧忌,但同樣用刑。對觸犯他們利益尊嚴、意志的偽滿軍政人員、親朋好友,只要日本關東軍、憲兵隊、各級日本官吏不滿意,同樣是酷刑相加,即便是犯了罪的日本警察,也會遭到日本憲兵的酷刑拷打。
社會名流
1932年六七月間,原駐哈爾濱黑龍江省鐵路交涉局總辦、東省特別行政區市政管理局局長、愛國老人馬忠駿,本已賦閒在家,因幫助過馬占山抗日,被哈爾濱日本憲兵隊逮捕,並在他家中搜出了槍支。
審問他時,日本憲兵說:“私藏槍支、反滿抗日就是死罪!”馬忠駿回敬道:“年逾花甲,死不足惜!”日寇惱羞成怒,給他用刑,用鞭子抽打他的臉和胳膊。由於查無實據,又因各方面人士聯名具保,日寇只好釋放了他。但同時,確定他為“要視察人”,並派日本特務長期住在他家,對他的一言一行都要進行監視。
偽滿高階官吏
1936年3月末,在偽滿興安省省長會議上,偽滿興安北省省長凌升強烈反對日本“開拓團”移入內蒙地區,反對日本官吏大權獨攬,反對日本關東軍干涉“地方政權”,引起日本關東軍的惱怒。凌升和他的秘書華霖泰從偽滿洲國首都新京回到興安北省首府海拉爾,被駐海拉爾日本憲兵隊逮捕。隨後,凌升的胞弟福齡、妹夫春德等13人都遭到逮捕。
在獄中,他們都受到酷刑拷打,被逼承認“通蘇”的罪行。而日本關東軍給他們確定的真正罪名是“以凌升為首的蒙古人搞蒙古獨立”。1936年4月24日上午10時,凌升、福齡、春德、華霖泰在偽新京南嶺刑場被執行槍決。凌升一案表明,儘管身居省長高位,又是偽滿洲國“建國元勳”,但只要是觸怒了日本主子,等待他的就是酷刑和死亡。
偽滿皇帝的護軍
1937年6月27日是個星期天,偽滿皇帝溥儀的二十幾名“御林軍”——護軍到“大同公園”遊玩,被經常在暗中監視的日本便衣發現。透過密謀,日本關東軍無事生非,蓄意尋釁,抽派一個班計程車兵,由兩名參謀帶領,扮成遊客,假裝來公園遊玩、結果以爭遊艇為由,與護軍打起架來。
日本憲兵跟蹤而至,勒令護軍頭目警衛處長佟濟晌立即交出肇事的護軍人員。佟濟胸是清朝的遺老舊臣,一直追隨在溥儀身邊,忠心耿耿,但官大膽小,特別怕日本人,看到日本憲兵就眼睛發直,四肢癱軟起來。
他本來就口吃,越發急越眨眼,額頭冒汗,臉頰抽搐得幾乎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只有唯唯聽命,惶惶然把那些護軍交日本憲兵帶走。這些護軍在憲兵隊受盡各種酷刑。溥儀回憶說:“護軍回隊後,日本憲兵隊立即用大卡車把他們抓走,施以酷刑,赤體鞭打,灌涼水和辣椒水,打了之後又叫他們赤體跳舞,以為取樂,並且逼他們承認,反滿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