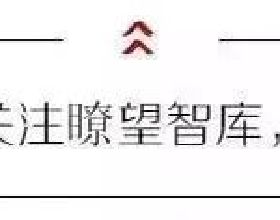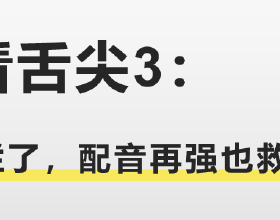來源:環球網
轉自端莊文藝週刊,有刪減 原題:“明清回儒思想正規化”對當下民族文化融通的啟迪意義
編者按:
“大陸新儒家”學者訪談,作為端莊書院新“回儒對話”的系列活動之一,我們近期邀請了三位“大陸新儒家”學者,對他們分別進行訪談。
採訪物件:齊義虎,1978年生於天津,中國當代新儒家學者,1997至2004年在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讀書,獲政治學碩士學位。2004至2005年在天津商學院任教,2005至2007年在北京遊學,2007年至今為西南科技大學政治學院講師。主要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比較政治制度。
訪談策劃:馬文軍,端莊網站長,端莊書院創始人。從事文化創意工作,習行明清回儒思想,當代新“回儒對話”的倡導者。
馬文軍:最近十年國內儒學展現了波瀾壯闊的氣象,從書院、祭孔等活動來看,儒學確實發展得很恢弘、很蓬勃。但與此同時,媒體對儒學的報道立場、以及知識分子對這樣一些與儒家相關新聞的評論,有時候又是持批判立場的。您是怎樣看待這樣一個現象,儒學真的迎來黃金髮展期了嗎?
答:黃金期還言之尚早,套用現在的一句流行語,我覺得是機遇與挑戰並存吧。所謂機遇,就是說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已經狂奔了一百多年,該經歷的都經歷過了,對現代化不再那麼霧裡看花,充滿浪漫主義的想象,而是有了更切實的感受。隨著現代化的深入,暴露出來的問題與取得的成就大體是成正比例的,片面追求現代化的弊病越來越凸顯。中國要實現文明覆興,就要超越以西方模式為代表的現代文明,在推進現代化的同時克服掉現代化的毛病,從而“通古今之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達成和解互補。換言之,看不到片面現代化的缺陷便無法理解傳統文化復興的歷史意義。但由於中國的現代化最初是以反傳統的面目展開的,所以一時半會兒還難以克服舊的思維模式。比如你提到的媒體和一些現代知識分子,他們本身便是現代化的產物,在知識結構和思維模式上具有強烈的西化特徵。在他們那裡,古今是兩極對立的,歷史是線性進化的。這樣一種認知模式便看不到現代化的病灶,更看不到傳統的可貴之處。可以說,媒體與知識界的西化氛圍是今天儒學復興的最大阻礙。要扭轉這一風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馬文軍:今年十一月,端莊書院在北京成立,我們以回儒精神為根基,謀求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以期回儒思想在現代乃至未來中國能有一個大的發展,您怎麼看這個現象?
答:我很讚賞你們的努力。對比世界其他地區的宗教極端化的趨勢,你們的本土化伊斯蘭教顯得更加難能可貴。真理是唯一的,但展現真理的形式卻是多樣的。歷史上曾有過佛教中國化的成功案例,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追求的也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也就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化。可以說,任何一種外來的思想或信仰,一旦傳入中國,進入中國人的生活,在形式上都不得不做出適應性的調整。佛教、伊斯蘭教如此,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樣如此。這不是對原有主義或教義的改變,恰是其在具體時空的落實與展開。原教旨主義的拒不變通只能引起文化衝突,積極融合的中國化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外來思想或信仰的中國化,既是對中國的豐富,也是對其原有思想或信仰的豐富。即便對於儒學這樣的本土文化,雖然不存在中國化的問題,但也會有地域化的特色,更有因應不同時代的變通損益。而當儒學傳到朝鮮、日本、越南這些國家,也分別形成了在地化的特色。儒學不是僅屬於漢族人的信仰,就像伊斯蘭教不是僅屬於阿拉伯人的信仰一樣。儒學可以有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等不同的地域特色,同樣的道理,中國的穆斯林也可以具有不同於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中國特色。當然,對於共同的信仰,我們可以有橫向的借鑑,但更不要忘記縱向上對我們自己先輩傳統的繼承與發揚。
馬文軍:您是從何時起開始關注明清回儒的思想的?您如何評價明清回儒的思想史其義?
答:我大概是四五年前開始關注回儒思想的,可以說是某地的暴力衝突事件使我回頭想去了解一下我們歷史上的伊斯蘭教信仰是怎麼一回事。我希望從古人那裡可以找到克服極端化、實現不同信仰和諧共生的路徑和方法。我覺得明清之際的回儒以儒學來詮釋解讀伊斯蘭信仰,是繼佛教中國化之後的第二次外來宗教本土化努力,可惜的是這個歷史程序沒能繼續下去,隨著儒學在近代被打倒更是失去了可以依靠的文化資源。隨著儒學的復興,希望伊斯蘭教內部的有識之士可以把這個傳統接上,完成先賢未竟的事業。
馬文軍:關於明清回儒的思想正規化,通常的說法是“以儒釋經”“以回補儒”,您站在儒家立場上如何評價回儒的思想正規化?在今天的狀況下,回儒的思想正規化對我們有何啟發意義?
答:中國人對於不同的信仰歷來秉持一種相對開放的心態,正所謂一致百慮、殊途同歸,與其固守一家之說,不如兼採眾教之長。所以歷史上我們常常能看到出入佛老的儒家士大夫,或者入世極深的和尚與道士。這種相容幷蓄的開放性與西方一神教的固執性可以說大異其趣。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狹隘的信徒不惟不能弘道,反而會使人對你所信仰的宗教產生懷疑。與那種過分強調不同信仰之間的異質性因素相比,“以儒釋經”、“以回補儒”的調和性無疑是一種更為理性、平和的融通方式。這種教義上的相互格義比那種刀兵相見的宗教戰爭自然是高明瞭許多。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各宗教之間雖有競爭但卻能和諧共處,從未爆發過西方那種血腥的宗教戰爭,正是與中國人這種開放的心胸有關的。因為我們深深地知道,任何宗教的經典都是用人的語言文字寫成的,語言文字都有其有限性,歸根結底皆不過名相之言筌。為了名相而起爭執、動刀兵,乃是泥於教條、不見大道的法執。明清回儒的思想正規化,不光對今天中東地區的宗教極端主義有預防和化解的作用,對於未來基督教的中國化轉型亦有借鑑和示範的意義。
馬文軍:回儒的思想譜系肇始於明朝中後期,而勝於清初。在差不多同一時期,天主教耶穌會進入中國,代表人物利瑪竇同樣採取“以儒釋耶”“以耶補儒”的方式來會通天主宗教和儒家文化。以天主教的經驗作為參照,您認為,回儒與利瑪竇的思想正規化是否在形式類似的表面下存在著什麼不同?
答:我想最大的不同就是,同樣作為詮釋者,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外來天主教士與長期沁潤在中華文化中的本土回儒相比,其儒學造詣相對而言要低很多,這無疑大大影響了他們“以儒釋耶”、“以耶補儒”的學術品質。所以從結果來看,在義理上“以儒釋回”要比“以儒釋耶”要更成功。當然,如果假以時日,天主教或許也可以繼續完善和推進他們的中國化工作,只可惜這一程序隨著禮儀之爭而中斷了。這也從另一方面提示我們,不論伊斯蘭教還是天主教、基督教,在其“以儒釋經”的過程中,人的因素很重要,只有同時具備深厚的儒學功底和宗教知識,才可能高水平地完成這一融通的工作。當儒學沒落的時候,這一外來宗教中國化的程序自然也就停頓了。隨著今日儒學的慢慢復興,我們希望這一程序能重新啟動,使得中國人可以避免極端化和宗教衝突的威脅,造福中華大地。
馬文軍:我們知道,“回儒對話”這個命題真正被提上國際視野的是港臺新儒家代表杜維明先生,當時引起世界矚目。在“文明對話”框架下的伊斯蘭教與儒家關係以及“回儒”群體的研究,多少修正了“影響——接受”模式下那種文化流動的單一方向,使得兩種文化以平等的身份進入彼此的視野。作為大陸新儒家的一員,您是否有對於這一路徑有相應的思考,它的前景如何?
答:我覺得在中國一國之內的“回儒格義”與中國之外的“文明對話”還不太一樣,前者是中國人內部的義理融通,後者則僅僅是不同族群文明的交流接觸。從深度上來說,前者遠遠高於後者。“回儒格義”之所以能取得那麼大的成就,主要是因為有一批兼跨伊斯蘭教與儒學的卓越學者,他們以一心冶二教,用自己的生命來打通回儒。相比之下,所謂的文明對話不過是自說自話,因為諳習伊斯蘭教的學者也許根本不懂儒學,而熟悉儒學的學者同樣不懂伊斯蘭教,這也就使得深入的相互格義成為不可能,最終大家只能停留在表面的交流上。今後國際間的文明對話若要有深入的推進,還是要靠我們自己先培養出一群兼通回-儒的大學者,這樣他們到國際上去講話發言才會有深度。不過在此之前,我們更需要先培養出一群儒家的經學大師。說實話,自從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經過一百多年的體制摧殘,完整的儒學人才群體還沒有恢復起來,這或許還需要一二十年的教育積累才行。
馬文軍:明清回儒思想的著終極目的是彰顯伊斯蘭傳統的優越性,但對開創中伊傳統之對話,促進伊斯蘭教在中國之本土化,影響深鉅,值得深入探討。請問明清回儒所嘗試建構的中伊傳統之對話,對當代東西文明的對話(或衝突)具有何種時代意義?
答:我想最大的意義就是告訴世人,極端主義並不是伊斯蘭教的正道,伊斯蘭教有開放包容的一面,至少中國的穆斯林可以做到這一點。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極端性或許來自於地域、氣候、個人氣質等其他因素,而未必是宗教本身。只要放棄唯我獨尊,以開放和學習的心態彼此借鑑,就可以避免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化和頑固化。我們應該以人為本而不是以教派門戶為本,允許個人層面的信仰重疊。宗教的目的是安頓人,而不是分裂人。當然,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不止一個民族,能否把回儒的歷史經驗與其他兄弟民族分享,這或許是我們可以去承擔的比東西文明對話更切近的任務。
本文來自【環球網】,僅代表作者觀點。全國黨媒資訊公共平臺提供資訊釋出傳播服務。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