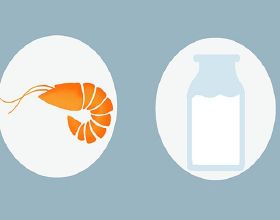著名的學者啊李澤厚在美國去世了,也是90多歲了。注意,是在美國去世。那麼一個學者,尤其是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啊,然後在美國定居,這意味著什麼。
那其實我之前有一個,一個觀點啊,研究我們中國文化的人,研究儒家的人,如果逃離中國大陸,一定是二流的,一定是不入流的學者。實際上李澤厚他也是有這個傾向。
中國文化有兩大基本特徵。一是義理-心性的,二是實踐的。中國文化的傳承有學術和實踐兩條線,但基石是實踐線。儒家義理不僅寫在四書五經中,更寫在人民的實踐中,寫在中國大地上。逃離大陸便意味著遠離中國文化之基石,緣木求魚。因此逃離大陸的中國文化學者、新儒家們一定是淺薄之輩,是見利忘義的學術投機分子。
所以身在美國的“新儒家“余英時有儒家已成遊魂說。不是儒家成孤魂野鬼,而是他自身成孤魂野鬼。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從學術上來講,李澤厚其實屬於民國遺老的這個範疇。當然如果算民國遺老的話,他還是要年輕一點啊。他是出生於1930年。但是在學術上,他確實很好的繼承了這種民國的傳統。
那民國的傳統是什麼?就是否定中國文化、全盤西化。那麼從辛亥革命之後,從新文化運動之後,就在學術上主張全盤否定中國的東西,然後全盤西化。新文化運動以後,中國的學術風氣是這樣的。
研究中國文化的人,也是用西方文化的標準去研究中國文化,那這樣的話其實是扭曲的。包括對歷史。我們現在為什麼會有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就是以西方的標準去看中國的歷史。然後凡是和西方不相符的就是否定她、扭曲她。
那研究中國文化也是一樣的,拿西方的標準當成一個標準了。那其實西方的文化呀,從我們中國的框架來看,他是屬於蠻夷的範疇。
那麼我們知道啊,西方的現代文化、現代文明,他其實有一個基本的背景是什麼,就是去宗教化。那就是從基督教到現代文明,他是有個所謂的世俗化、去宗教化,包括理性化,去宗教化、世俗化他就等同於什麼理性化。那他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那麼從西方的標準來講,現代文明是西方去宗教化的一個產物。但是有一個問題很少人去問,就是說你說去宗教化,你真的去宗教化了嗎,你去宗教化徹底了嗎。所謂的去宗教化的話就是去迷信化,那你真的去徹底了嗎。
那實際上來講,只有站在中國文化的框架下,才能看清這一點。那他是沒有去徹底。現代文明啊,其實是依然保保留了這種宗教因素啊,他只是在形式上來去宗教化。就是打倒神了,打倒上帝了。打倒神打倒上帝,但是你並不是說真正的去宗教化了,不是說真正的就不迷信了。
我們說迷信的話,就是說迷信一個虛構的東西。我們說宗教迷信,那就是說你這個神,你是虛構的對吧。沒有神,現在大家都知道沒有神。那沒有神,你相信他,而且你認為他是世界上最權威的東西,是世界的本源,是世界的創造者和支撐者,那就是迷信。
當然從技術上來講,那麼去虛構這個神,然後讓人去信仰,是有一種教化,道德教化的作用,所以叫宗教。也就是《周易》說的“神道設教”。但是從根本上來講,從這個認識上來講,你是迷信。
西方現代文明他去宗教化,那他認為是一個進步,但是呢,儘管說在形式上,你打倒了上帝對吧,不過呢,在思維的深層,在基本的思維方式,你並沒有真正的去宗教化,沒有真正的去迷信化。
什麼意思,就是現代文明因素中,尤其是現代學術中,那麼他依然保留了一些虛構,一些虛構的概念,而且認為這些虛構的概念,象宗教中的神一樣,是這個世界上最根本的東西啊,是世界的本體。
注意,我說這個李澤厚,他就是繼承了這個民國的傳統啊。就是李澤厚他的研究的套路,其實也是這樣的,用西方文化的標準去看中國文化。或者說把中國文化硬塞進西方的這個框架中。
最典型一個例子就是所謂的“情本體”。李澤厚晚年接受採訪的時候,非常引引以為傲,很自豪的是,他說自己的一個重要的學術創新,就是提出“情本體”。
那麼要真正理解情本體,就要理解西方文明基本的背景。就是剛才我講的,是基於本體論的,是本體化的,尤其是現代西方學術。李澤厚也就認為中國文化也應該有一個本體,努力將中國文化本體化,將儒家本體化,努力為中國文化找一個本體。
於是他就認為中國文化是情本體的。很少人能夠真正的能夠看清楚,這個情本體它到底意味著什麼,包括李澤厚自己。
從根本上來講,我們應該看清這一點,他是拿西方的文化的框架,去衡量中國文化,或者把中國文化套入西方文化。其實是一種曲解、扭曲。所以呢,李澤厚他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是破壞性的而不是建設性的。
我們說歷史虛無主義,他其實是一種比徹底的否定中國文化稍微好一丟丟,也是一種文化虛無主義。
所謂的本體是什麼意思。這個本體啊,屬於哲學概念,那其實他就是神。更準確地說,它就是去宗教化不徹底的一個產物。神的話是世界的創造者,世界的支撐者,而且它是有著人的屬性,與人同性甚至同形。事實上神就是人格化的世界本體。而哲學、科學的本體,只是把神中的部分的人格化屬性去掉了,即去宗教化。
現代西方他說去宗教化,把上帝把神去掉了,他其實只是去掉了一部分,僅僅實現形式上的、區域性的去宗教化。
神的核心特徵之一就是人格化,有人的情感和理性。多神教的神甚至還有人形,有具體的神像和神廟。從多神教到一神教,事實上也是區域性的去宗教化,把人形的部分去掉了,即所謂的去偶像化,實現神的抽象化。從基督教(一神教)到哲學、科學,同樣是區域性的去宗教化,把神的人格屬性的一部分再次去掉,這次去掉的主要是人的情感,而保留了理性。
所以西方近代哲學就是以理性主義開端,其所謂的創始人是笛卡爾。
實際上,我們漢語中是不存在西方哲學中理性主義的東西的,但是我們用“理性”來翻譯它,實為似是而非。理性主義其實不是理性,而是迷信。這個理性不過是神去掉情感後的產物,依然是神的,依然是本體的。
笛卡爾式的理性認為,所有的知識都先驗的存在於理性這個精神實體中。實際上,這個理性就是一個預設、虛構,象對神的預設和虛構一樣,是不存在的。這個理性也象神一樣,是人之外的一個東西,是世界的本體。
然後理性又進入到人的心裡邊去,這樣人也就有了理性,有了知識。
所以我起了一個概念叫“晶片心”。理性就類似於一個電腦晶片,預裝裝了很多的知識,美好的知識。然後插到人心中,這樣人也就有了理性。
理性實為去宗教化不徹底的一個產物,依然是一個類似於神的世界的本源、本體。現代的西方和古代宗教時代的西方一樣,都認為世界不是獨立存在的,人也不是獨立存在的,由世界背後的某種本源、本體所創造和支撐。在古代這個本體是神,現代這個本體是哲學的理性等本體概念,以及科學真理、客觀世界、客觀規律等本體概念。
笛卡爾的理性是本體,後來出現的客觀世界、客觀規律也是本體,嗯這個跟科學有關係了。我們認為科學是最好、最正確的東西對吧,其實科學中依然包含這種本體論。科學象哲學一樣,也是去西方去宗教化不徹底的產物,依然保留著宗教殘餘,宗教式的預設和迷信。
也就是說哲學、科學都是新的宗教形態、意識形態。
順著這個路子,我們才能真正明白李澤厚的“情本體”是怎麼回事。
李澤厚研究中國文化,他認為中國文化很重情感。事實上,這個判斷依然是以近代西方學術的框架審視中國文化的結果。在近代西方哲學中,是把人性三分的:理性、情感、意志。笛卡爾重理性,叔本華、尼采重意志,英國的經驗主義重感覺、情感。
中國講心性,對人心人性的認知是整體的,不會機械地拆分。一個心包括了全部。西方對人性進行機械地拆分,其實也是受宗教影響的結果,或者說是繼承了宗教的傳統,也是去宗教化不徹底的產物。
當李澤厚把中國文化定義為情本體後,就犯了兩大錯誤。一個是將心性窄化,另一個則是將心性固化、物化。
你乍一看似乎是也懂中國文化,甚至還有“學術創新”。
但是呢,中國文化我們是不講本體的,是沒有本體的。我們講什麼呢,我們是講人心的,講心性的、義理的。心性和義理是同一個東西的兩個側面。
人心和本體他是兩回事,截然相反的兩回事。
西方他總是認為,人不是一個獨立的思考主體。我們中國文化最和西方不同的地方是,從文明的一開始,從伏義時代,從易經的時候,我們的老祖宗就意識到,人是一個獨立的思考主體。
人的本質在什麼?在思考,人會思考。人和動物的區別就是在於人會思考,動物不會。這就是人禽之別、人禽之辨。因此,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說某人是禽獸,就是罵人的。也產生了一些這樣的成語:人面獸心、狼心狗肺、豬狗不如、狼子野心、衣冠禽獸、狗仗人勢。
儘管有些動物看似也有很高的智商,但從根本上來說,所有的動物都不會思考,而是按本能來生活。本能就是一套固定的生活程式,而不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改變。而人則會因應環境的變化而變化,而不會固守某種程式。
動物的心才是真正的“晶片心”:都是預裝的固化的程式。而人心不是。
更重要的是,人能夠判斷是非善惡,而且根據這種判斷進行選擇和行動,“善善惡惡”,喜歡善的、厭惡惡的,選擇善的、拒斥惡的。而動物則沒有善惡是非,一切靠本能,有利而無義。
人會思考,能發出思考活動,人的行為就是以思考活動為核心的。那麼我們的祖祖先呢,對這個思考活動進行抽象、進行總結,然後就形成了兩大概念。第一個就是人心,這個心就是思考的器官,也是對思考活動的抽象,就是指思考、思考功能。
還有一個就是義理,義理的更側重外在的在行為中的表現。人的行為是基於思考的、基於人心的,在人心的主導下展開的,是人心思考結果的具體呈現。義理就是指人的行為的合理,而這些理則是人心的呈現,所以人心和義理是一回事。
宋明理學說“心即理”、“性即理”,老百姓說要講理、憑良心。
我們一定要注意,在中國文化中,人是一個思考者,一個獨立自由的思考者。人生的意義就是按自己的本心本性去獨立自由的思考、行動。這就是《中庸》說的“誠者天之道”。“率性之謂道”。
也就是說,人生的意義就在思考,就在保持思考的獨立性,而不受外物的干擾。於是就有了心物之辨的問題。心物之辨的要義就在破除外物對人心的干擾,保持人心的獨立和自由,保持思考的獨立和自由。
我稱之為“心性獨立”、“心性自由”,這是中國文化之要義。
思考就是對思考物件進行思考,而一切外物皆思考人心之思考物件。我們做事的過程中,就是一個和外界、外物接觸的過程,我們就接觸很多事物,要對這些事物進行處理,要對這些事物進行思考。
那麼這個心和物的界限在哪裡?明白心物的界限,是確保心的獨立自由,確保心不受外物干擾的基本前提。
心就是思考,是思考本身,是思考功能、思考活動本身,心之外的一切東西都叫物。
而且這個物啊,不是絕對獨立於人心之外的,恰恰相反,人所感知的一切物都是人心認知思考的結果。因此,物的準確定義是:人心思考的結果。物是人心認知思考的結果。這就是王陽明說的“心外無物”。
你思考,你思考,一旦你下了判斷,有了結論,這個判斷、這個結論就是脫離心,而成為物了。這就是心物之間的界限。這對現代人而言很難理解。
思考是無限靈活的,也是無限包容的,所以我們叫“虛心”,心越虛越好,越虛就越能保持思考的靈活和包容性。而物則是固化的、固定的。一個結論、一個判斷,儘管是主管的,但是也固定了、固化了,就變實了,就是物而不是心了。
一旦脫離心而成為物,這個物就立即成為思考的物件,成為人心的思考物件。
這樣,所有的結論所有的判斷都是物;所有的知識系統、理論體系都是物,包括所有的哲學和哲學概念,包括所有的哲學本體;所有的宗教所有的神都是物;所有的制度都是物;所有的法律都是物……這些東西都是人心思考的結果。
在中國文化中,就是從心物之辨的角度來認知物,而不會去區分唯心-唯物,精神-物質。事實上,西方的唯心-唯物、精神-物質、主觀-客觀等維度恰恰是未能正確人之心性的產物,未實現心性獨立的產物,也是去宗教化不徹底的產物,都包著含宗教迷信因素。
只有人,只有人心,只有思考本身是不變的。人是一個永恆的思考者。物的話就是人心之外的東西,是身外之物,即是可變的,也是不重要的。
西方文明之所以是本體化的,根源就在未能實現心性獨立,未能認識到人是獨立自由的思考主體,未能認識到心的獨立、思考的獨立,當然也無法正確區分心物。
未能實現心性獨立就是心性依附,西方文明一直處於心性依附的狀態。什麼意思,他們總是希望存在一個永恆不變的東西,然後去信仰它、依附它、一拉,以帶來確定感、安全感。這些西方宗教的本質,也是現代哲學和科學的本質。
即西方文明一直是重物而輕心的,一直是有物而無心的,一直是以物為本位的。而中國則相反,是心物之辨的,有物有心,但以心為本,以物為末,以心為體,以物為用。
我們說本體,其實他也是一個物,對吧,他是人心思考的一個結果。一旦你沒有認識到人是一個獨立的思考主體,沒有意識到物不過人心思考的結果,那麼你就會迷信於某一種外物,你比如說迷信神、迷信這個哲學本體,包括現在科學,迷信科學真理啊,將這個技術真理化。
這些都是迷信,這也是西方文明的核心特徵,從古代到現代都如此,只是具體的迷信的物件隨著時代而改變。
因此中國文明是基於心的,而心是永恆的,所以中國文明本身也是永恆的。西方文明是基於物的,物是可變的,因此隨著物的變化,西方就會出現文明的更迭,西方的文明都是短命的。
西方現代文明儘管說名義上去宗教化了,打倒了神,破除了對神的迷信,但是他建立了新的迷信,建立了對哲學本體和對科學真理的迷信,對知識的迷信,對制度的迷信,比如對民主的迷信,對法律的迷信。
現代西方非常重製度,以制度為本位,陷入制度迷信,陷入制度決定論,認為好的制度就是救世主,有了好的制度一切都OK。實際上現代西方對制度的認知,是包含著宗教因素的,是包含著宗教式的預設和虛構的。
沒有認識到就是真理、制度不過是物,不過是人心思考的結果,並非永恆存在的人的守護神。象神一樣,現代的科學真理、民主制度中,承載了西方人的不合理的希望,也都是本體化的。
所謂的科學真理,不過只是一些經驗技術總結而已。所謂的制度,不過是因應具體條件而設計的一個時代的權宜之計,是需要隨時空而損益變化的,而且在制度執行的過程中,更重要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具備獨立思考的人本身。制度是物,是人的思考物件。人才是獨立的思考者,行動者。
所以我們沒有本體論,而只有心性學、義理學。
心和物是兩端,心獨立了,物就不能獨立;物獨立了,心就不能獨立。中國文明是心獨立而物不獨立,西方文明是物獨立而心不獨立。
李澤厚啊,他其實是掉入了西方文化和學術的泥潭裡,當然他也是受民國的這種影響,
以西方的文化為高。其實這個西方文化,壓根就沒有心這個概念,沒有意識到人是一個獨立的思考主體,沒有實現心性獨立,而一直處於迷信外物的階段,一直處於心性依附的狀態。
西方從基督教到現代文明固然是一種進步,其實這種進步,並不比從多神教到一神教更大。哲學、科學認為宗教是迷信,同樣一神教也認為多神教是迷信。從中國心物之辨的視角看,多神教、一神教,哲學、科學和制度主義,都是迷信,迷信物。
也就是說,西方現代文明依然沒有擺脫迷信,只是迷信的方式和物件變了而已。都是對物的迷信,只是所迷信之物變了而已。
我們中國從一開始就認為,人是一個獨立的思考者。你這個制度也好,宗教也好,知識也好,技術也要,都屬於外物的範疇,都是物,都是可變的,都是人的思考的物件,都是人心的思考處理物件,我不會去執著於你的,不會對你迷信的。
未能實現心性獨立,未能讓心讓思考獲取獨立地位,那麼這樣的社會和文明一定是僵化的,一旦環境變化,這些社會和文明因為和物繫結,就無法調整,一定會崩潰。
所以西方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的文明更迭的過程,舊的文明形態不斷崩潰,新的文明形態不斷出現。這是西方的歷史週期率。西方現代文明的出現就是此歷史週期率的產物,而且依然未能跳出這個週期率。
也就是說,現代西方文明會象歷史上曾經存在的西方文明形態一樣,也會崩潰,因為它也是迷信的、僵化的。
這幾年我們看的很清楚,美國的話,面對新冠疫情,面對中國崛起,他無法調整,其根源是他們的思維被意識形態所繫結,無法正確地、事實求實地認清現實,他們迷信於他們的技術和制度,是的整個社會是僵化的。面對新冠疫情,美國只能死人,只能躺平,而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辦法。
李澤厚,其實他的學術上還是屬於民國遺老啊,他繼承了民國的學術傳統、學術陋習,就是以西方為高,否定中國文化,然後以西方文化的標準去曲解中國文化。
現在中國崛起最大短板在文化,而文化崛起的最大短板在學術,學術的短板在學術正規化。中國需要廢掉民國時期建立的西化的學術正規化,而應該以中國的義理-心性為核心,建立一套新的中體西用的學術正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