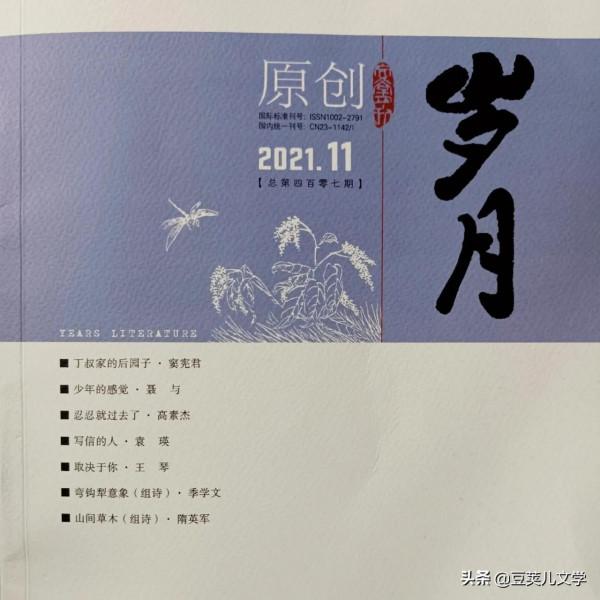丁叔家的後園子
# 竇憲君
今冬的雪大,丁叔家的後園子積了一兩米厚的雪。初春,丁叔把園子一側的雪清開,清出來的雪堆起來像座小山。轉些時日,殘雪還未化淨,又見丁叔在上面蓋了塑膠布,邊角壓上木頭石塊,早春的陽光瞅著金燦燦的,還是冷,這樣做便於土地懷暖,促進新芽早日長出。
年年丁叔家的草莓下來的早,和丁叔下的功夫有關。丁叔每年在草莓上都有收入,年頭不好幾百塊,年頭好了幾千塊,零花錢有了,還能攢點。雖然守著小兒子生活,丁叔老倆口一直自食其力,不討嫌。
丁叔是拙樸的莊稼人,年輕時種大田,老了侍弄小園子。年年我的小菜園子,種什麼,什麼時候種都向丁叔請教。丁叔已屆八十高齡了,除了說話時需要看著你的嘴,身板硬實著哪。他和丁嬸兒在園子裡說話,都扯著高音大喇叭,隔著窗子像欣賞情景劇。許是說習慣了,丁嬸兒和我說話,常常是說上幾句之後,便自覺地放低音量,跟著解釋,我這聲兒都是給你丁叔鬧的,他聾啊。同樣近八十高齡的丁嬸兒,一碗粥一頓飯,瘦成一根線,細細的胳膊每次掄著鋤頭,惹人唏噓。可是,丁嬸兒一直就是這個樣子,不見著生病,多大的風也沒把丁嬸兒怎麼著,見天細著嗓子,甩著高高的調門,和老伴在園子裡進進出出。
丁叔春天忙,秋天也不閒著。秋天的菜收完了,園子中間會出現幾個馬架子,三五米長,趕著便有結對的玉米棒陸陸續續掛上去。結不成對的玉米堆在臨時搭就的平臺上,用不上十天半月,玉米垛便起來了。這都不是自己種的,是撿來的。
都知道,現在的收割以機械為主。原來十天半月的活,如今機器作業,一兩天完事。快是快了,但是收不乾淨。地主也沒辦法,僱人工撿漏不划算,與其讓長了一季的果實爛在地裡不如由著人拾去。年年秋天,出城去地裡拾荒的人不在少數,大多數人肩背手提,而丁叔開電動車。丁叔耳朵不靈,可是有丁嬸兒望風,即使這樣也少不了家人擔心。可是,擋不住。丁叔不服老,種不了莊稼了,去大田裡走一走的念想丟不了,何況還有躲在犄角旮旯的沉甸甸、黃橙橙的玉米棒誘惑著,那可是糧食,管誰種的都不能糟踐。鎮裡像丁叔這樣的拾荒老人很多,有癮似的,逮著空閒,就往野外奔,去了就有收穫,家裡喂個小雞小鴨什麼的,省了飼料錢。
丁叔撿來的玉米在園子裡曬了一冬天,草莓的活撂下,又開始收拾玉米了。
丁叔家撿來的玉米棒用手工脫粒兒。小時候我也幹過。媽媽買來幹玉米棒,手邊放了大盆,家把什是一個木製的東西,叫穿子,長長的,見方,正面中間部分有個槽,裡邊嵌一個鐵製的倒戧刺,玉米棒順茬對著推,一會就是一棒。媽媽弄得飛快,我卻使不轉,使出吃奶的力氣,玉米和玉米核就是咬死了不分開。媽媽抹著汗說,不急著幹,長大了不學就會。現在看丁叔幹,丁叔臉上汗津津的,手和脖子爆出青筋,丁嬸兒在一旁用瓢舀出脫掉的玉米粒兒,裝進袋子。老倆口乾活默契,一輩子柴米夫妻做過來,眉眼高低不用指使,自然著哪。丁嬸兒說,幹活有好處,累點吧,能多吃飯,活著就得勁兒。
玉米離了核,還有溼氣需要晾曬乾淨。丁叔將成袋的玉米裝車,從自家出來,繞一圈,曬到一杖之隔的王家房子前面的水泥地上。做這些活時,丁叔小兒媳婦來幫忙了。如此多出一個人聲,三個人喊,就是比兩個人氣勢,聲浪一波一波,聽了也不覺得鼓譟。玉米一天曬不好的,趕上好天曬兩天,遇上孬天氣,陰一陣兒,陽一陣兒,吃不準,來了雨,春風又浩蕩,曬出去的玉米少不了折騰幾個個,直到完全進了倉,頭年秋天的心思,才算了了。幹這些活時,丁叔難免數落老天,罵是沒有的,莊稼人迷信,天老爺是罵不得的。
天漸漸變暖後,朝陽的土地完全化透了,窗外又傳來了丁叔刨地的聲音。去年的壟溝變壟臺,灑在表面的烏黑的農家肥,被翻到土裡。培好的壟沉上一兩天,就見丁嬸兒拎個小筐往土裡按蒜種了。這時丁叔不插手,揹著兩手跟著。蒜種的遠近丁嬸兒說了算。老兩口不交流時,畫面靜好。春陽透明,春天的秀色還遠,丁叔丁嬸兒穿土色的衣服,臉上沒了光彩,閉塞的小園子裡,兩個風燭殘年、暮色將至的老人像幅黑白照片,靜靜地掛在時光這面透明的牆上。
丁叔家的日子殷實,家大業大,是丁叔引以為傲的地方。老一輩口中的家業,不是銀行賬戶裡的數字。丁叔的家業,分房子前面的園子和房子後面的園子,房子也要分老房子和新房子,另外還有倉房、庫房,細數真要數一陣子。丁叔老倆口住老房,兒子住新房,老房子是土坯的,這樣的房子早就少見了。房子低矮,但是保暖。以前吃水在一組,輪流收水費時,我每年都會去一次,去一回就時光倒流一回,尤其是依舊保留的老式的大鍋灶,見了眼前便有影像出來。想想,過年孩子們回家,除夕夜大鍋煮餃子,立時就煮出了節日的團圓和熱鬧。後來自來水按人頭單獨收費了,沒特殊事幾乎沒走動,雖然和丁叔一杖之隔,大門衝著的卻是兩條街,距離還是有的。不過,只要天暖了,隔著窗戶,隔著杖子,都能說上幾句,家長裡短、陰晴圓缺的,不耽誤。一等草莓下來的時候,想吃了,衝著丁叔家的房子喊幾嗓子,應了,遞個盆過去,稱幾斤新鮮的草莓。丁嬸兒會客氣,但是,錢是一定要給的。
春末夏初,丁叔的後園子裡基本上種得齊全了,草莓旺盛地結著果,黃瓜、豆角、茄子、辣椒、西紅柿,參差著長,包括地壟溝裡的小白菜、小菠菜,也搶在黃瓜豆角上架之前風光一把。丁叔見天出沒在菜園裡,草莓下來的時候,得忙上一個月,採摘,售賣,丁叔和丁嬸兒忙得腳打後腦勺。採摘草莓的活不輕巧,通紅的草莓果躲在葉子底下,每一顆都需彎著大腰翻找,瘦小的丁嬸兒有時候蹲在地裡,草莓的秧苗再高一些,不仔細瞅都瞅不著。
摘草莓的時節是丁叔家後園子最熱鬧的時候。兒子兒媳閒了都來幫上一把,丁叔最小的孫子上大學了,草莓地裡跳躥的變成丁叔大女兒的孫女,當了太姥爺的丁叔和小傢伙一老一少,一唱一和,標著高音兒鬥嘴,粗聲細聲,瞭然成趣。
我眼中的“小人物”
————《丁叔家的後園子》創作談
我一直生活在小鎮,慢慢喜歡上小地方的好。年輕時需要熱鬧,眼光也輕佻,好多人和事看不見,寫的東西也花哨,漸漸就靜了,漸漸發現,那些淳樸的人,那些沒有大作為,將日子連在一起卻能織出花的人就在自己的身邊閃耀著。他們有進退,有操守,不辭勞苦,和土地共榮辱,養兒育女,不聲不響,活成和土地一樣的顏色,最後被土地淹沒,彷彿從沒有來過這世上。
但是,他們活生生地存在著,被看見的幸福和煩惱,就在我的眼前呈現。我想記錄下來,也應該記錄下來,他們不只被天空看見,不只被土地熟悉,也應該留在世界的文明史上。他們是我們這個民族,也是人類安定、祥和的根基,是我們後世子孫應該感激的先輩。
像丁叔、丁嬸兒這樣的人很多,他們不介意會有人寫他們,不介意勞作之中會有一雙眼睛在看他們。他們活得自我,活得不知道什麼是境界,他們就用生命的本色活,用最原始、也是用最恆久的、對生命本能的感知回應這個世界,發現美,創造美,而不去探討美。他們的可貴,如水利萬物而不爭;他們的可愛,如雨潤萬物卻無聲。
我欣賞他們的世界,簡單的快樂,一餐一飯,一朝一夕,善待天地,厚愛生靈,自然的生長是經營人生的冷暖,理性、自覺,自給自足。沒有豪言壯語,無大起大落,不為人傑,凡事泰然。殊不知,和平之樂,就在他們的身上奏響。
作家劉震雲先生對大小人物有過這樣的詮釋:“我只不過把被弄顛倒的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概念再顛倒過來,讓他們恢復正常。”我贊成他的說法,也為此做著努力,真實地寫出他們,《丁叔家的菜園子》的初衷,就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