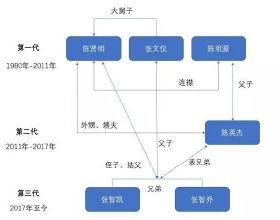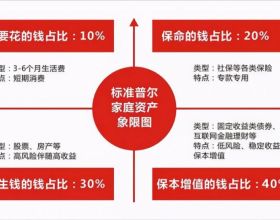三十九年前,也就是1970年,我可以清晰地記得,那是一個夏天的傍晚。
一個小夥伴來到河邊,急匆匆地把我叫上岸來。
我們長期堅守一個約定,無論是誰,只要碰到有趣的事情,都要通知彼此。
我被我的小夥伴叫上來了,一問,村子裡來了一個奇怪的人,是個女的,她不停地說話,卻沒有一個人能聽懂她說的是什麼。
我和我的小夥伴就開始跑,在奔跑的過程中,我們的隊伍在壯大。
這也是鄉村最常見的景象了,孩子們就這樣,一個動,個個動。
等我們來到目的地,一群孩子已經拉出了一支隊伍,把當事人的家門口圍了個水洩不通。
村子裡真的來了一個奇怪的人,是個女的。
等我們來到這裡的時候,這個女人已經不說話了——她說過了,哭過了,現在已經疲憊了,她在休息。
顯然,她是不受歡迎的,她的屁股底下沒有板凳,她只是就地坐在一個石磙子上。
然而,儘管屁股底下沒有板凳,我們也不敢小覷她——她雪白的襯衣,筆挺的褲縫,塑膠的、半透明的涼鞋,尤其重要的是,她優雅而筆挺的坐姿——毫無疑問,她是個城裡人。
這個城裡女人就那麼坐在石磙子上,一動不動,滿臉都是城裡人好看的憂傷。
老實說,我不是看城裡人來的,我也不是看憂傷來的,我一心想聽她說話。
我的小夥伴剛才氣喘吁吁地告訴我,她的話“一個字”都聽不懂——這怎麼可能呢!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我的小夥伴的話很快就得到了證實。
休息好了,這個女人蹺起腿,開始說話了。
她的聲音並不大,但是,在寂靜的鄉村黃昏,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聽見了她在“說”。
她一個人說了很長時間,真的,我們一個字都沒有聽懂。
那麼她的“說”還有什麼意義呢?她的“語言”還有什麼意義呢?
毫無意義。
我很快就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的周圍沒有一個成年人,甚至連房子的主人都不在,他們家的小兒子也不在。
鄉下的孩子往往有一種特殊的本領,他們可以從成年人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情。
我很快就知道了,人們其實在迴避這個城裡女人,她來到我們村絕對不是幹好事來的。
她究竟是幹什麼來的呢?
女人一直在說,說著說著,她哭了。
我一直覺得,城裡的女人是“不會哭”的,她們只會流淚,只會發出一些痛苦的聲音。
鄉村女人的哭就不一樣了,她們的哭有固定的節奏,有確切的旋律,邊哭邊說,準確地說,是“哭訴”。
她們的哭有許多實際的內容,而不只是表達悲傷的情緒。
正因為城裡的女人“不會哭”,她們的哭往往叫人揪心。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我很難過。
我注意到她試圖問我們一些問題,但是,誰知道她說的是什麼呢?
事實上,我們也和她說話了,但是,她同樣聽不懂我們的語言。
我們近在咫尺,其實來自不同的世界,彷彿陰陽兩隔。
也許是由於絕望,這個城裡女人坐在了地上,然後躺下去,在地上一心一意地哭。
她徹底顧不上城裡人的體面了,像一個潑婦一樣在地上打滾,一邊滾一邊說。
此時此刻,我們只知道她痛苦,卻永遠不知道她為什麼痛苦。
我至今記得那個夏日的午後,一個陌生的、城裡來的女人把她所有的悲傷留在了我們村。
沒有人能夠幫助她,沒有人知道她為了什麼。
這個女人後來是自己爬起來的,她撣了撣土,整理了一番頭髮,一個人離開了。
她再也沒有在我們村出現過。
後來我們知道了謎底,事情一點也不復雜,她是來尋找她的兒子的。
那個我們都認識的、沒有露面的小男孩,其實是她的兒子。
她兒子是被拐來的還是她和某個人私生的呢,我沒有得到進一步的訊息。
村子裡所有人都對這個問題三緘其口。
偶爾也會有人提起那個孩子的身世,但是,言說的人一定會被阻止。
這阻止不是大聲的呵斥,而是一種不動聲色的目光,是告誡——這是鄉村的又一種文化了。
好多年之後,我意外地得知,她是江南人,她來自蘇州。
現在,我用一句話就可以把那件事說清楚了:三十九年前,一個蘇州女人來到蘇北的一個村莊尋找她丟失的兒子,沒有人能聽懂她在說什麼,她最終消失在我故鄉的夜色裡。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蘇州與我的蘇北村莊相隔多遠呢?也就是兩百公里。
但是,在這“也就是”兩百公里的距離之間,有一樣東西,它叫長江。
毛澤東有一句詞,是描繪武漢長江大橋的,曰:“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
毛澤東詩詞一直都是這樣,氣度非凡。
但是,詩詞的氣度往往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意象的開闊。
毛澤東所選用的意象是什麼?是長江。
這是一條綿延的、深邃的江,它劃分了南中國與北中國。
長江同時是中國地理的分野、語言的分野和文化的分野。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當她的文化足夠豐富的時候,這文化必然是多樣的、多元的。
豐富啊豐富,你是華光,也是業障。
所以,在整個農業文明時期,長江不叫長江,叫天塹。
天塹強調的是分,刀劈斧鑿一般。它具有洪荒的、絕望的氣息。
當洪荒的、絕望的阻隔之間出現了連線時,我們可以想象一個浪漫主義詩人的豪邁。
“天塹變通途”幾乎就是脫口而出。這是一種令人喟嘆的欣喜,它所指的不再是分,而是交流上的無限可能。
可事實上,無論是科技還是人文,就我們人類所達到的高度而言,“天塹變通途”的可能性早就存在了,我們只是習慣於蔑視交流的可能性。
我們一邊在建造大橋,一邊在積極地劃分“兩個世界”或“三個世界”。
兩個世界,三個世界,一個優雅女士的就地打滾,一個傷心女人破碎的心。
三十九年過去了,我現在居住在南京,從我的窗戶望出去,腳底下就是長江。
它不是天塹了,再也不是了,它只是一條江。
老實說,我是喜歡這條江的,它是我最好的風景。
可是,在風景的遠處,我始終能看見一個蘇州女人,她在“說”,一直在“說”。
作者:畢飛宇。來源:《讀者》雜誌2018年第20期,原標題《好看的憂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