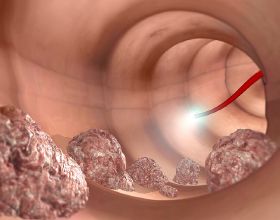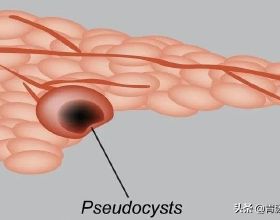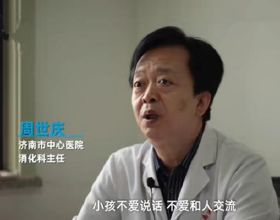各位朋友:
這是“我怎樣寫瑜伽”系列的第四篇,集合了有關山林間漫步的一些手記,似乎跟瑜伽關係不大,不過我覺得在實質意義上,這與瑜伽是息息相關的。閱讀愉快。
*本合集約3300字。
01.
你有沒有一個人走在山中,四顧無人,只有鳥在看不見的樹尖,嘰喳叫幾聲,有點瘮得慌這種體驗。參加過一些呼吸法課程,而最近幾個早晨開始覺得,找一片安靜的山林漫步,差不多已經是好的呼吸練習了,甚至是基礎性質的——為什麼過去人跑到深山裡去,除了苛政猛於虎的理由,一定還有個清晰的道理。
就是在人群兒裡待久了——更別說大都市裡,那是人海——會有一種幻覺,即一切是人為的、人有的、人用的。練個瑜伽,也是在人造的房間裡,站在人造的墊子上,呼吸著淨化器出來的空氣(或者外面人造的霧霾),聽著他人發出的指令……
某種意義上這也不壞,但是,似乎只有獨自面對自然的時候,有著純淨特質的山河、大海和天空,讓人輕易認識到“人”並不是它的目的,人只是這個龐大體系的一部分。說到底,你也只是被創造的,你能懂的和能“控制”的何其之少,樹頂忙著談情說愛、養家餬口的各種鳥也是這麼看我們的吧。
回到山裡,除了還穿著衣服鞋帽,差不多回歸一個人本來面目的時候,很神奇地,你的呼吸就會比以前好一點。正如有學者說的,動物和野人什麼體式和呼吸法都不用練,一切都正常著呢。
當然我不是想做隱士,田園牧歌只存在於想象,還是要回來吃飯的……(2019.11.29)
02.
“看它們在那兒吃東西,就很開心。”可能養寵物的都有這種體驗吧。其實看原生態動物的“吃播”更好。
今天中午,我在山上看一群灰鳥吃漿果。它們幾乎不叫,噗嚕嚕地施展樹頂上的瞬身之術,尤其向高處樹枝躥升的時候,那動作介乎跳躍、奔跑、飛行之間,肉眼難以捕捉,帥得不得了。人要去吊威亞,哼哧哼哧模擬的移動方式,是這些傢伙的日常。
我有時候想,時不時目擊這種絕非人造的原始生命力,安排一些屏息凝神的圍觀時間,是非常有益的,你會不自覺地想,人就要能吃能睡啊,人本來也是自由的啊,人就要趾高氣揚啊,為什麼不呢。(2021.06.17)
03.
你沒有碰過含羞草的話,是一個小遺憾。隨著一隻手指的觸碰,它那羽毛狀互生的小葉子敏感地合攏,很像收起翅膀的一個奇異蟲類——據說其反應速度快到0.08秒。
如果你手掌懸停在幾片葉子上方,這一點點熱量,也足以讓一個葉柄整個向後避開,柄上所有葉子同時間關閉。難怪催生了“含羞”“怕醜”等擬人稱謂,也可以想象正要啃食它的動物,此時完全懵掉的表情。這到底是一株小草不是啦?
事實上,它曾改寫科學家對動植物區別的認知。路邊的花草樹木如果瞭解多了,很難不為它們沒來由地高興,更不要說“林間自在啼”的鳥,在樹枝上像忍者一般追逐的松鼠……(2021.06.30)
04.
傍晚見到了傳說中的黃猄。循著幾次窸窣的跳躍聲,轉眼瞧見它的時候,它已經跑到幾十米外,想必是這傢伙認為的安全距離。回頭打量著我們,瞪著清秀的黑眼睛,膘肥,腿細,帶白條紋的尾巴比想象中長。然後三跳兩跳,不見了。它們也是白雲山的“原住民”,屬於野山羊的一種,能見到自然狀態下的真容,太好了。(2021.08.17)
05.
那位靠樹的大爺,又在山上嘣嘣嘣地練功了。光背撞在樹幹,整棵樹都在抖。我淺薄地想,這或許對椎間盤和那棵樹都不好,健身的作用,說不定源自他在山裡跑來跑去,而不是撞擊。
看著可能已經失去生理曲度的脊柱,念及老人家令人豔羨的意志力,我想,這前前後後會是一個好故事吧。
最近對“好故事”有所反思。大陸觀眾很容易為一個好故事感動,爛片太多了,畢竟多數影片的商業邏輯本不是講好故事,而是挑逗、按摩人膚淺的情感,然後以量取勝,這似乎無可厚非;但誠實一點說,讓小眾推崇的,往往也不過是“不太爛的故事”,包括我,對真正的好故事是葉公好龍那樣的……
好故事來到眼前,需要一個人耐心地目測善惡的深度,長久地凝望未知的深淵,體驗感不總是愉悅,完全可以是困惑,甚至不適的。所以欣賞好故事,不需要隨時準備好膜拜,而是儘量準備好自己。(2021.08.23)
06.
全然地行走,感覺妙不可言。實在要描繪,就是通透、安心,同時一點不累。我有一點能理解每天早晨堅持“熬湯”的人們了。(2021.08.27)
07.
“一個人的大多數心理問題,都是每天凌晨5點跑10公里能夠緩解的”,這話有點意思。不是說不需要在精微一點的層面上了解自己,也不是提倡過度運動,而是說,“堅持”二字完全是看人下菜碟,你輕佻對待,它很快讓你感到厭煩;你認真對待,它會給你豐厚的回報。一個看似簡單的事情,比如寫字,堅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它跟別人做的絕對不是一碼事了。(2021.09.17)
08.
在山上遇到唱歌的、拉琴的、吹笛子的,各種愛好音樂的人們,不通音律如我,有時會為之停留,有時會趕緊走人。音符與他自己是否有深入關聯,是否成就瞭如臂使指的自如表達,還是不難體會的。只要不被刻意篡改,原裝的感知一般沒有大問題。
昨天恰好聽到戴建業講蘇軾的“江城子”,他說著說著,眼圈泛紅,聲音哽咽,以至於草草結尾,但我想這是“懂”詩歌的,在瞭解詞句背後廣泛資訊的基礎上,他的“我”完全在場,於是心意相通,情感共振,自然而然有了活的表達,不會淪為應付差事或者炫耀。明乎此,技術層面就是“考的全會、蒙的都對”,甚至錯也得分了。(2021.09.18)
09.
羅琳構思的神奇動物,有一種鳥蛇,喜歡填滿一個空間,大到百貨大樓,小到一個茶壺,體型大小變化自如。我忽然想,這靈感可能是來自人的“知覺”。
為什麼整天關在屋裡的人,忽然面對壯闊自然景觀之時(比如山林、江海、星空),猛然覺得精神舒展,心意自由?頗為類似。至於自然景觀可以改善人的健康指標,這類研究結果沒什麼好驚訝的。
有意思的是,鳥蛇一個產地設定在印度,羅琳可能是再一次從這種長於神話、宗教與意識研究的文化汲取了靈感。當然借鑑更明顯的角色是大蛇“納吉尼”,直接是從梵語雌性蛇nagi衍生出來的,電影也是找了個東方美女來演的。(2021.10.15)
10.
嬰兒的凝視,幾乎永遠是動人的。再平常的東西,一朵小花,一隻蝴蝶,一個玩具,都可以激起全部的好奇,睜圓忽閃的大眼睛看許久,不覺亮晶晶的口水流下來。
其實成年人應該保留這種“赤子”般的體驗,找到機會,去凝視叢林深處、水波深處、星空深處,當然還有時間深處……只是好奇、讚歎、遐想之中,不會淌下口水。
走在活了幾百年乃至千年的大樹下,抬頭看它依然枝繁葉茂,已然見過了幾十代人,還將繼續見證下去。於它而言,或許我們就是“夏蟲”“蜉蝣”一般短暫的存在,往好聽了說,就是小孩子吧。這樣也好,保持好奇的凝視,不虛無,也不虛妄。(2021.10.17)
11.
閱讀一大樂趣,是看到開啟想象空間的問題。比如一位植物學專家提出,有一些蘭花會欺騙昆蟲傳播花粉,同時還不給昆蟲提供花粉、花蜜之類食物,那麼昆蟲對此是否“知曉”?會不會不為吃喝,只是來娛樂一番?進一步,蘭花的欺騙行為,除了繁衍之目的,有沒有找一個小玩伴的意思?其實你想,不論是否存在實質上的意圖,單是“欺騙”用於描繪植物行為,就已經令人遐想了。(2021.10.29)
12.
“吸取天地靈氣”,古人修行語境的這種表達,想必是伴隨“觀想”的能量、意識層面練習。不過現實中有多少流於忽悠和調侃,多少獲得了成果,很值得懷疑。
我要說的是,可能古人沒有意識到——他們也缺乏今天的知識來意識到——植物的生存方式,就是“吸取天地靈氣”啊!
它們向上延伸,吸取陽光;向下紮根,吸取水和養分;加上空氣,就創造出數不盡樣式的枝葉、花朵、果實,繁多的自我複製方式,驚人的空間佔領策略,順帶為動物提供食物、居所和寶貴的氧氣。它們沒有行動器官,卻可以覆蓋廣大的土地;它們沒有大腦,卻可以相互通風報信;它們默默無言,卻享有動物難以企及的“壽命”……
很大程度上,它們更像是天地之間的主宰,而動物是其附屬。我不是什麼“主義者”,也不是什麼修行人,只是越來越覺得,經歷和觀察不夠、知識和理解不足,自認的身份標籤都還嫌早,或者說,可憐地被侷限了。(2021.11.02)
13.
“有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魯迅這話,從植物學來理解,是代表了我們日常概念裡的誤會——植物的“個體”,跟動物以及人的“一個”意義不同,前者更像是某種“統合體”。
比如常見的,一個枝條被剪下來,插在土裡,長成另一棵完整的同類。細一想簡直像外星生物……你能想象楊過的胳膊被砍下來一條,長成另一個神鵰大俠不?
大家總難免用動物的思維談論植物。又好比爬山虎,事實上它們的“動作”是成長和繁殖(除了含羞草那種奇葩)。反正植物複製“分身”是稀鬆平常的,站在古老的榕樹下,你選用代詞“它”或者“它們”都對。東方傳統修行裡不乏“分身”的討論,我覺得沒有人們身後的花草樹木來得嚴肅。(2021.11.04)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