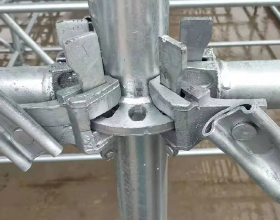長城是中國歷史上一項偉大的工程,不僅在中國家喻戶曉,且在國際上享有不凡的知名度,據稱美國阿波羅11號登月飛船上的宇航員曾說,在太空能夠看到的人類工程只有中國的萬里長城與荷蘭的圍海大堤。長城就像它腳下的土地一樣,無論為人所知還是不知,厚重的歷史永遠有著磁鐵一樣的吸引力,令人駐足、深思。
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與明長城幾乎處於相同的位置,而農牧交錯帶不僅是農田與草原兩種不同環境的過渡地帶,也是農耕與遊牧兩種經濟生活方式的結合部。歷史上,發生在這一地帶的戰事,不同於農耕區內部東西、南北之間的爭鬥,而屬於農耕民族與草原民族之間的軍事爭鋒。
長城以南有密集的人口、適宜耕種的農田;長城以北人口稀少,草原荒漠之上民生所繫為畜牧業。長城南北有著完全不同的自然環境與人文風貌,長城則是兩者之間的過渡帶。
在當代中國年降雨量分佈圖上,400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線東段與明長城走向驚人的相似,這一點告訴我們,正是降水這一制約種植業的關鍵因素決定了長城所在位置擁有過渡地帶的特徵。400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線是農耕生產對於水資源需求的底線,這條年降雨量線以南為半溼潤區,以北為半乾旱區,兩個不同性質的環境地帶在雨量因素的制約下,不僅表現出農田與草原、荒漠的差異,同時也造就了農民與牧民的區別。長城界分農、牧,而自身卻是真正的過渡地帶,既不屬於農耕民族,也不屬於非農耕民族,無論經濟生活方式還是人們的社會風貌均具備明顯的農牧兼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徵。
在這樣的地帶修築長城,從戰國時期直到明代陸陸續續延續兩千多年目的是什麼?對於這一問題已經有諸多討論,傳統且主流的觀點認為長城是抵禦北方草原遊牧民族南下的軍事屏障,是用以限制漢族的活動範圍。所以將長城修建在農牧過渡地帶的決定力量來自於農耕民族,漢民族的活動範圍決定於農耕生產對環境的適應,因此長城的位置既是漢民族以及漢化的少數民族依託農耕生產定居的底線,也是農耕生產的底線。
漢民族試圖用長城這一人為的工程擋住北方民族南下的馬隊,但歷史證明,長城的出現並沒有真正終止農、牧兩種力量的較量。
自戰國至秦漢時期匈奴人帶著草原民族特有的雄豪,躍然於中國歷史文獻記載之中,此後烏桓、鮮卑、柔然、羌、氐、吐谷渾、突厥、回紇、吐蕃、鐵勒、契丹、女真、蒙古、滿人……這些來自於長城以外,活動在草原上、森林中的非農業民族,如同搶灘的浪潮,倏忽之間來到長城之下,又旋即呼嘯而去,不僅將金戈鐵馬、烽火狼煙留在塞上,而且也為後人留下許多思考:歷史時期長城地帶的戰事究竟是土地之爭還是民族之爭?
在內陸亞洲,匈奴帝國將遊牧部落組織為一個統一力量,透過從草原外部獲取資源。在戰時,單于發動突襲,為他的追隨者和匈奴國家提供戰利品。在和平時期,單于扮演了中原與草原之間中介者的角色進行貿易,並透過貴族制度對漢地物資加以再分配,獲得了其他政權所未曾獲得過的穩定性。
面對草原民族的南下,經營定居生活的中原王朝最初無力出擊,長城即成為戰略守勢的產物;當歷史進入西漢中期,漢武帝“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設定河西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如此舉措導致“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武帝的戰略在於斷匈奴右臂以絕其援,此後唐王朝乃至清朝更進一步圖謀擁有草原,並在阻遏草原騎兵南下的同時,實現版圖擴充套件以及與西高東低地形一致的高屋建瓴的政治戰略。經過近兩千年的努力,至乾隆年間才最終將大清帝國的版圖穩定地擴充套件至亞洲西部山地與草原的邊界,並實現了“農耕地區對草原的還擊”。
無論西北或東北的民族還是中原民族,長城所在地年降雨量400毫米的地理環境決定了這裡首先成為農耕民族守疆保土的底線,然後成為農牧雙方交鋒的戰場。南下突破這條界限,鮮卑、匈奴、氐、羯、羌、契丹、女真、蒙古、滿等民族均在農耕區建立過政權,固然中原王朝曾時斷時續將權杖伸向草原,但作為農耕民族的代表,最終越過400mm等降雨量線,將田園與草原統為一體的卻是來自東北森林草原地帶的滿人。
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些戰事早已遠去,無論從西向東、從北向南還是自西北、東北向中原,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地理不僅僅是展現歷史的舞臺,而且是推動歷史的基礎。而真正的地理既可以顯山露水,也蘊藏在人們的生產活動摸索中,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線即是如此。把握地理之根本,運用於戰略之中,不僅能夠克敵制勝,而且可以成就宏基偉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