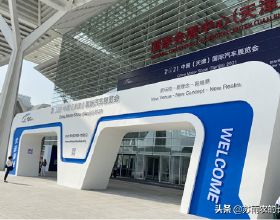1926年8月底,魯迅來到廈門大學教書,過得很不如意,百無聊賴,便寫了很多回憶文章,取名《舊事重提》。11月18日,他用清冷沉鬱的筆調,回憶了和昔日老友範愛農的瑣事,以及範愛農悲慘的遭遇。全文語言樸素,感情真摯。
範愛農,名肇基,字斯年,號愛農。浙江紹興黃甫莊人,生於1883年,比魯迅小兩歲。父親是個“紹興師爺”,在他三歲時去世了。母親帶著他和妹妹寄居在叔叔家,經常被嬸嬸羞辱嘲罵,母親不堪其辱,在他五歲的除夕夜吞金自殺了。範愛農兄妹跟著祖母艱辛長大,1905年,徐錫麟和秋瑾在紹興開辦大通師範學堂,22歲的範愛農前去報考,並被錄取。範愛農勤奮學習,成績優良,深得徐錫麟青睞。同年年底,範愛農跟隨徐錫麟夫婦赴日留學。魯迅前去迎接,兩人就此相識。
1907年,徐錫麟發動安慶起義,失敗被殺,範愛農作為同黨被清廷取消留學費用,無奈回國,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只好躲在鄉下,教幾個小學生餬口,還曾被清廷派人抓捕,倖免。1909年,魯迅回國,在浙江杭州兩級師範學堂教書,第二年,在一次同鄉聚會上,他們再次相聚。兩個落魄的人同病相憐,惺惺相惜,範愛農經常來魯迅家裡喝酒談天,日子越過越緊張。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魯迅被任命為紹興師範學校校長,請範愛農為監學,範愛農“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據當時一位學生回憶,魯迅“溫良敦厚,給人一種敬而愛之的感覺”,範愛農“一年到頭穿著一身學生裝,一雙布底鞋,留著一個平頂頭,衣著非常單純,像一個窮學生,教書時態度嚴峻,對學生尤其嚴肅,總是成天閉著嘴,沒有一絲笑容。”
學校離魯迅家相距不到一里路,每天辦公完畢,範愛農便身著棉袍,頭戴農夫所用的卷邊氈帽,下雨時穿著釘鞋,拿了雨傘,來找魯迅談天。魯迅母親便替他們預備一點家鄉菜,拿出老酒來,聽主客高談,聽了有時不免獨自匿笑。這樣總要到十點鐘以後,範愛農才打了燈籠回學校去。
然而好景不長,也就幾個月時間,學校便由於經費緊張,人事複雜,辦不下去了,只好提前考試,提前放假。恰在此時,魯迅好友許壽裳向教育總長蔡元培推薦了魯迅,蔡元培說,我也早就聽說過豫才(魯迅本名)的大名,正要寫封聘任函,現在你就趕緊替我寫封信,讓他趕緊來。這封聘任函對於魯迅無異雪中送炭,魯迅把去教育部上班的決定告訴了範愛農。範愛農很贊成,但頗淒涼,說:“這裡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魯迅到了南京,範愛農隨即寫來一封信,講述自己在學校的艱難處境。其中有“蓋吾輩生成傲骨,未能隨波逐流,惟死而已,端無生理。弟自知不善趨承,斷無謀生機會,光景絕望矣。”
魯迅很快到了北京,範愛農又寫來一封信,此時他已經被學生們驅逐出校了。過程大體如下。
一個星期日,兩個跟範愛農平時有意見的同事讓廚房給學生們開伙,按照校規,星期天補開伙食需要教務室和後勤室同意,所以廚師沒有聽這兩人的話,拒絕了。兩人懷恨在心,遂在第二天早飯上唆使學生們鬧事,聲稱飯裡吃出了蜈蚣。當時範愛農正好在場,他是監學,便命令廚師換掉重做,還訓斥了廚師幾句。不料午飯時,學生們又說飯裡有蜈蚣,當時範愛農不在場,校長在場,帶頭不吃。眾意洶洶,要求換掉廚師。校長便讓學生們徵詢範愛農的意見,範愛農說,讓廚師們重做就行,如果做得還不好,可以讓學生們自己帶飯吃。
結果晚飯做熟,教員們和學生們都不來吃。去請也不來,搖鈴也不來。範愛農說,此前說好的,嫌棄飯菜不可口可以自備,現在你們都沒有自備,就請無論如何吃一點,眾人還是不吃。範愛農怒了,說道,這是學校,不是飯館,你們不吃飯也不上課,如果想就此退學,那就趕緊回家,即使你們幾個退學了,學校照樣還開。學生們於是都去吃飯上課了。
第二天早飯,校長等眾人坐好,忽然說,以後大家如果覺得飯菜不可口,應該在吃飯前就說,不能在吃飯時才說。就像昨天那麼搞,以後再犯,我絕不答應。學生們怒了,吃完飯一起找到校長,聲言要罷課,接著把矛頭對準範愛農,因為範愛農說過嫌飯菜不好可以回家的話,學生們聲稱,如果範愛農還在學校,他們就不上課。範愛農說,除非校長辭退我,否則我不走。校長於是開除了兩名學生。支援學生鬧事的兩個同事於是帶了幾個學生,把範愛農的行李搬出了門房,並把這件事登在報紙上,範愛農就此失業。
範愛農失業後,走投無路,又去曾經逼死過他母親的二叔家蹭飯,沒蹭幾天,就被二嬸趕了出來。此時他的身邊沒有一個老友,有的去了杭州,有的去了南京,有的去了北京,正在窮愁之際,一位報館的年輕朋友伸出援手,邀請他擔任社外編輯。範愛農把此事寫信告訴魯迅,魯迅高興地跟一起住在紹興會館的許壽裳說,範愛農進了報社,總算找到了一個吃飯的地方。沒想到僅僅過了一個月,範愛農和報館中的朋友一起乘船出去玩,半夜酒醉,失足落水而死。
對於範愛農是怎麼死的,魯迅在回憶文章中“疑心是自殺”,理由是範愛農會游泳,不容易淹死。這個推論得到了魯迅二弟周作人的附和。周作人說,範愛農“似乎很有厭世的傾向,這是在他被趕出師範以前所寫的信裡,也可以看出痕跡來。”這個痕跡,就是第一封信中寫的“蓋吾輩生成傲骨,未能隨波逐流,惟死而已,端無生理。弟自知不善趨承,斷無謀生機會,光景絕望矣。”
我們覆盤範愛農短暫的一生(30歲),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便是“性格決定命運”。範愛農也知道自己的性格短板,便是“天生傲骨,不善趨承”,用現在的話說,便是情商低,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這導致他“斷無謀生機會”,最終釀成悲劇。
但是話又說回來,範愛農之所以混得這麼慘,還有一個原因,便是沒有“一技傍身”。我們以魯迅作為對比。魯迅也是被學校排擠出局,但他很快得到了教育部的新工作。教育總長蔡元培雖然也是紹興人,而且是光復會的會長,但他從來不因私情照顧熟人,許多人去找他都碰了釘子,為此不無怨言,有人找到同盟會的某大佬說情,該大佬無奈地說,進別的部還行,進教育部我也沒辦法。魯迅之所以能進教育部,絕非跟蔡元培有私交,事實上當時他根本不認識蔡元培。蔡元培之所以聘用他,皆因魯迅是有兩把刷子的。
魯迅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就跟兄弟周作人一起搞文藝,翻譯了很多外國小說寄回國內發表,小有名氣。他還是章太炎的學生,舊學功底非常深。他們的好學甚至引起了日本媒體的注意,當時的日本媒體登載,清國留學生中有姓周的兄弟倆,學習異常刻苦,非常難得。所以魯迅的大名,蔡元培是聽說過的,魯迅的才能,蔡元培也是見識過的,因此許壽裳跟蔡元培一推薦魯迅,蔡元培馬上便答應了。後來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校徽便是請魯迅設計的。
比起魯迅,其弟周作人就差點。魯迅去教育部上班,周作人一直在杭州教書,直到幾年後蔡元培當了北大校長,魯迅為了給周作人找工作,多次出入蔡元培府邸,自稱“晚生”。周作人到了北大,怕教不了書,每次白天把講稿寫好,晚上交給魯迅修改,第二天自己謄抄一遍,交給北大教務處審閱存檔印發。就這麼過了一年多,周作人才在北大站住了腳,逐步得到了同行認可。
魯迅剛到北京時,也曾試著給範愛農找個工作,可是一來人生地不熟,自己還沒有開啟局面,沒有人脈,二來範愛農沒有一技之長,想給他找個合適的工作也很難。畢竟自古以來“長安居,大不易”,帝都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幾乎在創作《範愛農》的同時,魯迅又寫了小說《孤獨者》。小說中的“我”和“魏連殳”就是現實中魯迅和範愛農的翻版,但是魯迅給了魏連殳一個悲壯的結局。現實中的範愛農窮困潦倒而死,小說中的魏連殳卻在被學校解僱後,為了活下去,當了一位師長的幕僚,過了幾天頹唐奢靡的生活。
《孤獨者》中的“我”與魏連殳同樣有著一身傲骨,但在處理現實問題上是有區別的。“我”對現實的打量和生存的策略,相對客觀、冷靜、務實而沉穩一些。“我”能將生活的壓力和精神的掙扎化為一種淡定的應對,換言之,能夠適應社會,但是魏連殳卻不行。
周作人把範愛農去世的訊息寫信告訴魯迅後,魯迅悲憤異常,徹夜難眠,寫了三首詩祭奠。
風雨飄搖日,餘懷範愛農。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世味秋荼苦,人間直道窮。奈何三月別,竟爾失畸躬。
海草國門碧,多年老異鄉。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故里寒雲惡,炎天凜夜長。獨沉清洌水,能否滌愁腸?
把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酩酊,微醉自沉淪。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故人云散盡,我亦等輕塵。
魯迅最得意的一句便是“白眼看雞蟲”,因為範愛農經常喜歡翻著白眼看人。
魯迅的文章冷靜沉鬱,非常耐讀,值得反覆讀,多次讀。這套魯迅作品集,十冊只需幾十塊錢,物美價廉,喜歡的朋友可以買一套看看,點選下方連結即可直接購買。
魯迅經典全集(全10冊) 正版原著 雜文小說散文集
¥79.5
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