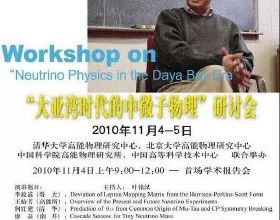採訪、撰文 | 趙力
封 |《孤兒》劇照
2021年8月,晚上六點多,躺在只有四十平老房子裡的龔強聽到手機短短的震動,他一骨碌爬起來、伸長胳膊去夠床頭櫃上的手機。可看到微信的一剎那,他又癱在了床上。
微信是龔強的母親發來的,內容和這個月之前發來的幾條沒有太大的差別,“你發工資了嗎?”龔強哭笑不得,心裡堵著。母親每個月都會來要錢。“只要不是幾百塊,給她一千兩千三千都不挑。”
但今日的龔強已非從前,“媽,我都快失業了。你還一個勁兒地管我要錢啊!”龔強發完這條語音,又頹在床上攤開身體。他是一名校外培訓機構的老師,自從國家實施“雙減”政策後,已經快一個月沒上班了,平時的他,只能靠家教過活。
最後一萬塊錢
8月末的一天,龔強衝進地鐵站時天空還在下著大雨。一個小時後,他從城市另一邊的地鐵站出來時,天空已經轉陰。龔強顧不得鞋子和褲腳浸溼,在路邊掃了輛共享單車,向做家教的小區奮力蹬去。
到了高層樓下,按響門鈴,那端傳來女主人的聲音,“你在樓下沒看見我家孩子嗎?”龔強一愣,“不是約了這個時間家教?孩子怎麼能在樓下?”女主人聽起來也很無奈,“他說不願意家教,就跑出去了。我也攔不住。”“那你給孩子打個電話吧!”龔強的語氣有點生硬,他真的不高興,“我等你一會。”
幾分鐘後,女主人打過來,“孩子不接電話。老師,真抱歉,讓你白跑一趟。”龔強心裡老大不願意,今天這五百塊錢又跟他一起泡湯了。
龔強的家教價格在高三年級中算低的。他多半靠熟人介紹。換做兩個多月前,他恐怕都沒時間接這樣路途遙遠的家教,“週末兩天、平時晚上六點到十點,排得滿滿的。講一個小時,只能休息十分鐘。到了週一白天,真是嗓子疼得一句話都不想說。”而現在,一天能有一次家教已經算“爆單”。
龔強回到家,還沒來得及脫掉溼襪子,母親的電話就打了進來,“你還沒發工資啊?”“你不是找了份超市的工作嗎?還這麼缺錢?”龔強有些不耐煩。“我可幹不了這個活兒。”母親在電話裡的語氣讓龔強甚至想象得出這個年近六十的女人眼睛一眯、嘴一咧的表情。
“在超市幹活不比伺候家裡那幾畝地輕鬆?”龔強繼續說。“時間長、不讓休息。天天被使喚。”母親在聲音上壓過龔強,“不說這些。你這個月到底發工資沒?以前這個日子都發了的。”龔強氣得語速更快,“我都快失業了,你咋不問問我咋活下去?就知道要錢。”
龔強的母親面對兒子的指責總是臨危不亂,“你就給別人講講課、動動嘴,幾百塊就到手了。你看我和你爸,像你這個歲數時,天不亮就要下地幹活。老了這疼那疼。哪有你賺錢這麼輕鬆。”龔強知道自己再說下去也是於事無補。他一邊聽著母親喋喋不休,一邊看了看微信餘額,還有不到兩萬塊錢。
“你月月管我要錢。就沒想過管我姐要錢嗎?”龔強還在做最後的掙扎。“對了,提到你姐,你還真要多給我一些錢。我打算這個月去你姐家幫她帶孩子。你姐也不容易,嫁了個男人,好吃懶做。我不去看看都不放心,不知道她這日子怎麼過……”
“行了,我最後給你一萬,你以後別管我要錢了。你從大學就不管我。你再要錢,咱倆就斷絕母子關係。”說完,龔強掛了電話。他轉了一萬塊錢給母親,母親連一秒鐘都沒耽誤,收了。剩下的九千多塊錢中有六千是接下來半年的房租。而培訓機構這個月一千五的底薪還沒發。龔強感覺從心裡到外的累,喘氣都費勁的累。
“我不會朝鮮語族”
2019年,沒有新冠疫情,也沒有“雙減”政策,龔強還有個男朋友。在他看來,那段日子雖然滿是爭吵,但他的身體至少有個溫暖的去處。時間再往前推一些,2010年龔強讀大二。母親一個月給他五百塊。這五百塊不僅包括了生活費,還包括了學雜和住宿費。“根本不夠用的。”龔強只能試著打工賺些錢。
“你是朝鮮族?”一家燒烤店的老闆看了眼龔強的身份證,“你會說朝鮮族話不?我們這裡幾乎都是朝鮮族的。”龔強遲疑了一下,搖搖頭,“我爸我媽和我姐都會,就我不會。”老闆嘆了口氣,“太可惜了。看你人高馬大的,應該是一把幹活的好手。但不會朝鮮族話……”
從龔強記事起,父母在家裡就對自己講漢語,而跟姐姐講朝鮮族語。其實龔強聽多了,也會一點。有一次母親聽見龔強和姐姐用朝鮮族語對話,立刻把剛上小學的龔強打了一頓,邊打邊訓,“誰讓你學的!”父母一輩子幹農活,手很有勁,龔強被堵在土炕一角,打得幾乎昏過去。從那之後,龔強再也不敢表現出來自己會朝鮮族語了。
龔強讀小學二年級時,母親的腰忽然壞了。他只知道父親帶著母親去了城裡治病,一去就是半年多。那幾個月裡,龔強跟著姐姐,兩人摸索著學會了煮飯、炒菜,在左鄰右舍的指導下學會了下地除草、施肥和打藥。
2011年,龔強看到校園裡張貼著招聘兼職教師的廣告。一節課六十塊錢。他在心裡迅速算了一下,如果一天兩節課,一個月就可以到手三千多元。那他就不需要母親“施捨”的那五百元了。更讓龔強沒想到的是,做了半年多小學補習班老師後,自己被安排到初中補習,課時費也漲了。這期間他結識了一位四十歲出頭的家長。那時還不確定自己喜歡男生多些還是女生多些的龔強,第一次跟了這位大叔。其實大叔的孩子不是龔強的學生。兩人不過是打了個照面,龔強就電光火石般開了竅。等到在培訓學校旁邊的浴池再次偶遇後,他們對上號。
一年後,龔強大學畢業,順勢就在這個培訓學校入職,從初中部調入了高中部,收入豐厚了許多。可他還是偶爾想起2012年那個大叔給他的溫暖,“我也搞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大叔讓我覺得溫暖。連我媽都沒給我這樣的感覺。”
2015年底母親再次摔傷。這一次傷得很重,需要置換人工軟骨。一輩子務農的父母掏不出將近十萬的手術費。那時已經出嫁的姐姐卻主動跟龔強商量,“你看你姐夫也沒工作,我也在家備孕,一直沒上班。這個家裡唯一有收入的就是你了。你還是男孩,要不你想想辦法?”
龔強跟學校請了假,回了老家。到鄰居和親戚家一家一家地說好話、借錢、寫借條,好不容易湊了六萬多,再加上自己攢下的三萬多,終於湊夠了手術費。
母親的手術是在省城做的。龔強沒去照顧,連面都沒露。姐姐去照顧了半個月。他不知道父母和姐姐在一起會用朝鮮族語議論些什麼。以前這樣的場景經常發生在家裡,讓龔強每一次都不太舒服。龔強清楚地記得,他從做了二十多年的老鄰居家帶著五千塊錢走出來時,背後那一句“別看老龔家撿了個兒子,關鍵時刻還都靠這小子”。
這句話是用朝鮮族語說的。大家都以為龔強不會朝鮮族語。其實他聽得懂。
“孤兒”
龔強已經有三年沒回家過春節了。2020年是因為疫情。2018年和2019年是因為男友。龔強的男友在很小的時候就失去了父母。龔強不得不承認,這是最讓他有“共鳴”的一點。他執拗地認為自己也是一個“孤兒”。
母親開始無休無止地問龔強要錢。男友曾勸龔強,“不如你直接問你的父母吧?”龔強不肯,他更不敢。他怕如果自己真的是父母撿來的孩子,接下來的日子,是和父母姐姐形同陌路,還是一如既往?無論哪一種,對他來說都是一種折磨。
忙碌的工作讓龔強的業餘時間變得很少。週末和公共假期都是最忙的時候,就連夜晚也是工作時間。但男朋友是做銷售的,人活潑。夜裡各種各樣的“應酬”,讓龔強眼花繚亂。一開始,龔強還會叮囑“別喝多了”、“早點回來”。兩個多月之後,兩人開始就此發生無休止的爭吵。
這樣的狀態沒有持續太久,男友提出了分手。龔強特別不理解。和男友的分手讓他無法在原來的住處繼續生活。沿著地鐵,他換到了距離學校四站地的另一側。房租也比原來的要便宜。龔強自我安慰,“這樣每個月可以多還一些之前借的錢了。”龔強在還錢這件事上,最初很有壓力,他拼命攢錢,每個月可以攢下近五千。按照這樣的速度,一年多的時間就可以還完之前的借款。可從2016年起,母親每個月都會問他要錢。有時龔強忍不住發脾氣不想給,母親就安撫他,“我們家就你這麼一個兒子,我還能有別的心眼嘛!將來要是攢下來錢,也都給你。”
龔強是從2017年開始再也不相信這些話的。那一年,龔強跟母親商量,“我不能總是租房子啊!我怎麼也要買個房子,也算是有個住處。哪怕小一點的二手房也可以啊!”電話那端的母親正在跟左鄰右舍的幾個女人打麻將,心不在焉地說,“你這麼大了,也該養家了。你每個月多給我一些,你想幹嘛就幹嘛,別的我不管。”龔強心裡尖銳地痛了一下。掛電話前,母親又急三火四地擠進來一句,“你最近多給我點吧,你姐打算要孩子了,我得多給她一些……”
“憑什麼?”
“你不是還沒物件嘛!你也沒結婚,哪裡就有那麼多用錢的地方。”
母親就沒有心嗎?龔強甚至後悔,當年的借條為什麼是寫了自己的名字?救誰的命,不就該寫誰的名字嘛!
讓龔強特別堅定自己是一個撿來的孩子的原因是父母從來都沒有催他結過婚,“男孩要結婚,家裡無論如何要出錢的。哪怕不買房子,聘禮總要給幾萬吧?”
從2015年給母親治病後,父親常年在外省打工。母親去過外省一段時間,兩個多月後就返回家,“那些活兒我都幹不了。”而母親口中的“那些活兒”也不過是一些後廚洗碗、超市理貨。一輩子務農的母親習慣了天大地大,不受管制。母親催著姐姐結婚、然後又催著姐姐要孩子時,龔強還暗自慶幸,畢竟他喜歡男人。可如今想來,怎麼母親不催自己,反倒催姐姐?
一天,龔強結束了家教,路過城市裡的室內冰場。他忽然想起小時候的冬天,村子裡的小孩扎堆玩一種叫做“滾冰”的遊戲。其實就是在冰上划著冰車追逐打鬧。因為諧音“滾病”、寓意把病都滾走,所以大人也願意讓孩子們去凍冰的河面玩。
一次,龔強跟姐姐一起從一個小陡坡上坐著冰車滑下來,半路磕在一塊凸起的石頭上,兩人一起從裂縫的冰面掉進河裡。因為是在河邊,水不深,沒啥危險。倒是衣服都溼透了。龔強不願回家換衣服,怕被母親罵。姐姐跑回家,足足過了快一個小時才出來叫龔強回家,“媽怕我感冒,給我洗了熱水澡。現在讓我叫你回家。”
龔強那時光顧著害怕。回到家,母親讓他用姐姐剩下的溫水洗了洗,換了身衣服,並沒有問他是不是冷了餓了。龔強一直以為是姐姐安撫了母親。可如今,他電光火石一般:也許母親壓根就沒有擔心過自己。
龔強不願意想這些,可又忍不住。似乎每一條得到的資訊都在指向那個答案。他甚至覺得,連自己這麼努力工作的習慣,都跟母親姐姐不一樣。
2020年6月,龔強的手機響了,區號顯示是老家的電話。他遲疑著接了,是五年前借錢給自己的一位老鄰居的兒子,語氣特別激動,“當年你媽病重,你過來管我們借錢,我們也借給你了。雖然就幾千塊錢,也不能一拖就好幾年不還吧!我爸現在病了,錢是小事,你不還錢,老爺子心裡憋氣。”龔強雖然隔著電話,也被這段話數落得面紅耳赤。
對方繼續說,“我剛才去找你們家。一個人都沒有。你媽是跟你在一起,還是跟你姐在一起?”龔強心裡疑惑,“我好幾年沒回去了。我不知道我媽去哪裡了。應該是跟我姐在一起吧?”對方也很無奈,“老龔家也就你這麼一個人還算靠譜。你先把錢從微信上給我還過來吧!也讓我爸別那麼上火。”
龔強心裡一動,“還錢沒問題。我有個事想問大爺。你能幫我問一嘴?”對方聽龔強說要問“自己是不是父母親生的”,也是一愣,只能說“試試看”。龔強先把借的錢在微信上轉了回去,又等了足足一個多小時,對方才回信息說,“我爸說這是你們自己家的事,他一個外人不好說,也不清楚。”
就在龔強反覆品著這短短的一句話,打算回覆“謝謝”時,對方忽然發了四個字,“你懂了嗎?”龔強的背後慢慢滲出一層細膩的汗。
2021年9月,龔強又接到了母親的“催款”資訊。這一次他非常憤怒地撥了電話回去,“我沒錢了!我真的沒錢了!我現在都快失業了!你讓我活下來行嗎?你以後管我姐要錢吧?”母親在電話那端卡殼了幾秒鐘,“你姐最近也出去工作了,去夜場賣酒。賺得辛苦錢,沒有你這麼輕鬆。”“我不輕鬆。”龔強彷彿被咬了一口,“你讓我攢點錢,我也想買房子,我也不想總是一個人。”母親的回答有點莫名其妙,“你想買房子就買房子,不用和我講的。我沒錢,沒法給你掏錢買房子。”
“那我不結婚了。”龔強又說。這是他的心裡話。他心想,“我一個男同性戀,我結什麼婚!”但之前一直都沒有機會說這些。這一次,趁機吐出心裡話。母親毫不遲疑,“隨你便。你不想結婚就不結婚。”頓了頓,又補上來,“這個月你先給我一千吧!”
龔強竟然開心了。他不用像別的同性戀那樣需要擔心結婚這個問題。
--------
*文中人物為化名。

趙力| 作者
用盡全力才能默默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