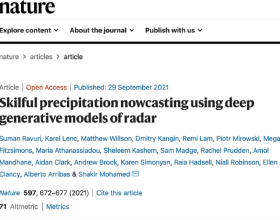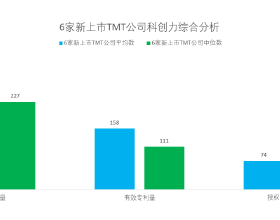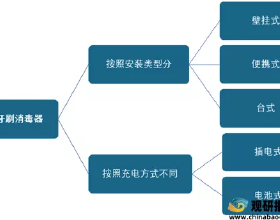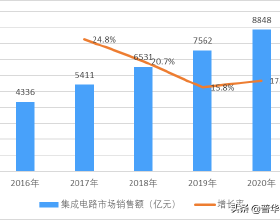“2020年1月18日,現代速度的高鐵刺穿凜冽的夜色,向著疫情正在失去控制的‘震中’武漢呼嘯而去。”長篇非虛構作品《鍾南山:蒼生在上》(《收穫》長篇專號2020春捲,花城出版社出版),就從鍾南山登上馳往武漢的高鐵寫起。
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讓地球按下了暫停鍵。在這場世界性災難面前,中國記住了一位耄耋老人,那一夜他奔赴疫情“震中”,匆匆的行色,睏倦時凝重的表情,危急關頭的果敢與擔當……都令世人印象深刻。
選擇寫鍾南山卻是一個費力不討好的活。首先,一個與現實零距離的題材,如何讓文學性不被堅硬的現實埋沒,讓藝術在接近紛紜社會時不至於窒息?其次,寫一個現實生活中真實的人物非常冒險。因為無論如何努力,作品中的人和真實的鐘南山依然有距離。一是受條件拘泥,不能放開寫。譬如一些特定時期,鍾南山內心的矛盾、糾葛並不好挖掘。幾十年後,或許這些遺憾會有彌補。二是,我們得承認,作者其實寫的是他心中的那個人,作家是一個塑造者創造者,就文學本質而言,真實的人不過是個原型,哪怕非虛構作品也是如此。寫成文字的東西沒有不是主觀的。這不但是個文學問題,也是一個哲學問題。但往往離人物太近,受真實人物的侷限,與真人像不像幾乎成了唯一的標準和追求。這樣做的結果,往往犧牲的是作品的藝術性。
三是鍾南山是個公眾人物,他的事蹟盡人皆知,幾乎沒有虛構的空間。而真實的東西往往會有種種限制。
但作家並非無所作為。寫作必須要有飛揚的靈魂。我可以把筆觸深入到鍾南山的內心世界,從他的精神與情感進行挖掘,並且打破時空,將人物置身於尖銳複雜的背景與宏大的視野,以文學的力量復原某些重大時刻,記錄歷史,留下現場,並對此進行深刻的反思。
這部書寫作用了1個月時間,修改卻用了近2個月的時間。寫作時,我每天只睡五六個小時,大都是凌晨2點才上床,寫得腦子就像發熱的轉子,還會脹痛。我從來沒有這麼辛苦過。現在用腦久了,還有後遺症。
熬時間只是一個方面,最麻煩的是我寫的是正在進行中的事情,它時時都在變化之中,就像這次疫情最初暴發,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誰也無法想象!事情有了轉變,之前的表述尺度就得修正,新的事實出現了,又得補充,不準確的地方還要修改。我也不想放過任何細節,所以被編輯笑話為“細節控”。寫作總有結束的時候,而疫情至今仍未停止,還得采取某種寫作策略。這是一種無休無止的折磨,我天天關注新聞,搜尋資訊,看手機看到想吐。

《鍾南山:蒼生在上》把鍾南山放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來寫,我也想透過寫鍾南山把新冠肺炎疫情的歷程寫出來。畢竟這是人類歷史很重要的事件。但這是寫人物,有傳記寫作的特點,我想把他的一生呈現出來,當然是有重點有選擇的。只有把他的人生寫透了,才能寫出鍾南山為何敢醫敢言,才能理解他的性情、胸懷和作為。
兩次疫情都在他年事已高的時候出現,都如此兇險。竟然都是他一次又一次出征。看到他84歲還如此操勞,這個事情本身就值得反思。從非典到新冠肺炎疫情,17年之間,到底我們有哪些地方進步了,哪些依然如故,重複著類似的劇情,發生著同樣的悲劇。誰能保證若干年後,這樣的劇情不再上演?如果沒有鍾南山,我們是否能夠做得更好?或者相反?
鍾南山一生充滿挫折,這是當初我也未曾想到的。這些挫折他自己也難以忘懷。如果沒有超乎常人的上進心、事業心,他走不到今天。強者,大成就者,挫折就是人生的階梯,有挫沒有折;尋常人,一挫就折,挫折就是他一生的失敗,一生也難以走出來的痛苦。命運誰也不能選擇,但奮起一定是個人可以主動選擇的。
我不造神,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是一樣的,都有七情六慾,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當普通人來寫。但人比人確實有高低,有的人光明磊落,有的人唯利是圖,蠅營狗苟,有太多小人惡人當道,正因為如此,鍾南山的出現才顯得珍貴無比。這樣的寫作才具有價值。
(作者系著名作家、魯迅文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