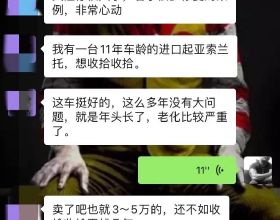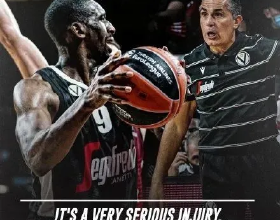佇立在沂蒙山下沂水縣桃棵子村的兩棵青松旁,沂蒙大娘祖秀蓮和八路軍戰士郭伍士的墳塋,一大一小,靠挨著,安息在此的這對“母子”可謂生死追隨。落葉在四周翩躚飄落,一個高地,一支號角,是那麼的樸素而又宏偉。掀開歷史的紙箋,時間深處,蘊藏著打動世人的真情往事。
山東省沂水縣桃棵子村地處沂蒙山腹地,抗日戰爭初期,桃棵子村一帶是八路軍支援建立的一塊根據地。戰火硝煙中,人民與子弟兵血肉相連,經受住了血與火的考驗,湧現出許許多多的英模人物。
其中有一個母親的名字——張大娘(祖秀蓮),祖秀蓮捨生忘死救護生命垂危的我八路軍偵察兵郭伍士,郭伍士落戶桃棵子村終生報恩的事蹟更是感動了無數人,教育了後來人。
祖秀蓮,原名祖玉蘭,1891年7月10日出生在山東沂蒙山區沂南縣杏墩子村,後來嫁到沂水縣院東頭鄉桃棵子村張文新為妻。丈夫比他大十來歲,二人生有四個閨女一個兒子。她為人正直、急公好義。
1941年11月2日,日寇出動5萬餘人對魯中地區進行大規模“鐵壁合圍掃蕩”。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部從敵人的空隙中轉移到沂水縣金泉區西牆峪村。
11月6日早晨,偵察兵郭伍士順著擋陽柱山,東坡地往北走偵察敵情。他發現幾里外的山上都有敵人,幾個村子正冒著黑煙,那是敵人在放火燒房。他的腳步加快了,想趕回部隊報告情況。
誰知,就在郭伍士剛剛翻上一道溝坎的時候,從前邊一個山崖上轉過來幾個鬼子。他還沒來得及隱蔽,敵人一齊朝他開了七八槍,他身子猛一震,就倒下了。接著,兩個惡狼般的鬼子撲過來,端著明晃晃的刺刀,哇哇叫著朝他刺來……。確定他不在動彈的時候,鬼子才收刀而去。
過了好久,他竟然甦醒了過來。等他用力地睜開眼睛,只見太陽已經偏西了。他只覺得天旋地轉,冰冷的身體像躺在千萬把刀尖上,口裡和心窩子裡火燒火燎的,似裝著一塊烙紅的鐵,他只想猛喝一頓水。
此時,西山上,激烈的槍聲傳到他的耳邊,郭伍士猛地想到:“不好,部隊可能又跟敵人遭遇了,應該去趕部隊。”他拼上最大的力氣,讓自己坐了起來。就在這空當,只聽見一個聲音說:“同志,同志!你還活著……!”
郭伍士見是一位老漢蹲在身邊,八路軍不管走到哪裡見了老百姓,就像見了自己的親人。他的身子一軟,靠在了大爺的身上,口裡想喝水,不知怎麼就是說不出來話。
大爺連忙扶住他,叫他別動,一邊說:“同志,我知道淌了血的人想喝水,可這裡哪有水啊!我先給你包紮傷口,你去最近的桃棵子村去找水喝。”
他把郭伍士的綁腿布拆下來,給他包紮左胳膊上、腿上那幾處傷,這是敵人用刺刀捅的,沒刺斷骨頭。最厲害的是脖子上和肚子上的傷是槍傷,腸子斷了,生命就危險。郭伍士自己把腸子塞進腹內,大爺用他的褂子把這個傷口扎住。
大爺扶他站起來,把放羊鞭的杆子塞進他手裡,往北一指:“那不,往北走幾百步就是村頭。我趕著羊太招眼,我往南把敵人引開,來掩護你。”才走了幾步,大爺趕緊回頭叮嚀道:“你淌了這麼多血,可千萬別喝涼水,一喝就完了。”
郭伍士點了點頭,他兩眼望著這位救了自己的放羊人,心裡有千言萬語想向他傾訴,可嘴巴里發不出任何聲音。
他艱難地拄著放羊鞭杆,一步步往村子的方向挪動,每走一步身上都是撕扯的痛,口乾又心熱,到桃棵子村頭只有幾百步遠。要是往日,他一口氣就跑到了,可是今日不行了,眼前還一陣陣發黑,身子老要倒下去。
總算到了村口,天就快要黑下來了。他多麼想撲進最近的農戶,大口大口地喝一陣水!入了村才發現,村裡空蕩蕩的,一個人影也不見。他一連走到幾戶人家的大門口,全都鎖著門。是啊,鬼子在這一帶來回掃蕩了好幾天,誰還不進山藏起來呢?
深秋的風吹得他直髮抖,他依在一塊大石上稍微休息了一下,又強支起身子,終於蹣跚到一個冒著煙的小團瓢屋邊。他也不知道哪兒來的力氣,幾步衝進了院子裡。郭伍士想喊人,喊不出來。
就在這時,從屋裡走出一位穿著一件土布淺藍褂子的大娘,她高高的個兒,五十歲上下。手裡端著的一個瓢“噹啷”一聲掉在地上,她被闖進來的這個傷者嚇懵了。
這位大娘,就是祖秀蓮,人稱張大娘。她定神一看,眼前這個人穿著一雙草鞋,下身穿著一件軍褲,裹腿包著傷口,很快明白過來了。
後來用她自己的話說,“一看就知道是同志。是同志就要破上命救!”她口裡說著:“你,你,我的老天爺……”。郭伍士身上的力氣不知跑哪去了,就像來到了自己母親的身邊,兩腿一軟,祖秀蓮幾步搶了過來,扶住了郭伍士搖晃欲倒的身子,把他架進了屋裡。
郭伍士感到身上的傷疼已經不是最要命的了,只覺得嗓子眼裡有團火在燒。他一把抓著大娘的手,指指鍋臺上的燎水壺,祖秀蓮趕快倒了一碗溫水,要往他嘴邊送,這時就聽那邊炕上一個老人說:“看你,越急越糊塗。同志淌了血,水裡要加鹽!”說這話的是大娘的老伴張志新大爺,他正發瘧疾,躺著起不來。
祖秀蓮大娘聽了,急忙從鹽罐子裡捏了一小撮鹽,放溫水裡攪拌開來。大娘往他嘴裡倒的水,又從嘴角淌了出來,一滴也流不進他的喉嚨裡。
郭伍士急得用手扣嘴巴,大娘忙放下碗,把他的頭輕輕放在她懷裡,掰開他的嘴,看了看說了句:“俺的娘……。”只見幾顆斷牙被血塊包著。
大娘的嘴唇有點發顫,臉上冒著汗,她伸出一個指頭,輕輕地伸進了郭伍士嘴裡,慢慢往外摳,一下子把粘著碎牙的血團摳了出來。
郭伍士只覺得自己的嘴巴和臉是腫的,並不知道原來子彈從自己的一腮斜穿過嘴巴,幾個門牙被打斷了,血和著碎牙凝結在整個口腔中。
祖秀蓮又端過水來往他口裡倒。郭伍士吸汲這救命的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水,這才流進他的肚子裡。四五碗水下肚,他慢慢有了點精神,頭靠在大娘的懷裡,彷彿被母親照顧一樣。生他的母親已不在人世了,這個八路軍戰士,今天躺在沂蒙山區另一位母親的身邊。想著想著,兩行滾燙的淚珠順著他的兩腮流下……祖秀蓮大娘用母親的手掌輕輕地為他拂拭、淚水。解放後有人採訪,問大娘當時什麼心情?她說:“同志能喝進水,俺心裡好受了……。”
正在這時,門外突然響起了腳步聲。原來是張大爺的三個侄子張衡軍,張衡賓、張衡玉過來了。他們來告訴大爺大娘,敵人從西山上下來了,一會肯定要進村再次掃蕩。
大娘扶住郭伍士,說:“別怕,孩子,這都是我的侄子,我正愁沒有人商量,他們來了就好辦了。”三個人一見郭伍士,看出來是受傷的八路軍同志。張衡軍急忙說:“日頭落了,鬼子下了山準在咱莊落腳,快把同志藏起來吧!”大娘為難地說:“同志傷得這麼厲害,可把他藏在哪裡能放心呢?”
張衡玉說:“先把同志送到莊後那個看山屋子裡吧!天都黑了,敵人應該不會去那亂翻騰”“行!”張衡賓說,“你在前面看看路,我和衡軍抬著這位同志。”
三人,一個在前頭探路,兩個小心翼翼地抬著傷員。祖秀蓮大娘從炕上拿出一條被子給郭伍士蓋上,又給他帶上一壺熱水,說:“同志,讓你受苦了,還沒有來得及給你做口吃的。”剛走出門,張大嫂又把張衡軍叫住,說:“這個同志神智有些昏迷,咱們不能把他丟在柴草屋子不管了,今夜你們仨在外看著點啊!”
張衡軍他們抬著郭伍士轉移到村北頭一間看山小屋裡。給地上鋪了很厚的草,把被子給他蓋好,囑咐了幾句。他們走後,天漸漸黑了下來。郭伍士因為喝了水,身上和心裡,好受多了,疲倦襲來,不知不覺睡著了。
黑夜裡,祖秀蓮在村裡探聽敵人的動靜,被住在東鄰的日本兵抓去挑了8擔水,就這樣熬了一晝夜。
第二天,鬼子回據點了,三個青年才有將郭伍士同志抬回到大娘家中。祖秀蓮大娘,這才看清楚八路軍同志身上的傷。這一看,這位從未處理過傷員的婦女 嚇得臉色發白,身體發抖。這麼一位個子並不高的戰士,全身上下有七處刀傷和槍傷。嘴上、脖子後,傷口還流血,肚子上居然有一個凹陷的洞。現在是兩手空空,半點治傷的藥也沒有。她只好燒了熱水,放上點鹽,一點一點給傷員洗傷口。每洗一處,郭伍士痛苦的咬牙聲,她都聽到了,她的淚水、汗水都流下來了。
敵人這次“掃蕩”,三天兩頭到這一帶亂轉,擾的老百姓日子沒有一天好過的,該搶的都搶完了,只剩下一條命了。敵人一來了,鄉親們都到山裡與敵人轉山頭。祖秀蓮大娘和張衡軍他們幾個商量,把郭伍士同志安頓在她家不到二里路遠的村西一塊大臥牛石下的洞裡。山洞是村裡挖出來來的,原本給沒有力氣爬山的老人藏身用的。這個山洞比較隱蔽,外邊的洞口是用石塊壘起來的,不知道的人,看不出來。
郭伍士暫時就住在洞裡養傷,祖秀蓮大娘每天送水送飯。大娘很是細心,每回,她都佯裝到山上拾柴拔草、挖野菜的樣子,有時領著7歲的兒子裝作走親戚。她和郭伍士定了個暗號,在洞外敲打三下石頭,就是她來了,然後她自己挪開石頭進去。
郭伍士的吃飯問題,也讓祖秀蓮大娘費盡了心。這裡山嶺薄地,本來家家糧食就少,這兩年,八路軍和地方抗日民主政府又常在這一帶住,群眾都寧願餓著自己,把糧食和乾菜拿出來支援。敵人大掃蕩,燒殺搶掠,更是讓家家連糠菜都吃不上。
大娘家天天吃的是野菜糰子和地瓜秧,就是發瘧疾的大爺嘴邊也沾不上幾口米麵,家中還有五個孩子,也吃不上真米真面的飯。為了給傷員補充點營養,祖秀蓮就把自己像藏金銀一樣藏的一點面,一回拿出一點來,做成麵糊糊來喂他。郭伍士吃了麵糊,她把鍋粑用水泡下來給大爺和孩子們喝點麵湯。
她不分白天黑夜地紡線,再跑30多里路到敵人佔據的院東頭或姚店子集上把線賣了,只為能換點米、面回來給傷員同志做口糧。有時日軍從村裡撤走後,她還跑到敵人做飯的地方,揀鍋巴,包好回來泡給郭伍士吃。郭伍士知道這點口糧都是大娘千辛萬苦得來的,他當著大娘的面,吃的很香,可是他心裡五味雜陳。
因為缺醫無藥,洞子裡又潮溼、悶熱,對健康人來講沒有什麼,可對一個重傷員來講,就十分危險。郭伍士全身發燒,處於半昏迷狀態,又一次到了死亡邊緣。
祖秀蓮大娘看在眼裡,急在心上,上山採各種草藥,一部分熬出來給他擦拭傷口,一部分喂他喝。郭伍士的幾處傷口化了膿,身子又不能動,傷口流出的膿和血,那個氣味連自己都受不了,可是大娘卻不聲不響。
“這裡少醫沒藥,還天天躲敵人,自己是難熬過來了。”郭伍士他不想再給大娘家帶來危險和麻煩,他也受夠了罪,心想:“不如死了算了。”郭伍士朝大娘指指自己的傷口,搖了搖頭,說“大娘,你不要再為我受苦受累了。”
祖秀蓮大娘說:“孩子,咱娘倆的命是綁在一起了,又我就有你。不要想那麼多,安心養病,俺侄子他們都在打聽著呢!打聽到八路軍的醫院就給你送過去。”
敵人不來掃蕩的時候,大娘就把郭伍士背出洞口曬太陽。郭伍士躺在陽光下,兩眼望著這少言寡語的大娘,他想:“要是母親今日在這裡,她能比大娘多做些什麼呢?這不就是我的親孃嗎!”想到這裡,郭伍士的兩眼模糊了,鼻子一酸,淚珠滾了下來。
大娘抬起頭來看了看他,見他的腮邊沾滿了淚水,老人家的淚珠也往外滴。也不知道是草藥果然有效,還是老天垂憐,在那樣重傷和缺醫少藥的情況下,郭伍士的傷勢竟然一天天好轉起來,奇蹟般地渡過了生死關。
這是鬥爭形勢也有了好轉,張衡軍終於打聽到一個好訊息:八路軍一個醫護所已經到了北邊的中峪村。那裡與桃棵子村相隔一座大山,大約要翻越10裡地的山路。這天黑夜,張衡軍他們用一輛獨輪車推著郭伍士,準備把他送往醫護所。
臨走時,大娘給他蓋上被子,千囑咐萬囑咐要他養好傷,以後不管走到山南海北,一定捎個信來。郭伍士滿眼熱淚握著大娘的手,說:“無論戰鬥到哪裡,也忘不了您這個‘娘’。等革命勝利了,我一定回來看您!”他們走出很遠了,郭伍士彷彿還看見大娘含著淚站在村頭。
1947年,郭伍士從馬牧池王家奄子軍用倉庫復員,好多和他一塊復員的同志,都回到自己的家鄉去了。他老家在山西省凌川縣與河南輝縣相鄰處,他兄弟四人都參加了革命,犧牲了一位,當時老家還有兩個兄弟。從1937年走進革命隊伍,已經十年未歸,思念家鄉的心情是很急切的。
思來想去,他還是決定留下,郭伍士在沂蒙山區戰鬥了多年,已經深深地愛上了這片紅色的熱地。大娘的救命大恩他更要好好報答。不久,郭伍士被上級安排到了沂南縣工作,在隋家店落戶,與雙泉峪子村一位姓祖的姑娘結婚。
那些年,郭伍士一直惦念著挽救自己生命的沂蒙山大娘。記得,他連一句感激的話,都還沒有來得及和大娘說。當年重傷的他時而神智昏迷,已記不清張大娘家究竟家在哪兒?那個村莊的名字他也是模糊不清,具體叫不上來。
但他永遠忘不了,大娘的模樣,圓臉,富態,慈祥,頭髮一絲不亂,土布淺藍褂子……可他不知道大娘姓啥叫啥名,當時一直喊她張大娘。
郭伍士在沂蒙山區已經安家了好幾年,與妻子生下了三個孩子。但他尋找張大年的願望一直擱在心上。
後來,郭伍士想出來一個好法子——賣酒尋母。他挑著一副擔子,一頭賣燒酒一頭掛羊肉。走一村吆喝一路,有誰來買或來和他閒敘,他都會打聽人家認不認識張大娘。
這一帶人家姓張的戶數多,喊張大娘的也多。郭伍士就更難找到他要找的恩人了。時間長了,三轉悠兩轉悠,1956年的一天,郭伍士又一次走到了桃棵子村,感覺有些累了,就坐在大樹下乘涼歇息。他望著前面一道一道石頭壘砌的荒塹,還有溝裡流著的水,好像不知什麼東西,觸碰了他的神經。
他的腦海中浮現鬼子追打他,他逃命的情形,他一下子想起來這條路就是他拖著傷重的身體走過的地方。他腹上的傷疤近一尺長,每逢陰天下雨就又疼又癢。有一年,腿也疼得厲害,到醫院去檢查,結果從大腿上取出了一顆彈頭。撫摸著這些山石,往事浮上了心頭,救命的大娘就住在附近!
想到這裡,他挑起酒擔,先找到了村支部書記,說起了村裡有一位大娘當年捨命勇救自己的往事。哪知這位支部書記就是當年抬過他、藏過他的張衡軍!
張衡軍很快領著他去找祖秀蓮大娘,當時大娘正在河邊洗衣服,遠望著鬢生白絲的祖秀蓮,這個堂堂的七尺漢子撲通跪下了。
祖秀蓮遠遠地看著一個人跪著向自己走來,她心裡還納悶這人怎麼用膝蓋走路,郭伍士一步一步跪著走向娘,當他走近,祖秀蓮定睛一看,這不是……她還沒來得及說話,郭伍士一下子撲倒在祖秀蓮懷中哽咽不止:“娘呀,我可找到您了,整整八年四個月,我總算是見著您了!”
這一別十五年未見了,祖秀蓮還是能認出自己曾經照料過的八路軍同志。大娘扳過郭伍士的頭,看看後腦頸上的槍眼,槍眼沒了,可那銅錢大的傷疤依然清晰。然後,又看著他的牙,假牙,像藍鋼筆水染過。祖秀蓮抱著郭伍士,娘倆哭成一團,同行的人無不為這世間難得的真情流下了熱淚。
解放後,祖秀蓮家屢遭不幸,先是老伴去世,後來唯一的兒子又病逝了,只剩下她與三個孫子相依為命。大娘的悲苦遭遇讓郭伍士心中十分難受,他決定來到“娘”跟前盡孝。
1958年,沂蒙的深秋,片片落葉,隨風飄散。在桃棵子村崎嶇山路上,一輛載著郭伍士的三個孩子和全部家當地手推車,緩慢前行。
“俺爺用車子推著俺三個,俺還扛著個小竹竿,晃盪著玩兒。”郭伍士大女兒郭文榮回憶著說。
郭伍士當時所在的沂南縣隋家店修水庫,他可以留下,會有安置房和土地。他也可以回山西老家,葉落歸根,那裡還有兩個兄弟,能夠相互依靠。
思來想去,他最終決定落戶桃棵子村,他要報答“娘”一世的恩情。
在這之前,郭伍士曾幾趟來到祖秀蓮家,把自己的想法透給老人家。祖秀蓮說:“孩子,還是回到你山西老家吧,那裡是你的根呀,爹孃生前,你不能給他們端碗飯,他們過世了,你在他們的墳前,燒燒紙,他們在地下也安穩些。”
“娘啊,俺親孃,她要是活著,也會讓俺留在您身邊的。沒有您,哪有俺的今天啊!俺留在您跟前,能給您端碗飯,倒碗水,這心裡也踏實呀!”郭伍士的心裡話說得祖秀蓮眼淚汪汪。
鄉親們接納了這個歸來的兒子!“你是俺們村救的,你要落戶,落就是了。”曾經把他推到醫院的張衡軍主動提出讓郭伍士一家先到他家住。
後來,村裡出物出力,老少爺們齊上陣,給郭伍士家蓋起了房子,這個全是張姓人家的山村,從此多了一戶郭姓人家。
在孝順祖秀蓮的同時,郭伍士也不忘報答全村人的恩情。他幫助村裡爭取扶貧款物。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幫助村裡爭取來蒙古羊、蒙古牛養殖,還爭取來一臺“泰山牌”拖拉機。郭伍士曾幫助村裡訓練過民兵,他的軍事素養令當過兵的戰士敬佩不已。
郭伍士屬桃棵子村第三生產小隊。第三生產小隊的工日值只有一角五分,後來又生了3個孩子的郭伍士,現在是四兒二女,這對於一個有6個孩子的大家庭來說,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好在,郭伍士享受老紅軍待遇,那時,他一年能領136塊錢的補助。再後來,他每月能領到25元傷殘補助。
每月發下補助,他都是先買點心給娘送去。上級供應給他的花生油,他捨不得自家燒菜用,也都送給了祖秀蓮家,他說,這些補助,不是我的,應該是咱孃的。
安居樂業的日子是那樣的舒心,母子倆在小村裡相處了19年,沒有血緣,勝似家人。
1976年,在她85歲高齡時,祖秀蓮終於夢想成真,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她一生的願望。1977年7月,祖秀蓮因胃病去世,享年86歲。當時,郭伍士正在山西老家,他的侄子出了事故,家鄉人讓他回去料理。等他知道娘病危的訊息,他立即往回趕,但還是回來晚了,沒能見上娘最後一面。
1984年,農曆正月十一,郭伍士去世了,享年74歲。他生前告訴孩子,就葬在桃棵子村,葬在娘身邊,永遠陪伴著娘,孩子們按照他的遺願,把父親安葬在奶奶的墳墓旁。
郭伍士前半生為國盡忠,後半生為母盡孝,祖秀蓮帶著母性的光芒,帶著水的上善、山的巍峨,用血淚溫情滋養鋼鐵戰士的筋骨。戰火鑄就的母子情書寫了一段人間的大愛與大義!
感謝你看完全文。
文字由作者主觀思想+歷史客觀事實梳理撰寫。
讀歷史生智慧,讀歷史長學問,讀歷史明事理。關注@文乎
轉自:文乎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向原創致敬!
免責宣告:本文已註明轉載出處,轉載此文是出於傳遞更多資訊之目的,不作任何商業用途。若有來源標註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私信聯絡我們刪除,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