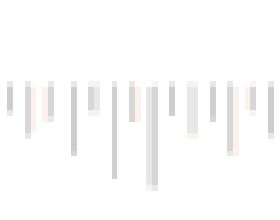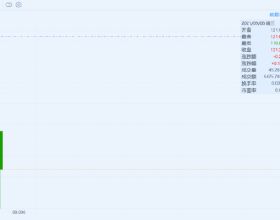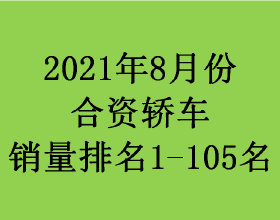1900年在鎮壓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戰爭中,各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暫時地聯合起來,結成了聯盟,向中國發動軍事進攻。但是,正如列寧所指出的:“試問,在儲存著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考茨基正是以這樣的條件為前提的),‘可以設想’這些聯盟不是暫時的聯盟嗎?‘可以設想’這些聯盟會消除各種各樣的摩擦、衝突和鬥爭嗎?只要明確地提出問題,就不能不給以否定的回答。”中國,是列強在東方爭奪的焦點。在戰爭中,他們在華的矛盾就已表現得十分明顯,特別是英、俄在直隸和英、德在長江流域的矛盾都已劍拔弩張,達到相當緊張的程度。戰爭結束後,它們間又以各種形式展開了激烈的角逐。
英國,這個原來在華享有最大權益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一面繼續緊緊地控制中國最富庶的地區——長江流域和華南各省,一面以印度為基地,向西藏和西南其它各省伸展侵略勢力。沙俄,在當時帝國主義列強的對華侵略中扮演著急先鋒的角色,野心勃勃地向中國的東北、蒙古、新疆和西藏擴張勢力。當時沙俄的陸軍大臣庫羅巴特金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皇上的腦袋中有宏大的計劃:為俄國奪取滿洲,把朝鮮併入俄國,還想把西藏併入本國。”日本和美國,垂涎欲滴地覬覦著東北。德國除控制山東外,竭力要插足長江流域。法國除在財政上支援沙俄的對華擴張外,也向中國的西南各省進行擴張。如1902年一名清朝政府官員所記述的:“英於長江、法於雲南,已久視為權力所及之地;德于山東,尤牢籠一切。”
在這樣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當時統治著中國的清朝政府又處在一種怎樣的狀態呢?這是一個極端腐朽昏聵的賣國政府。它不但談不上保衛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卻寧肯大量出賣國家權益,以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援,鎮壓人民的反抗,維護它在國內早已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
自然,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後,清朝統治者同外國侵略者之間就已逐步勾結,成為外國侵略者的工具。但是也應看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由於統治權力上的矛盾,封建統治者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之間畢竟還有著利益衝突的一面。因而,在人民群眾反侵略鬥爭的推動下,在各種條件的作用下,清朝政府還曾參加過反對英法聯軍的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和反對八國聯軍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儘管清朝政府的態度從來表現得十分被動、十分動搖,並且都很快以投降而告終,但它終究還算參加過這些戰爭。而到1900年的戰爭以後,就連這樣的抵擋,也再不能看到了。
1901年2月,當列強提出和議大綱時,那時還流亡在西安的清朝政府立刻發出一道“煌煌上諭”,宣佈政府今後的對外方針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並且厚顏無恥地宣稱:“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
《辛丑條約》簽訂後,1902年1月,清朝政府從西安回到北京。他們從開封到正定這一段路,坐的是火車。進宮那天,“當西太后乘輿經過使館人員站立的陽臺時,她在轎中欠起身來,以非常和藹的態度向他們回禮。”當1月28日各國使節受接待時,“‘召見從頭到尾是在格外多禮、格外莊嚴和給予外國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況下進行的;這件事之所以特別值得注意,乃是因為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見中公開露面’,而不是在紗幕後面的。”2月1日,她接待外國使節夫人,“在問候這些夫人的時候,表示出極大的同情,並且一邊和她們說話,一邊流淚。”“據美國公使康格夫人後來說,太后一把抓住她的手,抽泣哽噎地說:進攻使館區是極大的錯誤,後悔莫及;又趕緊摘下自己手上的貴重戒指和手鐲給康格夫人戴上。”其曲意討好的神態,令那些洋人也“認為有些熱情過分”。這些,看起來都是頗具戲劇性的枝節小事,卻很具有象徵性,顯示出了清朝政府同帝國主義列強之間政治關係上這種新的微妙的變化。
還都以後,清朝政府確實在各方面都更加獻媚於帝國主義列強。它一再傳諭保護外人權益,竭力鎮壓人民愛國運動,聘請外國人擔任財政、軍事等顧問,連地方大吏的任命也聽任外人擺佈。1901年春,歸綏有外人被殺,綏遠將軍永德幾乎被問斬。梧州英領事一電,廣西巡撫于蔭霖當即開缺。1903年初,俞廉三簡任山西巡撫,“駐京英、美、法三國公使聯名照會政府,略謂晉省傳教最盛,今俞廉三頑固性成之人,為該省巡撫,將來教案之起,正未有艾,請另簡他員補授,以為防患未然之地云云。政府無可如何,遂令俞廉三退官。”各地方官於是更加一意媚外,竭力維護外人在華的特殊權益:“外人或有所要求,苟不至過於難堪,中國(按應讀作清朝政府,下同)從未嘗峻拒,即有要索所難堪處,中國亦必曲為設法,所謂通融辦理者是也。而時請外人聽戲,而時請外人遊園,而時請外人宴會,內而宮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員末秩,皆莫不以敬禮外人為宗旨。”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在1902年2月1日得意地寫道:“我們在‘暴亂’(按誣指義和團運動)中並無所失,而事實上我們的威信大增,我敢肯定地說,多少年來我們在北京或在中國的地位,從未像今天這樣高,我們與清朝官員的聯絡從未像今天這樣密切。……袁世凱多年來比任何其他官員和我們聯絡更密切。他跟我們商議之頻繁、請教之謙恭,是暴動前不曾有過的。”
清朝政府以自己的行動,將它的賣國面目清清楚楚地暴露在全國人民面前:這是一個“洋人的朝廷”。
正因為這樣,人民大眾對待清朝政府的態度自然不能不相應地發生急遽的變化。如果說,在這以前,還有不少人對清朝政府存在著幻想;那末,到這時,抱有這種幻想的人就越來越少了。許多人不能不這樣地來提出問題:
“列強對華政策,方利用其政府以壓制我國民。不公然割我土壤入彼版圖,起我國民之反抗力,及分利不均以引動全球戰禍。乃出以至狡猾、至險狠之手段,盡網羅我國民之權利而留一地殼以居之。是將使我國民束縛於重重之壓制以自相屠戮自相消滅,而滿清政府為彼之功狗也。長此悠悠,暗無天日。我國民之目的,如即視政府為國家,則將實受覆亡之慘,而終其身在睡夢中,我同胞盍三思之。”
有的人就更直截了當地喊出:“起!起!排滿排滿!滿洲不排,則我同胞無再生之日。”
陳天華在《警世鐘》中激憤地寫道:
“你但問俄國佔東三省的事真不真,不要問瓜分的事真不真。俄國佔東三省的事倘若不虛,這瓜分的事一定是實了。你看德國佔了膠州海口,俄國、英國、法國,也就照德國的樣兒,各佔了一個海口。於今俄國佔了東三省,請問中國有幾塊與東三省一樣寬的地方?將來分的時候,恐怕還不夠分哩!於今還來問真問假,真正不知時務了。”
這段話,確實反映出當時無數愛國者奮起救亡圖存的共同的急迫心情。而印度等鄰國淪為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後的悲慘境遇,更給了許多人以血的事實的教育,使他們感到怵目驚心。有人寫道:
“彼白人近日所施於支那之政策,何一非前時所施於印度之政策乎?彼印度前日所經過之歷史,何一非支那現在親歷之歷史乎?吾人一讀印度史,但覺滿紙腥風,一把血淚,目之所接,心之所觸,誠不知己之置身於印度乎?抑置身於支那也。嗚呼,支那支那,爾其竟為印度之續哉夫?”
怎樣將中國從極端危殆的局勢下挽救出來,已成為一切愛國者日夜苦思焦慮的中心問題。他們探討一切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都是緊緊地圍繞著這個中心問題尋求答案。20世紀初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思潮的發展,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形成和壯大,都同這個根本問題聯絡在一起。既然清朝政府把自己和帝國主義侵略者緊緊地捆在一起,中國人民也就將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同反對封建統治的鬥爭緊緊地聯結在一起。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