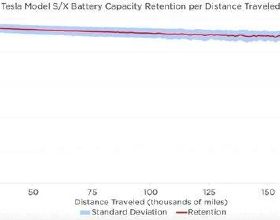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俄國著名作家,與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並稱為俄羅斯文學“三巨頭”
寂寞的殿堂
今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200週年誕辰,今年是其逝世140週年。
站在過去——現在的二維時間線上,以現在為零點,歷史人物的死亡總是比出生更近發生的事情。這不符合活著的人的感受:我出生,我來了,我活著,活著是現在進行時,出生是不遠的事情,而死亡似乎不可捉摸,乃至遙遙無期。
以此探討下去,事情就變複雜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這樣一個複雜的小說家。
他是俄羅斯文學的三座最高峰之一,同時又是世界的,全球研究他的著作汗牛充棟。換言之,在人類文明中,他是進入世界文學聖殿的聖人,居廟堂之高,應該是確定無疑的了。
然而在他身前,我更願意把他比作今天的網文作家,一名身處江湖的作家。因為他出身沒有列夫•托爾斯泰那麼華貴,一生都在低處匍匐前行。最重要的是,他寫作的直接目的是謀生。他似乎也曾上達天聽,沙皇曾被他的小說感動,但他卻並未因此享盡榮華,甚至與此相反,從沙皇的死刑稽核簽名下撿回一條命,但終生都是危險分子,一直被當局緊張地監控。
陀思妥耶夫斯基將自己的小說創作總結為“心理現實主義”,以此解釋他筆下的人物為何多為病態、撕裂、激烈矛盾衝突的複雜形象。但後世對他的解讀有成百上千的不同視角,今天我們要認識籠罩在各種光環下的文學巨匠,最直接的方法還是閱讀他的經典。不過陀氏的小說雖是“現實主義”,但讀起來卻相當不輕鬆。再加上翻譯的因素,如陀氏的重要中文譯者,年近九十的翻譯家榮如德所言,很多讀者知道這是世界文學的一座高峰、一顆明珠,但嘗試閱讀又半途而廢的大有人在。
一輩又一輩的翻譯家在努力,千方百計讓當時的讀者能夠把經典讀得下去,而且儘可能讀懂。這是讀者的有幸,而有心的讀者,還可以一邊閱讀,一邊回過頭看,200年前誕生的文學巨匠,這一百多年中人們是怎麼閱讀他的,是否存在人云亦云的低階誤讀,是否有被埋沒的閱讀發現。
在經歷過蘇中百年時代變遷後的今天,我們國家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流詞條介紹,稱其作品“揭露出資產階級的紛繁複雜、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劇性”。而正是這樣的判斷,使之在今天的世俗文化中居於邊緣化。一個打工人如果在通勤的地鐵上捧著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看,除非是被當做應考學生,不然總會被投以異樣的眼光。
百年的共情
其實,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盡都是俄羅斯十九世紀社會轉型期的世俗故事。他的很多小說題材,其實都來源於當時的時代案件和報紙新聞。這是我把他比作今日網文作家的又一原因:都取材於最容易獲得的大眾關心的熱點。只不過,今日大眾關心的熱點不再是“現實主義”的,而是一味的虛擬和娛樂而已。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年代,俄羅斯社會經歷著這樣一種危機:俄國人舊的對於上帝和人的認知在瓦解,其認知的方式,大體來說,作為一種統一的正規化,陀氏認為正在變壞,已經不足以用作解釋現實的證據。相當於今天美國人引以自豪上百年的“美國夢”的正規化,已無法解釋今天美國的現實,等等。
在這場危機裡,天主教、新教、革命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紛紛湧現,發生了無政府狀態式的碰撞,每個正規化都有其或多或少的擁躉,因為它們都手握充分的事實作為理論後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裡,不同的正規化在許多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構成複雜的“復調”對話結構。這讓陀氏看起來顯得相當摩登,也因此被稱作“一個不斷更換舊式衣裳的現代主義者或後現代主義者”。
20世紀的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是“正規化”理論的發明者,他從科學角度揭示出普遍的週期性危機:當人們對某一過去起主導作用的認知正規化產生分歧,這種曾經居於支配地位的正規化,必然已經在現實生活中捉襟見肘,暴露出種種不規則情形,數量多到人們不可接受,人們六神無主,過去的支配者不再令人信服,此時新的正規化將在危機中登場。
幫助我們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動因之一,是雖然我們和作者隔著時空轉換的遙遠距離,但我們都正在為正規化轉換而焦慮。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如果你不好好讀一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要立志成為一個像郭敬明那麼火的爆款作家。
其實,從百年前的五四開始,中國讀者就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再陌生,可能其中也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中國百年風雲,正規化從未塵埃落定。
1926年,第一本中譯本陀氏小說《窮人》由韋叢蕪翻譯出版,此書從英譯本轉譯,由魯迅根據日譯本,韋素園根據原文加以校訂而成,凝結了很多人的心血,發行效果也很好,到1947年再版了12次之多。
在此前後,各類報刊雜誌如雨後春筍般譯介了很多陀氏的作品乃至生平以及傳記,包括一些長篇小說節選。1921年正值陀氏百年誕辰及逝世40週年,以《小說月報》為主的大量期刊加大宣傳力度,在該刊《俄國文學研究》專號中,讚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物的心理學家,是人類心靈深處的調查員,是微細的心的解剖者。他為人類呼籲,他的文學滿含著人道主義的性質”。
靈魂的審問
胡愈之等人主導的《東方雜誌》是新文化運動中《新青年》的首要論敵,該刊第18卷第23期闢紀念專欄發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稱其“能完全代表此狂野民族的偉大精神,能貫徹第三帝國的國民的神秘之心,能喊出從專制魔王、貴族、地主、資本家、警察、憲兵的積威下面所發出痛苦的呻吟”,對陀氏的崇敬之情溢於言表。
百年前的中國,當然是出於家國舊正規化的危亡,在對陀氏的閱讀中發生共情。陀氏被看作“高瞻遠矚的文學家”,與另兩座山峰屠格涅夫、托爾斯泰一樣,都是“俄羅斯文學改進時代的大人物”。郭沫若更說:“俄羅斯最近的大革命,我們都曉得是一些赤誠的文學家在前面做了先驅的呢。”
不過,作為左翼作家,郭沫若和茅盾等人一樣,承認陀氏是“人類自古至今的思想史中的一個孤獨的然而很明的火花”,但也對創造社同人發出不要用天才作為“不革命”的“護符”的警告——在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眼中,陀氏是“沒落階級”,《罪與罰》是“小布爾喬亞寫實主義”。
在蘇聯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後待遇在一眾俄羅斯大師中都是相當獨特的。當年蘇聯毫無保留地出版普希金、果戈裡、托爾斯泰、契訶夫等人的作品,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卻將陀氏雪藏。直到斯大林死後,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後,才相當謹慎地推出陀氏的作品,並且加以如下定性:
“《卡拉馬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記》《惡魔》——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幾部最具有傾向性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藝術家顯得最不自由,同時跟反動傾向結合得也最密切。”“《卡拉馬佐夫兄弟》在極大的程度上是按照統治集團的直接命令寫成的。”
反倒是在中國,瞿秋白深刻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用深刻的文學言語描盡道德律的矛盾衝突。問題是指出來了,可是不能解決——”,陀氏“尋求上帝而不能證實。個性意志自由的問題和上帝的問題同等的難解決”。
魯迅當然也是內行,他給首次出版的《窮人》作小引,指出,中國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將近十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為顯示著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於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這確鑿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然而,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汙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汙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安葬在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季赫溫公墓,他的墓碑上刻著《新約》經文: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基督與反基督主題
1924年,魯迅創作了小說《祝福》,借悲慘的祥林嫂之口,發出如此拷問:“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這算是人類靈魂之問的在地化,從中可以看出魯迅早就深入閱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他還翻譯過果戈裡的《死魂靈》。
對於同樣的問題,1878年,魯迅還沒有出生,陀氏已是人生暮年,他在給友人的書信裡寫道:
“請您設想一下,世界上不存在上帝,靈魂也並非不朽……那麼請問,我何必要好好生活、積德行善呢?既然我在世上要徹底死亡,既然不存在靈魂不朽,那事情很簡單,無非就是苟延殘喘,別的可以一概不管,哪怕什麼洪水猛獸。”
1924年,曾閱讀過陀氏的魯迅,在《祝福》中借祥林嫂之口發出拷問: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代,幾乎和馬克思的時代重合,當時無神論已經透過歐洲的革命獲得大量擁躉,在陀氏的小說裡,也時有出現無神論者,並且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同時,一定存在對立面的角色,即教派信徒,乃至宗教狂人。陀氏借各種角色發出自己的靈魂審問,因此,不管是有神論還是無神論者,他都不會給予道德審判,而是借他們之口,將困擾自己一生的宗教信仰和無神論的關係問題直陳紙面,引領讀者一起思考、自省。
在陀氏影響最大的長篇小說《罪與罰》中,落魄輟學的大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是“反基督者”,就像他的偶像沉思的拿破崙那樣。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揭示了拿破崙理念的主要的無力之處,不是政治上的,也非道德上的,恰恰是宗教的:在歐洲現代化程序復興古代羅馬君主制理念、大一統核心凱撒的理念、人神的理念之前,必須克服與之相對的基督教世界統一的理念、神人的理念。然而拿破崙沒有做到,他仍然是來自上帝也不反對上帝的,他和《罪與罰》的悲劇主人公一樣,是“偽反基督者”。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書中書《宗教大法官》,直接讓宗教大法官僭越基督本尊,因為基督發明了自由,而自由信徒開始出爾反爾地反基督,必須出來一個無情的宗教大法官,將基督發明的自由管控起來。《宗教大法官》這一章節,強烈震撼了一代又一代信神乃至不信神的讀者,也使神學家們被迫起來應對陀氏虛構的該書作者,書中人物伊萬•卡拉馬佐夫的挑戰。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則躲在小說後面,一切都是假他人之口,沒辦法,壓力太大了。他早年信奉人道主義,但到晚年,和沙皇、教廷和解了,《地下室手記》開始對唯物主義和理性主義、人道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展開批判。《罪與罰》更是以論證“偽反基督者”拉斯科爾尼科夫理性殺人實驗的失敗,宣告無神論的破產。
儘管陀氏始終矛盾,但他還是在最後被稱為“思想獨特的傑出的神學家”,“以自己的神學方式表達了東正教的自我意識”。沒辦法,要是他生在清末的紹興,情況一定不是這樣。
東方與西方主題
都能成功地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前行的路標。白銀時代指的是陀氏逝世前後的19世紀的最後三十年左右的俄羅斯。同樣是“西學東漸”,俄羅斯自認自己是東方的、斯拉夫的、東正教的,但這一傳統的系統,和東漸的西方社會哲學文藝思潮發生猛烈碰撞,思想受刺激變得矛盾重重又空前活躍,宗教哲學不破不立,反而更加勃興。
對民粹主義者來說,陀氏首先是“被侮辱的與被損害者”的控訴代理人、保護者;對理性主義者和非理性主義者(存在主義者)來說,他是“殘酷的天才”,敢於直面淋漓的鮮血;對東正教徒來說,他是新基督教的先知;對現實主義者和象徵主義者(頹廢派)來說,他發現了“零餘者”“多餘人”;對民族主義者來說,他是斯拉夫人的旗手……
白銀時代的各種思想正規化互不相容,但都從不同的立場,以學習和紀念陀氏的名義進行殊死論戰。
而陀氏本人並沒有系統的哲學學說和政治理論,也沒有系統地闡述過宗教體系或藝術理論,只是在小說裡借角色之口發出種種自相對立的聲音,在日記、書信裡透露出或尖銳或溫和並往往自相矛盾的隻言片語。
經歷過黑暗的死刑解除和八年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為一個根基主義者。所謂“根基主義”,既抨擊西方帶來的自由主義和虛無主義,又揭露本民族斯拉夫主義的功利主義和專制。他認為俄羅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良“嫁接”,導致了俄羅斯的分裂,而本來,俄國的使命“將指引西方盲目的、失去了基督的人類”。
分裂主要是指貴族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脫離了人民,脫離了自己的“根基”。陀氏最有資格講這個話,因為流放西伯利亞,他天天和罪犯、苦役——亦即作為根基的俄羅斯人民在一起。
自由主義和虛無主義是困擾白銀時代俄羅斯思想界的兩大思潮。我們且看陀氏年輕時是怎麼被判死刑的:寫過《死魂靈》的前輩泰斗曾激勵青年陀氏的鬥志,但晚年果戈裡倒向沙皇專制,陀氏參加了秘密革命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公開宣讀對果戈裡的檄文。
1860年以後,陀氏流放歸來,繼早年受沙皇的不殺之恩之後,進一步享受監視下的在彼得堡的居住自由。他的思想則從根基主義慢慢靠向斯拉夫主義、民族主義,雖然說不上是完全意義上的。斯拉夫人長期以來,甚至在日耳曼人眼裡都是野蠻人,就像日耳曼人曾經在羅馬人眼裡是野蠻人一樣。而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告:“歐洲人對天狼星比對俄國更瞭解。暫時這一點就是我們的力量。”
至於經濟和科技上的落後,在1876年的日記中他寫下:“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到頭來誰羨慕誰還很難說。”
由陀氏原著改編的影視劇——群魔劇照
反烏托邦主題
1861年,沙皇正式批准了廢除農奴制的法令,長達幾百年的制約社會發展的農奴制終於瓦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親,一個低階貴族小地主,就是因為農奴制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死於自家農奴之手。這個專制的父親,給了從小患有癲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大的影響,他後來把父親的形象安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邪惡放蕩感情脆弱的小丑父親老卡拉馬佐夫身上。
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畢業於軍事工程院校,但沒有老老實實從事本職工作,而是有志於文學創作。他作品中的一大主題是奴役與自由,他覺得理想中的社會不可能建立在農奴制的基礎上,並且在作品中任由奴役理論充分發展自己的說辭,讓自由和奴役在紙上各執一詞,任其各向極端發展,其中最驚心動魄的設定,是《群魔》中的理論家希加廖夫提出的“革命”理論。
這個理論提出,把人類分成十分之一的自由的統治階級和十分之九的絕對服從,其中那十分之一擁有對十分之九的絕對和無限的權力。十分之九的人必須喪失自己的個性,變成牲畜一般,如果一代人變不成,那就多奴役幾代,透過永無休止的服從,讓他們經歷一連串的蛻變,然後達到伊甸園一般的原始淳樸。
期間要執行一些“高明”的措施,比如降低教育水平,消滅感情和各種慾望,“人只要有了家庭或愛情,他就會產生對財產的慾望。我們要埋葬這種慾望:我們將利用酗酒、造謠、告密;我們要利用前所未聞的驕奢淫逸;我們要把任何一個天才都扼殺在襁褓中。我們要把一切都歸結為一個公分母,徹底的平等。”
而且,即便是對那十分之一的自由的統治階級,希加廖夫也要“每隔三十年會使他們發生一次驚厥,突然之間大家就開始你吃我、我吃你……”
這是陀氏揭發出的極權主義的邏輯:不僅十分之九的“韭菜”被最高統治者的無限權力收割,那十分之一享有無限權力和個人自由的精英,也是最高領袖統治下的高階奴僕,而即便是最高領袖,也將成為整個制度的奴隸。
陀氏死後的歷史兌現了這驚心動魄的一幕。陀氏提前半個世紀,準確地警示了這種被迫革命的恐怖現實。還好這不是他的預言乃至詛咒,但是畢竟都發生了。
在他心中,與《宗教大法官》和希加廖夫的理論相對抗,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提出自己的社會理想——理想專制制度和東正教社會主義。要人君相愛,不要群龍無首;要世界大團結,不要平均主義;要以德治國,最好政教合一……
他提出三個著名的模型:不要水晶宮(空想社會主義),也不要蟻穴(希加廖夫和宗教大法官的理想),而是保守地改良現在的雞窩(現存秩序),讓國家消失,一切屬於自由人的道德教育……
發現教育價值 記錄教育改革
本文原創自志道教育新教育家雜誌 文/張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