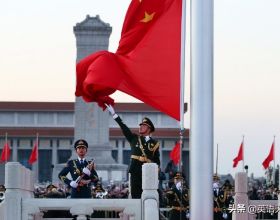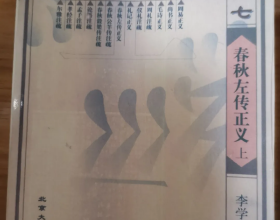阿富汗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明匯聚之地。此書記錄了作者劉拓(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現為蘭州文理學院旅遊學院副教授)於2014年和2017年兩次獨自踏尋阿富汗諸多古代遺存的故事。阿富汗局勢複雜,訪古行旅充滿冒險和艱辛,而普遍的貧窮和宗教的保守,也讓這裡有著獨一無二的風土民情。書中除了介紹阿富汗古代遺存的歷史、分佈和現狀,也描繪了此地的自然景觀和社會日常。作者在歷史、考古領域的紮實積累增添了此書的知識性,生動的敘述中飽含對過往和現實的人文思考,文筆樸實而充滿溫度。
劉 拓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驚魂巴米揚歸程
回到巴米揚,城裡幾乎一點燈光都沒有,我連來時的街道都找不見了。哈桑帶著我找旅館,我卻一心想找機會擺脫他。他還是和前面一樣耍小聰明,到旅館門口以後不讓我下車,自己去談價,然後跟我說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虛高價格。到第三家旅館的時候,我一定要自己跑去談,終於是正常價格。但他竟然說不願意跟我住一間,必須要兩個單人間,隨後我看他和店員說了什麼,結果一個單人間的價格幾乎和雙人間差不多。我積累了一天的怒氣終於爆發了,指著他的鼻子發火,全旅館的人幾乎都跑下來看熱鬧。然後我說,你自己住這兒吧,我走了,就拿起我的包跑進黑暗裡。哈桑和其他人一時沒反應過來,等他們追我時,我早就不見蹤影,伸手不見五指的夜裡,沒人能看出我是個外國人。
憑記憶走回巴米揚的街上,手機開始瘋狂振動,我索性就關機了。街上還有零星的幾個攤位,還不如遍佈星星的天空亮。我跑到街西頭的汽車站,猶豫了一下,最終沒有上亞闊朗的車,但也確實沒人願意回喀布林。我感覺自己都有點瘋癲了,在街上遇到一個人,就問他現在有沒有辦法去喀布林,大概問了20多個人,一直問到街東頭。都快10點鐘了,我幾乎就要放棄,最後又看見一家餐館,裡面還有幾個人,就想去碰碰運氣。
我帶著哭腔問飯店老闆,有沒有辦法回喀布林。飯店裡正在和人打牌的哈扎拉人魯胡拉聽到我的話,放下了手裡的東西,過來問我剛才說了什麼。我一字一頓地說,我要去喀布林,要趕明天早上6點鐘的飛機。他臉上露出了不可思議的表情,說這條路真的很危險,沒有必要為了這趟飛機冒這個險。我覺得真的是沒希望了,又不覺掉下眼淚。魯胡拉拍拍我,問我吃飯了沒有,我也確實餓了一天。他跟老闆點了一大盤抓飯,一邊看著我吃飯,一邊討論這件事。
魯胡拉說,他是和幾個朋友一起來巴米揚玩的,本來準備明天一大早回去。這段路晚上有塔利班出沒,塔吉克人和普什圖人透過沒有太大問題,但他們是什葉派的哈扎拉人,遇到塔利班後很可能有麻煩,他需要和朋友商量一下。一通電話過後,他的幾個朋友都過來了,一邊勸我放棄這個打算,一邊陷入激烈的討論。最後他們的司機,一個留著披肩捲髮,外形有點像騰格爾的小夥兒跟我說,如果我一定、一定要回去,他們願意跟我承擔這個風險,但希望我能給150美元的車費。事到如今,也只能這樣了。
我把自己的性命完全託付了出去,先隨他們到了離城區大概三四公里的一個小村莊,他們說在這兒稍微歇一會兒再出發。這是一幢非常大的房子,裡面鋪著華麗的地毯,乾乾淨淨,但除了電視,幾乎一件家電都沒有。朋友們席地而坐,開始邊看電視邊抽起水煙來。我感覺自己又受騙了,已經晚上11點,離飛機起飛只有不到八個小時,趕忙問司機到底什麼時候能出發。他說路上現在仍然危險,後半夜塔利班活動會減少,最早只能1點半出發,用最快的速度開過去。因為喀布林機場安檢非常煩瑣,6點半的飛機,5點半應該要到機場門口,這樣算起來,就只有4個小時的路上時間了。我始終覺得來不及,但司機一口咬定不會有任何問題,如果趕不到,他倒找我150美元。我只能將信將疑地答應下來。
魯胡拉的團隊共有五個人,因為我的到來,他們顯得非常興奮,在屋子裡抽完水煙後載歌載舞。房東應該是他們的朋友,巴米揚的當地人,拿出了很多小零食給我吃。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的房子為什麼是這個構造,除了一臺可能有50英寸的平板電視,屋子裡就只有地毯和很多收拾得整整齊齊的床鋪——沒準這兒是當地專門接客的民宿。到了12點,魯胡拉建議我們休息一會兒,大傢伙就都蓋著被子睡著了。月亮升了起來,斜斜地照在地毯上,我當然一點也睡不著,痴痴地看著地毯上的毛。兩天的遭遇給了我強烈的不真實感,我甚至有點希望再一次睜開眼睛,這月光是照耀在我學校的宿舍裡。
眼看要到一點半了,大家還是沒有要醒來的意思。我心裡著急起來,畢竟對於中亞中東人的時間觀念很難抱太大的希望。突然一陣鬧鈴響起,大家迅速站起身來,我才發現所有人都沒脫衣服。魯胡拉把我拉起來,最終大家在10分鐘之內就出發了。
我和三個人一起擠在後座上,這當然是出於安全考慮。車裡的空間極度狹窄,另外三個人都儘量縮起來以給我讓出更大地方。阿富汗山區的夜黑得沒有一絲人跡,路上幾乎沒有會車,沒有超車,我們放著當地的音樂在山路盤旋,好像淪亡在黑色的海洋裡。我取出手機定位,想看看到了哪裡,這才發現走了讓很多人聞之色變的巴米揚南線。時間上倒是有了些把握,而司機可能也是因為要利用後半夜趕到機場,才會選擇這條線路的。
我們的車在山區全程大概也就四五次會車,第三次會車時,迎面開來的車主動停下來,跟司機說了一句話。司機聽後臉色大變,說前面路上剛剛有塔利班活動。我們不能再走了,就找了路邊一個空地停了下來。後座上的幾個人趕忙下車,讓我趴在地上,他們三個再坐進去,用腿遮住我。氣氛萬分緊張,我問司機大概什麼時候能走,是否還能趕上飛機。司機說話有點顫抖,說別想什麼飛機了,能平安到達喀布林就謝天謝地了。我一向比較心大,以前雖然被軍隊扣押過很多次,甚至持續很多天,但從來沒有過性命的威脅,而這次我真的感到發自心底的害怕——因為連當地人都不知道,即將迎接我們的是什麼。
我趴在地上,一聲都不敢出。四周死一樣寂靜,只能聽到喘息聲,我不知道這樣的等待還要持續多久。半小時後,司機從外面跑回來,說新來的車報告沒看見塔利班,可以走了,但穩妥起見,還是讓我再趴一會兒。我的心算是放下來一半,又在考慮有沒有可能按時到達機場了。
通過了最危險的路段,司機讓我鑽出來坐好,明顯感覺他開得更快了,在山路上開出80公里/時的時速,應該是想把損失的半小時追回來。到了將近5點,我們終於到達了南線和喀布林-坎大哈主幹道的交匯處——邁丹沙赫爾城。“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危險啦!”司機大舒了一口氣,我們六個人也跟著歡呼起來。我這會兒才算是困極了,沉沉睡去。馬上到達機場時,周圍人把我搖醒,已經5點50了,離起飛只有40分鐘。司機露出小孩子完成任務一般的喜悅,和我使勁兒擁抱了一下,我趕忙就往安檢口跑去。喀布林機場有令人聞之色變的四五道安檢,乘客在1公里外就要下車徒步,經過連續三四個幾乎一模一樣的搜包檢查——沒有人知道為什麼要進行這麼多次。我手持機票,滿頭大汗地給安檢員指著上面的時間,他們也看出了急迫性,周圍的其他旅客見狀也讓開道路,讓我快速進去。最終在起飛前20分鐘,我趕上了換登機牌。巴米揚的驚魂一夜,總算告一段落。
參觀綠松石山遺產中心
時間快到9點,我準備打車去喀布林國家博物館,然而這個區域的車有些少,我就向南走,去磚橋清真寺北面計程車的集散地,竟遇到了本次阿富汗之行最後一個驚喜。在記錄老房子時,我發現這一片的房屋質量明顯高於喀布林其他地區,三層的房屋開始出現,很多房子在第二層會有木質的閣樓,又看到了好幾個雕刻精美的大門。我在其中拍得流連忘返,突然一個穿著當地服裝的年輕人湊過來,用非常流利的英語問我是不是在找綠松石山(TurquoiseMountain)。我聽發音以為是土耳其山,問他這是什麼,他說這個地方可太有意思了,可以帶我去看看。他領我走進了一個不起眼的古建築大門,拐過幾個彎以後,我看到一塊設計時尚的透明塑膠板子,上面寫著“TurquoiseMountain”。進門之後,能看到一個巨大的傳統四合庭院,正房共有兩層,都帶木質迴廊,迴廊做木雕拱券的裝飾,是我在喀布林見到的最好的院子。一位西裝革履的先生出來迎接我,詢問我的身份。在得知我到阿富汗是專門為了看文物古蹟,並且在不到十天的時間裡去了那麼多地方時,他的眼睛都亮了起來,不由分說就抓著我進了辦公室,要給其他朋友介紹。
一位坐在電腦前的姑娘站起來跟我主動握了手,向我講述這個地方的來歷——這是我在阿富汗唯一一次和當地女性有肢體接觸。辦公室所在的建築內部,裝飾更加精美,牆上都是灰泥雕成的花紋,傢俱應該都是從各處收來的古董。姑娘說,綠松石山的名字來源於古爾王朝首都的別稱,這個都城可能位於前文提到的賈姆宣禮塔附近,體現了這一機構創立的初衷,就是關注和保護阿富汗的文化遺產;在實際操作中,還包括了對傳統手工藝和裝飾藝術的保護和傳承。這個機構2006年由英國的查爾斯王子和阿富汗前總統卡爾扎伊共同設立。設立之初,它就選擇了位於喀布林河北岸,喀布林歷史街區中最好的穆拉德(Murad)片區進行修繕。十多年來,總共修繕了100多座歷史建築,並把辦公地點、培訓機構和工廠都安放在了最大的兩個院落中。隨後她給我播放了綠松石山的宣傳片,詳細展示了這些宅子修繕的過程。現在綠松石山的實際負責人,正是2003年徒步穿越阿富汗中央山地的英國人羅瑞·斯圖爾特。
一開始迎接我的那位男士帶我繼續參觀宅子的其他部分,其修繕工程甚至比我國很多地方做得都好,基本做到了儘可能少地替換構件,修舊如舊。參觀過程中,這位男士不斷詢問我這幾天去到的古蹟的現狀,很多地方連他們都沒有最近的資料,得知一切安好,他非常欣慰。在這裡的遊覽不斷開啟我新世界的大門……
……推離古宅的大門,再次看到那所有人身穿傳統服裝的雜亂街市,我感到很不真實。這個世界上偉大的人、偉大的事不算少,而這兩個低調的小院子,帶給我的震撼卻一直持續至今。在阿富汗這樣動盪的國家,很多驢友包括我,前去叨擾一遭,回來就書寫自己壯烈的行程、神奇的遭遇,乃至從中擠榨出的悲天憫人之心,實則於己於人都毫無進益。而這樣的機構,就這樣不急不躁地運作在那裡,對文化遺產的保護自不用說,長久下去對社會潛移默化的影響,更應讓人敬畏。
作者:劉 拓
編輯:蔣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