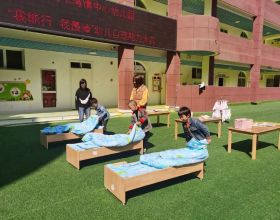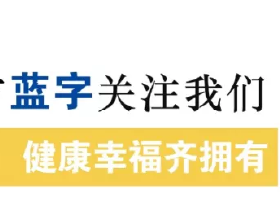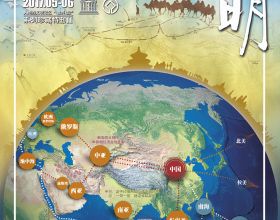農場裡有一條渾身漆黑的狗,那狗高高的,四腿粗壯,尾巴高翹,渾身圓滾滾的,很是威武與強悍。
那狗是農場學二連餵養的,說是上屆學生連留下來的。我們連隊進農場時,這條狗就是農場的“老職工”了。那狗也有名字,大學生們叫它黑頭。
黑頭每天都在學二連的營房內轉悠,很少光顧我們六連的營房,雖然只隔個操場。黑頭與學生連的每一個學生都很熟,無論是哪個學生叫它,它都會跟著走,我們經常看到學生們帶它在農田裡、營房內、操場上、小路上嬉戲與追逐。黑頭也是學二連的寶貝,在那個無聊的年代,大學生們經常與黑狗嬉戲,拿它開心和取樂,並將自己捨不得吃的食品餵它。有時,學二連與連隊進行球賽,黑頭也會蹲在觀戰的學生們身旁,煞有其事地看比賽。學生連進了球,學生們鼓掌,他也會開心地叫上兩聲,好像在助威。
連隊的許多戰士很是喜歡黑頭,常常拿白饃饃引誘它,企圖讓它也忠實地跟著到大田裡澆水,鋤地,或者在小路上徘徊,但結果多以失敗告終。
(1970年,連隊戰友高福利{左}和王建華在奇臺縣8847部隊農場。)
常言道:好狗護三鄰。黑頭卻護著整個農場,只要農場的小路上出現騎馬或趕車的牧民和小屯村的百姓,黑頭就會狂叫著一路跟蹤,直至將他們送出場區。孟場長與孫副場長也很喜歡黑頭,時不時地也會看到他們在農田裡察看莊稼,身後跟著那條黑狗。
1972年初,大學生們都分配走了,學二連的營房空落落地悄無一人。黑頭在那空落落的營房內轉悠了幾天,深感無主喪家的悲哀和淒涼,終於耐不住寂寞來到我們六連。開始它只是在連隊伙房外轉,炊事員瞧著它可憐,餵給它些食物。漸漸地它好像找到了歸宿,慢慢地在連隊營房內活動起來。有了走動,也就逐漸地和連隊的戰士熟悉起來,並開始嬉戲逗樂,黑狗也就成了連隊的一員。
(1972年,十一班戰友合影。第一排左起:王文和、王建疆、侯孝則;第二排左起:胡振興、黃有才、張雲向;第三排左起:丁衛國、趙明華、湯明華。)
記得那年夏季的一天傍晚,也不知黑頭是偷吃了炊事班的肉,或是惹惱了哪個戰士,好像是犯了什麼彌天大錯,激起了眾怒,被繩子繫住脖子吊在四排門前的單槓上。那晚我就站在單槓的不遠處,雖沒多少同情,但總覺得可憐。黑頭開始還在四肢亂動,沒多久便直直地垂掛在單槓下,一動不動。後來,戰士們都說,這狗眼紅紅的,像是患了瘋狗病,不除掉要咬人的。
(支中餘,1968年江蘇響水縣入伍。)
這時,連隊的集合號吹響了,戰士們迅速返回班排,並集結好,呼喊著口號來到四排門前站隊。那晚,連隊要點名,點名的地點正好在四排門前。因為這次點名,黑狗才死裡逃生。
那天,連長李文恭、指導員劉榮茂都不在連隊,由副連長郭俊文主持工作。副連長在連隊集結時就來到了四排房前,看了看掛在單槓上的黑頭,搖搖頭,命戰士將黑頭放下來,解開繩索。
黑頭軟軟地躺在地上,沒有了喘氣和動彈。副連長踢了黑頭一腳,罵了一聲後,繃著臉站在了隊伍前。
(王建標,1968年江蘇響水縣入伍。)
(柏金建,1968年江蘇淮安縣入伍。)
那天好像是星期天,點名要總結上星期的工作和部署下星期的工作。當副連長將工作講完,話鋒一轉,說起了當天的打狗事。他的話沒說幾句,隊伍後突然一亂,人聲鼎沸。原來躺在地上的黑頭,一陣蠕動,慢慢地站起來,虛弱地立在當地,緩了好大會兒,方才渾身一搖,抖落灰土,試探著走了兩步後,方才搖搖晃晃地消失在夜幕中。
黑頭走了,隊伍這才安靜下來。副連長見黑頭沒死,這才消了氣,對這事批評了幾句,也沒追究責任者便宣佈點名完畢。
點完名後,打狗這事便在連隊議論紛紛。當時為什麼要打狗,始作俑者是誰?是侯孝則等壺關兵上次吃狗肉後還想再嚐鮮,還是炊事班賈建築等為保護連隊財產而大義滅狗?時至今日還是個迷,我曾經問過四排的不少戰士,但誰都說記不得了。
(賈建築,1971年河南新安縣入伍。)
(2020年,和賈建築在河南新安縣重逢。)
(侯孝則,1970年山西壺關縣入伍。)
第二天,黑頭沒有在連隊出現,一個月後,黑頭仍沒在連隊出現。黑頭不但沒在連隊出現,在農場裡也無了蹤影。從此,黑頭便消失了。
農場和連隊也沒將這事當回事,黑頭沒就沒了。春回大地,農場的農事多得很,誰還能將那條狗掛在心上。
四十多年後,當我們在一起回憶農場的往事時,方才記起那條黑黑的狗,眼前也飄起他那威武彪悍的身影、奮不顧身狂吠著護衛農場的勇猛。
四排長袁家虎對我說:“你寫寫黑頭吧,它曾給我們留下不少記憶和快樂。”
(四排長袁家虎,1968年江蘇淮安入伍。)
(2021年,在江蘇淮安與四排長袁家虎重逢。)
附:
(張玉西,1968年江蘇淮安入伍。)
(張友生,1968年江蘇淮安入伍。)
感謝你的閱讀和欣賞,敬請關注《綠色印痕》的下一章節:“換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