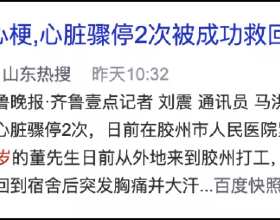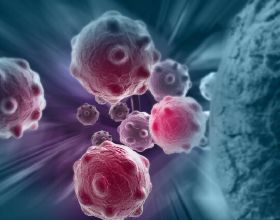文:蔡克舉
我下鄉當知青的時候,屯子裡曾經發生過一出誠是隔路的事兒啦,至今回想起來還是覺得挺招笑兒的。
屯裡有個叫二癟子的跑腿子,中午閒著沒事兒溜達到隊長家來了,想要跟隊長嘮嘮嗑,套套近乎,可不巧的是隊長沒在家,說是去市裡辦事兒了,要明兒晌午才能回來。他雖然覺得挺那個的,但還是不想白來一趟,於是就坐在炕沿兒上,沒話找話地和隊長的老婆嘮起閒嗑來了。沒成想隊長老婆不願意搭理他,自顧自地又是掃地又是擦炕蓆的,弄得二癟子總是得起身讓地方:一會兒得起身站在地中間,一會得到屋門口站著,一會兒又不得不重新坐在炕沿兒上,還得抬起腳來。就這樣,一會兒這嘎嗒,一會兒那嘎嗒的,折騰得二癟子心裡灰突突的很不自在。
二癟子和隊長家的北大倉酒
說來,這二癟子賊奸溜滑的也不是那種看不出聽的人,強熬了一會兒,他自覺苫不搭地挺沒趣兒,心想,咱這身價低,人家官太太不待見咱,咱也別太不識數,賴了哭吃的硬要呆在這兒啦,乾脆咱就腦瓜門子上貼郵票——走人吧。
無巧不成書,就在二癟子離開炕沿兒,剛要轉身走的時候,冷不丁看見窗臺上放著一瓶酒,黃個秧的,還以為是散裝北大倉呢,於是就假裝不外,也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拿起這瓶酒,掉過來掉過去的仔細撒磨,還裝的很內行地把鼻子對著瓶蓋兒,噝噝噝地聞了好幾遍,恭維地說,到底還是隊長啊,就是比俺們這些平頭百姓強百套,整天價都是好酒供著啊!
隊長老婆聽了,好像有點不樂意,說,你看你這嗑嘮的,誰供他呀?我就看他夜個兒晚上從老張家喝酒回來,拿著這一瓶酒回來,隨手就放窗臺上了,沒準兒是他們喝剩下的,人家客氣,讓他拿著的。二癟子立馬就接過話茬兒,卡麼卡麼眼睛說,你看,我就說的麼,隊長就是隊長,要麼怎麼叫隊長呢,跟別人就是不一樣,站長請客,喝的都是北大倉!然後,眼睛又是咪赤咪赤的,“不忍心”把那酒放回原處。
隊長老婆還有別的事兒要做,沒太多時間搭理二癟子,想要打發他快點兒走,就說,癟子,你要是真的饞了,就走它兩口吧,沒關係的,我這還要出去有事兒呢。二癟子等的就是這句話兒,也不管人家嫌惡不嫌惡,用他那幾顆黑門牙,嘎嘣一聲就把瓶蓋兒咬下來了,然後仰起脖頸,兩眼看著天棚,大嘴朝上,大半個瓶頸插進去,對著嗓子眼兒,咕嘟咕嘟就是兩口,大鼻涕都嗆出來了,完了還吭哧癟肚地連說好酒好酒!
隊長老婆盯著那酒瓶子一看,呵,好傢伙,說是走兩口,大半瓶子都進去了,就對二癟子開玩笑地說,二癟子,我讓你走兩口,你這一走就是大半瓶子,我這要是讓你走三口、四口的,那你就全乾光了唄?
那咋的,嫂子,你太小看老弟我這酒量了,說實在的,這算個啥呀!
隊長老婆想想,何不跟他開個玩笑,將他一軍,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還敢不敢總是吹牛逼!於是就用很瞧不起甚至很蔑視的眼神瞥了瞥二癟子,說,別把牛逼吹大發了,你還能把這一瓶子酒都走了還是怎麼的?
要說這二癟子,全屯子人都知道,雖說是好喝,但酒量並不大,平時三兩酒落肚就找不著北了,四兩酒喝了那肯定就要鑽到桌子底下不能出來了,可是這次他卻是不知咋回事兒,一反常態,雖說一口就走了大半瓶子,但是不但沒有找不到北,更沒有鑽桌子底下,反而還異常興奮,精神抖擻,就跟滴酒未沾似的,說,嫂子,你太小瞧人了,不要說三口,哪怕就是一口,只要俺想走,那也照樣能走進去!說著,又揚起脖子,像八路軍打鬼子站在山崗上吹起衝鋒號似的,嘴對嘴,一口氣就把瓶裡剩下的全走進去了,直把個隊長老婆驚得目瞪口呆,冒了一身冷汗,心想,得趕快讓他走,不然一會兒死在我家,這事兒就大了。
於是,她趕緊把地上的空酒瓶子和那個被咬癟了的瓶蓋兒踢進灶坑,拍拍二癟子肩膀,豎著大拇指說,海量啊兄弟,嫂子今天可真的見識了,怪不得人家都叫你二癟子呢!看來,人家都說你兩口就能把酒瓶蓋兒咬癟,這不是瞎話!要我看哪,應該叫你一癟子才對,剛才我看你一口就把我家瓶蓋兒咬癟了,哪用兩口啊?
二癟子雖說沒什麼文化,全加在一起才認得二百五十個字,但也知道在關鍵的時候和場合應該適當說幾句謙虛話兒,就笑眯眯地說,哪裡哪裡,過獎了。這時隊長老婆心裡有點發慌了,怕二癟子沒準兒幾秒鐘或者幾分鐘之內就有可能撲通一聲倒在地上死在她家,到那時她家可就遭殃了。於是,她也不假裝客氣了,一邊“叮囑”二癟子趕快回家好好休息,一邊就把二癟子推出她家門。末了,還一再叮囑二癟子,千萬千萬,跟誰都不要說是在我家喝的北大倉。
啊?好好好,二癟子更加興奮了,說,放心吧嫂子,我絕對不會跟別人說是在你家喝的北大倉,那要是讓別人知道了,影響該多不好啊,人家還以為你家一年到頭,指不定收了多少別人送的北大倉呢,人家還不得說呀,就連二癟子這樣的人都在隊長家喝北大倉了,那隊長家的北大倉肯定是多得都喂耗子了!
說來這二癟子好歹也算是個活了四十多歲的人了,打小兒十二歲就開始偷著喝酒,喝了大半輩子了,說實在的啥酒沒喝過呀?兩毛錢一斤的,四毛錢一斤的,五毛錢一斤的都喝過,可就愣是沒喝過北大倉,說來慚愧呀,實在是喝不起,哪有錢買呀,聽說好的要兩塊錢一斤那!以前每每聽人說起北大倉,他就饞的直淌哈喇子,今日終於如願以償了,而且還沒花一分錢!而且,而且,而且的而且,還是隊長老婆賞賜的,嘿嘿!
二癟子一邊往家走,一邊哼著喝酒小調:春風吹,戰鼓擂,老子喝酒從來不服誰,大腕幹,對瓶吹……哼著哼著,不一會兒就到了家。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就他這個懶蛋,往常中午是一定要睡個午覺的,否則一個下午都打不起精神來,就像捱了霜的狗尾巴草一樣——發蔫兒。可是今兒個中午他卻一點兒也不困,情緒激昂,心裡感覺特別的敞亮。他先是餵了喂剛買來的小豬羔子,又給小雞崽子撒了一把米,還破天荒地把小院子掃了掃,然後就又哼起了另一首喝酒小調:來一杯,再來一杯,品嚐美酒的滋味,來一杯,再來一杯,痛痛快快醉一回……。拎著一個細米兒扎的籠子,到草原捉蟈蟈去了。
而此時,隊長老婆正在家裡忍受著痛苦的心理煎熬。她一直是暗中害怕,整個一個下午了心裡也沒消停,簡直就如同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分分秒秒都不得安寧。她知道,喝酒喝多了搞不好是要死人的,這事兒以前屯子裡沒少發生;這二癟子,才二兩酒的量,只仰了那麼兩下脖兒,就把一瓶子北大倉走進去了,那呆會兒一旦酒勁兒發作了,口吐白沫翻白眼死了咋辦,怪誰呀?到時候他爸她媽他家七大姑八大姨的,抬著屍體往我家炕上就這麼一放,胡做亂鬧起來我這個家可怎麼辦哪?尤其是她媽那個老妖婆子更不是好惹的,啥損事兒都幹得出來!再說,就算是這二癟子命大不死,那胃肯定也得燒爛了,到時候他家那幫犢子們還不得把我家給砸了呀!俺自家老爺們能不能再當這個隊長了不說,這經濟賠償誰賠得起呀?再說了,那名聲也不好聽啊!
為了確認二癟子到底是死是活,隊長老婆急匆匆地就往隊部跑,由於心裡有事兒,煩得慌,一不小心右腳踹進水溝裡,腳脖子都崴腫了。這一路上,她逢人就打聽看見二癟子沒有,等到了隊部,又急不可耐地找副隊長,問派活兒時見沒見到二癟子。副隊長告訴她,下午二癟子根本就沒來,這就更加劇了她的擔心。
下午天氣太熱,路上沒幾個人,她又鳥不悄地跑到二癟子家,想要看看有什麼異常情況沒有,可是沒等她進院,二癟子家那條哈巴狗就撲過來,狂叫不止。她不敢進去,也不見二癟子出來。心想,我還是趕緊回去吧,沒準兒二癟子已經倒在他家地上死了,或者胃穿孔躺在炕上,癱巴了。哎呀我的媽呀,太恐怖了!不想了,不想了,反正到時候要是有人問,我可是絕對不能承認他是在我家喝了一瓶子酒;再說了,我自己不說,別人誰知道二癟子是在我家喝的酒啊!假如二癟子沒死,胃穿孔了,指著我的鼻樑子說是在我家喝酒喝的,我也絕不承認!
二癟子和隊長家的北大倉酒
就這樣,隊長老婆提心吊膽地度過了一個下午,還東家串門西家串門,沒話找話跟人家嘮嗑兒,也沒有打聽到有關二癟子的什麼訊息;晚上了,她一口飯沒吃。她根本不餓,非但不餓,反而還覺得胃裡漲漲的,所以只好老不早兒地就躺在炕上了。可是,她畢竟是個女人,心裡裝不住事兒,輾轉反側一直到天亮也沒睡著覺,熬得眼圈兒發青。這一夜,她一直在絞盡腦汁盤算著:如果二癟子一旦死了,公安局來調查,是否能查出他是在俺家喝的酒?如果真的查到俺家,俺應該如何搪塞,如何死不承認;如果老爺們回來了,要是問起俺他那瓶北大倉哪兒去了,俺該怎麼回答?嗨,就說是俺不小心碰到地上摔碎了。又想,死活都不能告訴他酒是被二癟子喝了。因為雖說老爺們這玩意兒一般都嘴硬,可是一旦被公安局叫去調查,誰能抗得住那頓打呀,人家一打他,萬一上個老虎凳啥的,他實在受不了了,就有可能招了;就算是不打他,公安局那些人都鬼道,就俺家老爺們那石頭腦袋的,能禁得住人家騙啊,逗赤逗赤的他就有可能說漏嘴,供出來了。對,絕對不能跟他說,這事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就我一個人知道。可是,第二天中午,她不但知道了二癟子啥事兒沒有,還烏鴉嘴瞎叭叭給她家造了不少的謠,這使她既感到慶幸同時又感到氣不打一處來。
原來,二癟子到草原捉了兩籠蟈蟈回到家裡已是傍晚了,正在他還在嗝兒嘍嗝兒嘍地回味中午在隊長家喝的北大倉時,他的狐朋狗友二蛤蟆來了,又把他叫去和另外幾個跑腿子喝酒去了。他們這次喝的是五毛錢一瓶的糖渣子酒,基本上就是酒精勾兌的那種。喝了一會兒,二兩酒落肚兒,二癟子有點兒高了,就見他漲紅著臉,兩手亂比劃著,雲山霧罩地開始咧咧開了。他先是咧咧了一通誰家的媳婦好看,誰家的大姑娘長得醜,然後就開始說他今天中午是如何如何走了鴻運了,在隊長家裡撈到了一瓶北大倉酒喝,還說那北大倉是如何如何味道獨特,非同一般,喝了一瓶都沒醉,一點兒都不上頭,就是胃裡稍微有點兒燒聽慌,肯定是六十五度高度的,沒準兒七十度都可能有了。聽他這麼一講,那幾個一輩子只是聽說過北大倉,但是連影兒都沒見過的傢伙都羨慕不已,自嘆弗如,既羨慕二癟子命好,又羨慕隊長家好東西多,還一個勁兒地拍著桌子叫:命啊,這就是命啊,咱哥兒幾個的命咋就這麼的苦啊!
二癟子和隊長家的北大倉酒
第二天,全屯子就傳開了,都說是隊長家北大倉酒是如何如何的多,多得箱子裡櫃子裡碗架子裡到處都是,裝不下了,就哪兒哪兒亂扔,連窗臺上都是,這輩子都喝不完;還有的嫉妒得直跺腳,罵:他二癟子何德何能,隨便溜達到隊長家就能混到一瓶北大倉酒喝,喝了個夠,難道他家祖墳冒青煙了不成?還有的又添枝加葉地說,隊長家槽子膏和長白糕如何如何多,一盒子一盒子的摞在炕衾上,一直摞到房頂,吃不完都長毛了等等。
隊長老婆聽到這些議論,肺都要氣炸了,剛要去二癟子家找他理論理論,隊長回來了,後面還跟著一個小男孩兒。就見隊長剛一進門,就急了火燎地直奔窗臺去了,見窗臺上空空如也,楞了楞神兒,就問他老婆看沒看見窗臺上的一瓶汽油。他老婆聽了這話兒,也楞了,說,汽油,啥汽油啊,窗臺上啥時候有過一瓶汽油了?隊長說,你胡謅白咧什麼啊,明明這裡有一瓶汽油嘛,我自己親手放這兒的我還不知道?隊長老婆這時開始驚愕了,她說,不就是有一瓶散裝的北大倉酒嗎,夜個兒晌午叫二癟子給喝掉了。然後她就一五一十地把昨天中午二癟子來串門,如何把窗臺上的“北大倉”喝了的事情說了,弄得隊長哭笑不得。但是他馬上就臉色一沉,問,聽沒聽說二癟子咋樣了?那胃要是燒漏了,可是要死人的。隊長老婆一聽,趕緊就說,沒事兒,那傢伙不知道啥時候長了這麼大的酒量,一斤酒進肚,啥事沒有不說,下午還到草甸子上玩去了,晚上又接著和二蛤蟆他們繼續喝,我都偵查過了,死不了,再說,也沒聽說他胃燒壞了呀。聽了這話,隊長那個大長臉馬上轉陰為晴,一股腦兒把窗臺上那瓶酒的事兒說給他老婆了。
情況是這樣的:臨去市裡辦事兒的頭天晚上,大隊機務站張站長請他到家裡喝酒,喝的是塑膠桶裝的龍沙陳曲。喝完之後,臨要回家的時候,隊長忽然想起自己那個叔伯兄弟跟他說了好幾次了,讓他給弄點汽油家裡平時用用,所以就跟張站長說了要弄一瓶汽油。張站長說,多大一點兒事兒呀,不要說一瓶汽油,就是十瓶汽油又能咋的,走,我給你灌去。說著,張站長就隨手拿起家裡一個瓶子,迷迷糊糊地也沒看清是不是全空的,只是覺得裡面好像有點逛蕩逛蕩的,可也沒在意。兩人一起來到農機站,張站長拎起大塑膠桶,就嘴對嘴咕嘟咕嘟地往瓶子裡灌——灌的是一瓶子,撒到地上的五瓶子也有了。剛灌完,張站長老婆就風風火火地趕來了,說是他老爺們剛才拿來裝汽油的那個瓶子是裝酒精的,裡面至少有少半下子呢,是她下午剛從赤腳醫生那裡要來打算平時擦腳用的。可是她來遲了一步,這個瓶子已經被灌進去汽油了,裡面的東西成了酒精、汽油兩摻的了。張站長說,倒它,倒它,再重灌一瓶汽油。隊長說,哎呀,沒關係的,不用那麼純,我那兄弟家要點這東西也就是平時擦擦腳踏車車條和鏈子的。所以,隊長就拎著這摻了酒精的汽油回家了,進屋就隨手放在窗臺上了。現在跟進來的這個小男孩就是他叔伯兄弟家的孩子,是他剛才在自家房後遇見,喊他來拿汽油的。
現在,事情已經是再清楚不過的了:二癟子在隊長家裡喝的是酒精、汽油兩摻的“北大倉”——既有北大倉酒那黃個秧的顏色,又有北大倉酒那濃烈的度數;但是,這特製的“北大倉”竟然沒能把二癟子的胃燒爛燒穿孔,還真的叫人不得不歎服。哎,二癟子就是二癟子,他皮實著呢!
當然了,二癟子得了便宜還要賣著乖,白喝了隊長家的“北大倉酒”不說,還到處造謠扒瞎,好像是隊長平時利用職權收了別人多少好處似的,給隊長的光輝形象造成了不良影響;而這隊長呢,恰恰是個脾氣火爆的人,想當年打架鬥毆那也是屯裡的一霸,哪裡咽得下這口惡氣!所以他當即就帶了兩個人到二癟子家,進屋就把二癟子按到炕上一頓狠揍,把他右腿骨頭都打錯環兒了。
二癟子既沒錢看病,也不敢報案,趴在炕上一個多月才能下地,全靠他平時要好的幾個酒友輪流來照顧一下。打那以後,他又多了一個外號:二柺子。
注:下面畫橫線的詞彙系東北土話。
誠是:非常
隔路:古怪、特別、於眾不同
招笑兒:令人感到好笑、可笑
跑腿子:光棍兒、單身
看不出停:看不出內裡是怎麼回事、看不出門道
苫不搭地:沒人理睬、自覺沒趣
賴了哭吃的:賴皮賴臉的不顧自己臉面
撒磨:這裡看看,那裡看看、到處亂看
夜個兒:昨天
卡麼卡麼:眨一眨
走:喝
哈喇子:口水
吭哧癟肚地:吞吞吐吐的、下句不接上句的
眯赤眯赤的:半睜半閉地眨巴眼睛
癱巴:癱瘓
鳥不悄地:悄悄地
老不早兒地:早早地
逗赤:引誘、誘導
烏鴉嘴瞎叭叭:胡說、亂說
嗝兒嘍嗝兒嘍地:不停地打飽嗝
咧咧:說、亂講
燒聽慌:胃裡發熱、火燒火燎地
哪兒哪兒:到處、隨處
炕衾:東北農村土炕的炕梢處擺放的長條矮櫃子,用以裝被子
急了火燎地:著急忙慌地、非常著急
胡謅白咧:瞎說、亂講
逛蕩逛蕩:晃一晃、晃盪、搖晃
皮實:禁得住折騰、扛得住吃苦受罪
作者簡介:蔡克舉,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人,一九七五年五月赴齊齊哈爾市郊區插隊落戶,一九七八年五月返城,先後從事教師、公安、紀檢、文化廣電等工作,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