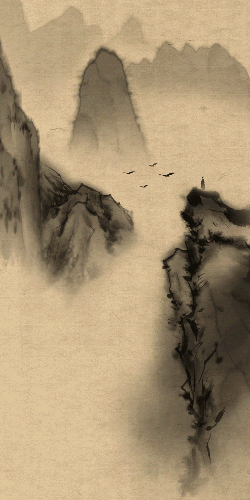一
唐開元年間,王沐為明州刺史。
王刺史性好雅靜,偏愛仙佛。
公務之餘,按月給自己排出日程:
上旬十天,清心寡慾以學道;中旬十天,沐浴焚香以參禪;末旬十天,喝酒吃肉養身體。
後院有十幾畝地,刺史叫人把凡俗的花木、彩砌的亭臺,能鏟的全鏟了,能拆的全拆了,所有帶煙火氣的東西都扔了。
鎖上院門,撂荒了兩年,直到它完全瘋長成一個荒園,才教人用竹子在園中搭起一個三丈高的高臺,名為“”招仙台,園子上又掛了個匾,叫“來仙園”。
從那以後,春秋兩季,蚊子不多的時候,太守天天在竹臺上過夜。
為了激勵自己,冬天也咬著牙蹲過兩宿,結果蹲出了重感冒和老寒腿,也就算了。
不為別的,就為了以示隱逸和高潔,等仙人來渡化和接引。
苦苦的支撐,勉強營業了一年,好像也沒什麼仙人光顧,倒是全天下成仙的奇聞異事灌了一耳朵:
誰誰誰入山訪道不歸,三十年後被樵夫發現在山澗下弈棋,容顏不改;
畫工為道館粉牆畫仙籙圖,偷偷添畫自己肖像,遂成仙童;
誰誰誰家貧無糧,入山採柏葉為食,久之身輕體健,通體異香,被封“柏葉仙人”;
王老二家的大黃,叼給討飯的乞丐一塊乾糧,結果被牽走了,只剩下一張皮;兩個月後群仙下界,寶馬香車,把王老二一家都接上了天;為首的一個長嘴的仙人,就是當初的大黃……
狗,狗都能成仙哪!
而且據家童說,王老二家就跟刺史的“來仙園”隔了一條街。
刺史大人很痛苦,幽幽清夜、捫心自問:
“我這是造了什麼孽嗎?
狗都能辦到的事兒,我不行?
我這個“來仙園”,成功的將神仙們遮蔽了啊!
眼瞅著街坊家的狗都成了仙,大人我準備了這麼多年都成不了,別人還以為我是故意的哪!
差哪兒呢?難道是……因為這院牆?
院牆太高,神仙爬不過來?”
拆!
一聲令下,只用了半天時間,原來兩丈高的牆磚院牆,拆得只剩下兩米。
果然,當天晚上就有了情況。
二
剛過了中秋半個月,晚上蚊蟲兇得很,露水又重,刺史叫人送來兩床棉被。
不只為了禦寒,院牆一拆,總有小孩兒淘氣,隔牆往裡打彈弓。
雖然夜色可以影響他們的準頭,奈何月光皎潔,他又穿了一身白。
牆拆完了,不知效果如何啊?
刺史大人不避艱險,冒著繩命危險執意“坐檯”。
更深露重,樹影婆娑。
刺史大人端坐高臺之上,圍了棉被,堪堪將要睡……醒。
牆外突然有了琴瑟之音,異香撲鼻,直沁大人的心脾。
睜眼一看,矮牆之外,燈火通明。
兩個童子提了水晶宮燈前導,後面跟了兩排腰肢纖細的侍女,全用白紗遮面。
人人手提花籃,一路走,一路撒花瓣,黃的,白的,黃的,白的。
再往後是四個力士,肌肉虯結,戴了面具遮臉,肩抬著一乘雲蘿暖轎。
轎簾一挑,轎中正襟危坐一位仙娥,玉骨冰肌,絕代的姿容,朝高臺之上略一招手,輕搖螓首、慢啟朱唇:
“妾身本月宮姮娥,嚮慕使君寒素,道心頗堅,特乘月色來拜。
此園荒悖,妾於與瑤臺設素齋一席,以結永好,使君可速隨我去……”
刺史大人,心花怒放啊,這見效也太快了吧!
所以說,姿勢不對必須起來重睡啊。
這個牆不拆,別說“招仙台、來仙園”,你就是把“喚仙、等仙、盼仙、催仙”的標籤全標上,也沒吊用……
拆個牆,仙人就來了啊!趕緊的,那還等個啥啊?
“隔牆疑是玉人來啊!”
大人風雅的吟哦著,爬下高臺,跨過短牆,跟仙女走了。
三
過了……大概有三天吧,大人回來了。
披著棉被,倚在門口喘氣,兩眼放光,但是失魂落魄。
夫人趕緊命人給架到屋裡,扶到床上,餵了兩口熱水,問他:
“瘋哪兒去了你?三天哪……”
刺史大人一臉得意的樣子:
“老爺我……我成仙了啊!”
夫人輕蔑的一笑:
“呦呵……那你怎麼又回來了啊?”
刺史大人一臉的意猶未盡:
“你不知道啊……瓊瑤仙宮,金堆玉砌啊,滿坑滿谷的月裡仙娥、國色天香啊……老爺我被奉為上賓,勸酒的勸酒,喂菜的喂菜……”
“等等,”夫人的眉毛樹了起來,“你說你去的是什麼地方?”
刺史說:
“夫人,老爺我去的是仙宮……瑤臺啊,那種地方,你永遠也去不了啊!”
夫人杏眼圓睜:
“去尼瑪的老爺,還瑤臺?窯子吧!”
刺史很激動:
“休……休要胡說!老爺我乃是有仙緣的人……”
夫人更激動:
“胡說?我就問你,你後院的白玉香爐、赤金雲磬呢?你的象牙笏板呢?你的碧玉簪青玉環白玉配呢?你手腕上的金手環、指頭上的翡翠扳指呢?你腰上懸著的寶貝田黃印章呢?都哪兒去了啊?”
大人有些結巴:
“供……供奉了啊!仙人們說了,我這一身人間俗物,如果不捐棄了,難證正道,這麼多年修來的仙緣將會前功盡棄、一切歸零。開始我也還有些難捨,仙人說幫我來斷舍離,來了四個力士,摁住我的手腳,把我剝了個乾淨,嘿,你別說誒,失去這些累贅,渾身一爽啊……”
“那叫渾身一爽?那叫渾身一涼好吧?然後呢?”
“然後……然後仙人說我靈根未固,還需再行歷練,這次先作罷,下次……再來……”
“還特麼有下次?
你特麼這是碰上“仙人”啦?
你這是碰上“仙人跳”了好吧!”
自此,夫人命刺史大人閉門謝客,畢竟,太丟人了啊。
四
王刺史拆了的院牆,夫人又給重新壘了起來,還在最上邊粘上了鐵蒺藜和碎瓷片。
再有“仙人”敢鋌而走險,極有可能會被紮了屁股。
保險起見,挨著牆根兒,還下了兩層老鼠夾子。
老鼠夾子再往裡,夫人又叫人挖了一條壕溝,深達一丈,不管誰掉下去都能修成“鐵柺李”。
園門上“來仙園”的匾額,高高的還在,但園子已經被夫人佈置成了“誅仙陣”,外防“仙人”,內防老爺。
刺史大人本尊,也被“監視居住”了。為了幫大人釐清修仙和奇遇的關係,夫人特意安排了自己的四位近侍,來負責料理老爺在內宅的飲食起居。
這“梅蘭竹菊”四位姥姥,本是夫人的媽媽的陪嫁丫頭,又成了夫人的陪嫁丫頭……
這四位骨灰級的“梅香”,整得老爺心如死灰、古井不波,漸漸的對紅塵俗世沒了一絲留戀。
大人天天唸叨著“向死而生”,琢磨著到底該怎麼“尸解成仙”,及早離了這沒滋沒味的俗世。
是圖好看用白綾子呢?還是整高階的直接吞金呢?
正糾結呢,有人來報,說定州大老爺家的二公子來拜。
五
刺史大人一下來了精神。
本家的親侄子來了,這個“客”,夫人那兒沒理由再謝了吧?
而且,這個大哥家的二小子王佐,跟他本人興趣相投,也是個好道之人。
這真是思賢若渴,想睡覺老天爺給送枕頭啊。
趕緊叫人請進來,叔侄二人一頓侃天侃地的寒暄,熟絡得沒大沒小。
夫人見他們叔侄情篤,也就任由他們喝酒胡扯,自己回屋溫習女德功課去了。
屏退了左右,王大人問他的侄子王佐:
“我侄子,最近功課怎麼樣啊!”
王佐回:
“小侄我蒙叔叔廕庇,天子賜了進士出身,正候補呢……”
王刺史說:
“……廢話廢話,問你那個了嗎?你那工作不是我給你安排的嘛,我不比你清楚啊?我是問那個……功課,那個……”
王佐說:
“嗨,我的親爸爸誒,五叔,不就是仙道的事兒嘛,直說不就完了?怎麼還藏著掖著的,跟逛窯……”
王刺史趕緊一把捂住他的嘴:
“嘿,小兔崽子,噓!這種事現在不能聲張,叫你五嬸聽見,我這月的餐標又得降……天天山藥黃精熬成粥餵我,靈芝茯苓磨粉當茶灌我,還派了她陪送過來的那四隻老怪物監視我,你看看我現在還有個人樣兒嗎?”
王佐偷樂:
“這不挺好嗎五叔,你這清心寡慾的正和道家的無為之態嘛……話說那四位姥姥,我六歲的時候她們就這幅尊容吧,這一晃十多年也沒個變化,駐顏有術啊。剛進來看她們亦步亦趨的跟著你,我還以為五叔你把她們給收了房哪……”
“胡說八道,胡說八道,”刺史大人拿筷子抽他侄子的嘴巴:
“小魂淡敢拿你叔叔開涮,別以為我疼你就捨不得打你……話說我再飢不擇食也不至於打破生殖隔離吧,就那幾塊料,估計你五嬸的爹我的老丈人,當初是當石獅子買回家鎮宅的……再笑?再笑撕你的嘴,你小子別閒著,有什麼奇遇給我講講,我這幾個月不死不活的,都特麼抑鬱了,道心都不……堅了,趕緊給你叔叔來碗雞湯吊吊命,快!”
王佐說:
“我的親爸爸誒,我五嬸把你迫害成什麼了這是?我就沒聽說過拿雞湯吊命的,不都是拿人參吊命嗎?看來你這不是道心動了,你這是胃裡的饞蟲動了啊……”
刺史說:
“小魂淡,別扯淡,到底有沒有……”
王佐說:
“……有倒是有,你不就想知道這世上是不是有真仙嗎?我還真碰上一位,準確點說,是我以為自己還真碰上那麼一位……”
刺史大人抿了一口酒:“說啊……”
六
王佐說:
“就是去年的事兒。
我不是得了進士出身,進京候補嗎?
當然也沒補上,到現在也沒補上,補上了我今天也不會來找你啊五叔,也就沒人給你講故事了對吧?誒,對了,你該不是為了聽故事才故意讓我補不上官兒吧?五叔?那你就太麻辣隔壁了吧?……別打別打,長輩也不能總打人哈,接著講接著講……
回家的時候,路過杜陵,荒郊野外的,景色殊勝但四野無人。
白雲變幻,野花自芳,滿川的秋色,自生自滅,但是依舊生機盎然,實在是令人感慨啊……
哎呦……五叔你有病啊,講故事不都得先抒抒情、寫寫景嘛,上來直接給高潮啊?那多不健康啊?你這是要喝雞湯的架勢嘛?我直接給你來個烤雞架多放孜然怎麼樣啊?……別鬧……馬上就入正題了。
我獨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糕點帶給外婆嘗一嘗……我去,我當然有糕點,我就不能有外婆嗎?你再打人我可惱了啊!就沒見過聽眾打說書先生的!
不是我說你,五叔,你在刺史任上這麼多年也沒個升遷,就是因為你文化水平……忒低。
文學!文學你懂嗎?
上來就要乾貨,聽有用的!我這不是公函,是文學!你明白嗎五叔,文學就沒有有用的知道了吧?
有什麼區別?
就好比你吃豆沙包。
五嬸正包豆沙包呢……是,我知道這娘們兒不會做飯,這是打比方哈。結果你忒猴急,上來直接挖了一勺豆餡吃了……這不叫文學。
什麼叫文學。蒸熟了,擺上桌,你老人家拿過一個,小口小口地細嚼慢嚥,仔細的品味,咂摸滋味,吃到豆餡的那一刻,甜……香……,這才叫文學。
什麼叫高明的文學啊?你看刺史大人的覺悟就是不一樣……這樣啊,還是五嬸做豆沙包哈。蒸熟了,擺上桌,你老人家還是拿過一個,小口小口地細嚼慢嚥,仔細的品味,咂摸滋味,帶著十二分對豆餡的期待,左一口右一口,興致勃勃的吃完了……完了,居然沒有餡兒,吃了個白饅頭。這就是高明的文學。
誒,不許動手啊!五嬸包豆沙包沒餡兒也正常啊,她又沒下過廚房……為啥會包出一個沒餡兒的?一上來你不是挖了一勺豆餡兒吃嘛?哎呦……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哎呦,刺史打死人咯……”
七
王佐接著說:
“咱們言歸正傳啊。
我不是獨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嗎?
雖然很窄,但還算官道,平坦坦的通向視野之外,一覽無餘。
路基往下,是滿坡的野草,再下邊是幽深的林子。
曠野無人,只有天籟相伴左右。
突然,右邊的林子裡,傳來一串清脆的銅鈴聲。
一頭瘦驢,馱著一個人,出了林子,沿著坡上的羊腸小道,噔噔噔噔的上到官道上。
小毛驢挺清秀,大眼睛水汪汪的,四個蹄子雪白雪白。
驢屁股上騎著個老頭兒,鬍子頭髮也是雪白雪白的,一張臉紅撲撲、樂呵呵的。
斜挎著一個鹿皮口袋,除此之外也沒什麼行禮。
我覺得挺好玩,也挺稀奇。
這個老人年逾古稀,一副樂天知命的樣子,獨自郊行曠野……看那旁若無人怡然自得的架勢,分明就像是綠野裡的仙蹤麼。
我趕上去,並轡與他搭訕:
“大爺您從哪兒來啊?”
看看我,不理我。
“大爺您這是走親戚啊?”
還是不理我。
“大爺您老貴姓啊?”
瞅都不瞅我了。
“大爺你這是回孃家嗎?”
這回理我了:
“我抽你信嗎?”
八
他怒了,老臉通紅,鬚髮皆張,一副雞毛撣子成精要吃人的架勢:
“你這小年輕的,沒事兒撩撥我老人家幹嘛?閒得你蛋疼啊?
瞎打聽什麼啊?
官差啊你?密探哪你?看我老人家像賊是嗎?你倒看看我渾身上下哪兒還能藏東西?敢惹我,信不信我死給你看哪?”
聲色俱厲,嚇死我了:
“誤會……誤會了啊大爺。我是純屬仰慕你啊!一看您就是個年高德劭、道貌岸然的高人,小子我不揣寒陋,願意效張子房學道於黃石公,陪伴您左右,為您牽馬、提鞋……”
老頭兒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有病吧,你?”
叱著驢就跑了。
我趕緊策馬跟上去:
“大爺,師父,神仙,您等我一下,我要拜你為師啊!”
老頭兒回頭鄙視的瞅了我一眼,說:
“我感謝你八輩祖宗啊!
我看起來像幾百歲的人哈?
老子我今年才三十三好吧?
笑話誰呢你?”
氣鼓鼓的騎驢前行,再也不跟我說話了。
九
我跟在後面,緊趕慢趕的追。
結果趕上一個硬彎兒,等拐過去,老頭兒不見了。
騎馬的居然把騎驢的跟丟了!
眼看紅日西墜,天已向晚。
路邊一個雞毛小店,推門進去,就一間房,一溜兒大通鋪。
大通鋪上空空蕩蕩,只歪著一個客人,正是那個老頭兒,頭底下枕著鹿皮口袋,正假裝睡覺呢。
我安頓好馬匹,從店主人那兒沽了一罈白酒,拍開泥封,酒香四溢。
老頭兒面牆而臥,聞見酒香,肩膀稍微抖了一抖,有戲!
我找了兩個椰瓢,把酒分好,滿屋的酒香繚繞:
“神仙大爺,整一口啊?還有燒雞下酒您不忌葷腥吧?”
老頭兒噌的一聲坐了起來:
“不忌不忌不忌……”
端起酒就喝,抄起肉就啃,片刻就吃成個醉飽,一鬍子的酒漬油膩:
“什麼三葷五厭哪五葷三厭哪,那是和尚道士的事兒,跟我老人家不相干哪,呵呵……你這小夥兒人不錯,知道體恤老年人嘛,嘿嘿……”
“你剛不是說你三十三?”
一罈酒,一隻雞,還有二斤豬頭肉,這飯量和牙口,我還真信他只是個三十三歲的白化病人。
這個真假存疑的老頭兒呵呵一笑:
“……大爺我也不白蹭你酒肉,如今長夜漫漫,走又走不得,就趁我醉眠之前,給你講點奇聞吧!”
我問:
“有多奇?”
老頭兒說:
“兩百年前的事兒,奇不奇?不講那些大頭巾在史書上編的故事,就講我親身經歷的事兒如何?沒錯,二百年前我三十三。”
十
老頭兒背靠著牆,盤腿坐好:
“那年我確實是三十三。
沒錯,如今是大唐,大唐之前是大隋,大隋時候南有大陳,大陳之前又有大梁。
宋齊梁陳都是南國的國號,我呢是北國扶風人,姓申名觀。
出生那年,北方還是宇文家治下的北周。
十八歲從軍,國號已經換成大燕了。
我投在公子瑾麾下,累積軍功,從士卒升為裨將,征戰了十五年。
三十三歲那年,隨軍去打梁元帝的荊州。
征戰半年,死傷枕藉。
荊州打了下來,主帥命令回兵,凱旋之師卻偃旗息鼓,沒辦法,一場慘勝的糊塗仗,倖存下來的都是些神智不清的殭屍兵。
那天,大軍屯在江陵。
軍中無事,我在帳篷裡悶頭睡了一下午,直到被晚飯的香味叫醒。
我坐起來,清清楚楚的記得剛剛做了夢:
只記得夢裡有兩個青衣人,對我說了幾句莫名其妙的話:
“呂走天年,人向住,壽不千。”
奇怪,詭秘,壓抑,心臟砰砰跳,不好受。
夢裡應該還有其他事兒,只是想不起來了。
我帳前的親兵是個精細人,見我衝著食案上的酒肉發呆,就知道有事兒。
我跟他說:
“做夢做得沒食慾啊!一點都不餓,嘿嘿。真有這好事兒,大軍的糧草都省了,一到飯點就睡覺唄,睡飽了就吃飽了……”
那個親兵說:
“嘿嘿,爺,那我這種成天睡不夠的,會不會撐得消化不良啊?”
十一
那個親兵陪著我,到江陵城裡找了個算命的解夢。
算命的這個人也奇怪,挺大的人不留鬍子,說起話來也不陰不陽的:
“你呀,當兵的命,到此為止了;當官的命,也到此為止了。
親兵說:
“他做夢,關我啥事兒啊?”
算命的說:
“本來也沒你啥事兒——說的都是他。”
我說:
“這個命也沒了,那個命也沒了,那我還能活嗎?”
算命的說:
“你只要把這兩條命丟了,剩下的命就會好好的……”
我抬槓:“那我要是就不丟呢?”
“那樣啊,你就啥命也沒了。”
我問他:
“那我這夢你還沒給解哪,先緊著嚇唬人哪?”
那人笑笑:
“你看啊……
夢裡的隱語是“呂走天年,人向住,壽不千”。“呂走”就是“回”字,“人向住”是個“往”字,這意思是要你趕緊回家,可得長生啊!”
長生?
這個詞好像塊磚頭一樣,砸中了我的天靈蓋,我像被誰開了瓢一樣,滿臉都是……頓悟!
這夢解得有點胡謅。
但是我本人已經厭煩了這連年的征戰,回營之後,就以此為藉口,向主帥告了退,準備解甲歸田了。
沒有跟至交好友告別,甚至連親兵也沒打招呼,我自己帶了路條,連夜偷偷離開。
天地之間,除死無大事。
回家之前,我又去了一趟江陵,那個算命的也還在。
十二
卦攤兒前冷冷清清,覓食的麻雀,像會飛的老鼠一樣躥上躥下。
那種亂世,命還值得算嗎?
不是打死別人,就是被別人打死,誰又有得選呢?
我坐下問他:
“官我也辭了,軍籍我也退了,明天就回家了。
這“呂走天年,人向住”,好辦。
那“壽不千”呢?
怎麼得長生?
就這麼等著,一年一年的捱嗎?”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說:
“你怎麼還執迷不悟呢?
我在這塵世等了你三十三年了,你怎麼還是沒一點長進呢?
你不認得我了嗎?”
我仔細想了一想:
“我敢確定,沒欠過你錢!”
算命的嘴巴歪了歪,一副瞧不起人的嘴臉:
“切……我說,你聽,能不能聽懂,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啊!”
十三
算命的說:
“你啊,如今是申觀,昨天是申將軍。
但三十三年前的你,叫薛君胄,家住梓潼。
沒錯,那是你的前世。
你前世好仙道,在鶴鳴山下買地,築了三間草堂,房前屋後遍栽花木、山泉巉巖竹影扶疏。
你遍訪丹書,服石嚼柏,日誦黃庭百頁,夜焚異香一屋。
你穿寬袍,戴峨冠,效古人竹林撫琴、月下長嘯,那嘯聲……把附近的野貓都引來了。
那天正是中秋,你對月獨酌,喝得有點上頭,開始喝佛罵祖的抱怨:
“我薛君胄恬淡如此,怎麼就沒有個仙人來渡我,我不配嗎?配!配!配!……”
然後,突然雙耳之間爆響,滾滾如有雷聲,頭疼欲裂,倒頭欲睡。
耳中的雷聲漸漸小了,換成滾滾的車輪聲,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晰。
一輛碧油小車,由一匹白馬拉著,從你的左耳出來,直接開到了枕頭上。
車上跳下兩個穿青衣的小童子,有青豆大小,跟你打了個問訊:
“呦呵,先生自在啊!剛才那一嗓子嚎得……真淒厲啊!
我們遠在兜玄國深山淨室裡打坐,都被你這聲如裂帛的叫聲驚醒了,你老人家……怨氣沖天哪?
我們主人說了,既然您這麼葉公好龍,那就跟我們回兜玄國吧?”
十四
薛君胄用睫毛打量了一下他倆:
“嘿嘿,你兩位豆芽仙人,沒事兒消遣我老先生啊?
你倆兒駕車從我的耳竅而出,想必那個兜玄國是在我耳中嘍?
你倆讓我同去兜玄國,試問我又如何鑽進我自己的耳朵眼兒裡去呢?
無稽之談嘛!”
兩個小童笑了:
“你老人家還真是沒有仙根哪,居然在這種沒品的事情上糾結。
我兜玄國幅員萬里,又怎麼會在你的耳蝸之內?
如若不信,跟來看看嘛!”
薛君胄搖頭:
“不去,不去。你們二位身不滿寸,如兩顆豆子相似,那匹馬有顆棗大?
如此推測,你舉國上下的人物,豈不都是些小小的耳蟲?
不去不去……”
兩位童子怒了:
“說誰是蟲子啊?你才是蟲子呢,朝生暮死昏昏聵聵的玩意兒!
你這無知的架勢,居然把我的道心都氣歪了,沒辦法,去也得去,不去也由不得你了,讓你見識一下什麼叫仙境,強過你在這兒醉生夢死……”
說完,身形爆長,一把抓起薛君胄。
老薛一通嚎:
“來人哪,綁票啊!邪教組織啊!我……不是,你們好像沒辦法把我塞進我自己的耳朵裡吧?嘿嘿……”
童子說:
“早跟你說了,我兜玄國幅員萬里,怎麼會在你的耳中?
只是,進進出出,總需要個孔竅才好,既然你的耳朵不讓用,就用我的吧!”
說完,一個童子提起薛君胄,往另一個童子耳中一塞……就給塞了進去。
十五
薛君胄濛濛昧昧,轉瞬而至福地。
睜眼一看,晴天朗日,山川壯麗,花木扶疏,鳥飛魚躍,萬類霜天競自由,別是一派異國風光。
兩個童子,拖著他跳上一朵祥雲,一路拉拉扯扯,帶他來到一間大殿之上。
大殿富麗堂皇,遠非塵世可比。
高臺之上一具鑾駕,端坐著一位王者,披雲霞而戴虹霓,垂翠幔而升玉階。
四個綵衣侍者,分持青紅皂白四色玉圭。
兩個童子收斂起來,低聲吩咐:
“這是我兜玄國的主宰,玄真伯,趕緊叩拜……”
薛君胄畏上,麻利兒的就給跪了。
大殿上閃出一個侍者,宣讀敕文:
“肇分太素,國既有億。爾淪下土,賤卑萬品,聿臻於如此,實由冥合,況爾清乃躬誠,葉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為主籙大夫。”
薛君胄不知如何應對,一個童子用手使勁兒擰他:
“快特麼謝恩哪,你現在工作有了,護照也有了啊……”
十六
薛君胄被安排做主籙大夫,但其實無事可做,因為他……不識字。
兜玄國的字,又小又怪,不光是認不得,想學也看不清。
薛君胄閒來無事,每天在班上聽人彙報,隨口吩咐。
開始他還煞有介事,後來發現自己是自作多情啦,不管他怎麼吩咐,下面人該幹啥還幹啥……
他就是團空氣啊!
憋著壞惡搞了幾次,胡亂吩咐,下屬也只是交頭接耳的怪笑兩聲,絲毫沒出亂子。
他明白了,自己就是個酸菜魚,又酸又菜又多餘啊。
心也灰了,意也懶了,班兒也敢翹了,事兒也不管了。
閒極無聊,登樓遠眺,無限惆悵。
拿了筆胡圖亂畫,順手謅了幾行字:
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
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
正獨自感慨,被兩個童子進來撞見,劈手搶了過去,一看就怒了:
“我去!
你就是個沒有根器的糊塗蛋哪!
憑空而得仙籙,不知珍惜也就算了,還在這兒長吁短嘆的思鄉。
瓊瑤仙宮你待著膩得慌,就愛你那個螞蟻窩啊?
你忘了當初了嗎?
當初是誰在螞蟻窩的那兒長吁短嘆、深夜浪叫,把我們兄弟噁心過去的?
行吧,既然薛先生覺得在這兒受了慢待,那咱幹嘛還要強留呢?
回去吧你!”
十七
雲程杳杳,瞬息而至。
薛君胄一身蔽衣,又回到舊居處。
山還是舊山,樹還是老樹,但小溪已經改道,草堂已經坍塌了。
走下山,訪四鄰,都目瞪口呆的一臉懵逼:
“還以為你讓狼叼走了呢,薛先生……你這些年,是去要飯了嗎?”
兜玄國幾個月,人間已經過了近十年。
之後又過了幾年,薛君胄因病而亡。
薛君胄死了,才轉生為你,申觀申將軍。
如今你在這個塵世,又歷經了三十三年了。
我這麼說,你能跟上嗎?”
算命的一臉疲憊的說。
十八
我跟他說:
“繞是繞了點,但還沒被繞糊塗。
你的意思是,我前世叫薛君胄,到過仙界叫兜玄國,因為不合群兒,又被遣返了,是吧?
後來他沒了,才又有了我,對吧?
那……你又是誰呢?
怎麼可能知道的那麼清楚?
即便能占卜,又怎麼會清楚彼時彼地的每個細節?
你不會就是……”
“沒錯,”算命的說,“我的前世就是那兩個青衣童子中的一個……”
“哪一個?”
“負責來回塞你的那一個。”
“那……你一個仙人又轉得什麼世啊?也思凡了嗎?”
算命的撇撇嘴:
“我懶得理你。
就是你上次被遣返,走得太急,沒給你帶齊術後的口服藥……
上次是你非嚷嚷著找仙人來渡你,結果真到了仙界,發現你這個人還真是葉公好龍,俗骨未褪盡,所以只好把你送回來。
但是走得急,忘了一樣東西:
本來位列仙班是可以長生的,你一個被貶之人自然不能長生,但是按規定,謫仙也可以有千年的壽命。
這個符籙……”
說著,他從口中扯出一條紅緞帶,上面是泥金的符咒:
“……這個符啊,忘了給你別在後背上了。
等我拿了符籙追過來,薛君胄已經死了,你申觀申將軍也已經三十三了。
所以……我現在給你別後背上吧,也算交差了啊……這跑得我上氣不接下氣的。”
說完,紅光一閃,符籙化進了我的身體。
那個算命的隨即變成一個童子,然後就不見了啊。”
老頭兒這麼說,說得口渴了,又灌了半瓢白酒。
十九
我聽得津津有味,都特麼餓了,問他:
“那您老人家……”
老頭兒拍拍肚皮,呵呵一笑:
“我老人家,在世上已經浪了二百年了。
真是活膩了啊!
草木榮枯,生老病死,興亡迭代,黃河改道都見過幾次了,也算是見識了滄海桑田了……
你不信?那我也沒辦法啊!
這個鹿皮口袋裡……”
他解開口袋,掏出一沓字紙:
“這兩百年來,有些大事我都記在上面,都是親眼得見,絕非道聽途說……感興趣我擇兩條給你念念?”
我說:“那感情好,求之不得啊……”
他念了兩條宮帷密事,果然是聞所未聞、駭人聽聞、三觀震裂啊……
再後來,我還想聽,結果老頭兒睡著了。
我把那些字紙拿到燈下看,密密麻麻的像螞蟻一樣的小字,一個也不認識。
再一會兒,燈油沒了。
我偷偷的把字紙藏了兩頁在懷裡,也睡著了。
第二天天一亮,一摸鋪上,老頭兒沒了。
我跳起來問店家,店家說:
“公子,昨晚上你喝多了吧?
太嚇人了,我也不敢說話。
你對著牆上的那張年畫,溜溜的白話了一晚上啊……那可真是熬到了油盡燈枯啊。
我也不敢勸,你就那麼坐著,一愣就是半天啊!
末了還把我家那張年畫撕了,揣懷裡了,你看這……這……”
我往懷裡一摸,還真是張畫,開啟一看,胖娃娃抱大魚……
但是,五叔,我再一摸,懷裡還有兩張紙,對著門口的天光一看,密密麻麻的盡是不認識的螞蟻字,就是昨晚上我藏起來的那兩頁“仙書”啊……
然後我也蒙了,說:
“畫壞了不要緊,我買了,燈油錢我一併還你。就是你得先告訴我,昨晚上那個老頭兒往哪個方向走的,啥時候……”
店家一臉懵逼、活見鬼了似的:
“哪有老頭兒啊,公子,我這間小店,整晚上就你一個客人哪。”
五叔,你說是不是很神異?”王佐說。
二十
刺史大人王沐,聽得有點如醉如痴,一時反應不過來:
“你小子……你先等會兒,我捋一下哈。
你是我侄子王佐,對哈?
你跟我講,你在杜陵郊野碰上一個老頭兒。
老頭兒自稱叫……申觀,說自己活了兩百歲了。
然後他給你講了個故事,說他在三十三歲上,夢見仙人給他留了隱語。
申觀找人解夢,算命的又給他講了個故事,說申觀的前世叫……薛君胄,曾經到過仙境兜玄國,還入了仙籍。
後來被貶回人間了,死之後轉生成申觀。
申觀,也就是那個老頭兒,得了本屬於薛君胄的長壽符,能活一千歲。
後來你跟申觀老神仙喝酒,他喝多了,你偷了他兩頁紙,對不對?”
王佐說:
“對啊,五叔,一點都對啊……”
王刺史目光炯炯,一臉肅穆:
“那……紙呢?”
王佐顫巍巍的從懷裡掏出來,奉上去:
“知道五叔大人你好仙道,乃當世的大隱逸,這等仙人至寶,小侄我怎敢私藏?我藏著也沒用啊!寶劍烈士、紅粉佳人、仙境五叔,絕配啊!”
刺史大人臉上波瀾不驚,肚裡翻江倒海,仔細地翻看那兩頁“仙書”,果然都是螞蟻文:
“嗯,呵呵,你這小子挺孝順哈,你補缺的事不要著急,就是這……一個月吧,一個月準有訊息。”
王佐意興闌珊,又掏出一張破畫:
“哎,我是沒有修仙的命啊。
好東西緊著大人、長輩使喚吧。
這張破畫應該沒什麼用吧,我自己留個念想,也算是見過活神仙的證據,沾沾仙氣哈!”
剛要收起來,被刺史一把搶過去,據為己有。
“誒,五叔……?”
“小畜生不要吵,好東西要緊著大人使,知道吧?”刺史大人語重心長的開導:
“你小孩兒老老實實去做官,修仙這種清苦事兒,還是大人來做吧哈!”
“不是,五叔,我就算有了官做,這上任之前不還得有一筆調費嗎……”
“別廢話,別廢話啊!小孩兒……怎麼還護食啊?五百兩,給你五百兩!買定……鬆手,一張畫嘛!”
“評書廉頗”,故事多多,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