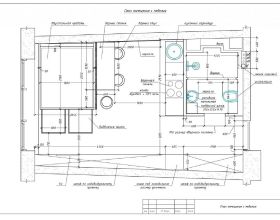摘要:近日一篇報道《困在光伏裡的農民:免費的陽光為何讓我欠了銀行20萬?》引起社會對光伏專案的關注,文中提到,在政策東風之下,一些光伏專案不僅沒有讓村民掙到錢,反而讓很多人困在了搭建光伏板的屋頂之下。無論在日照充足的北方村落,還是陰雨綿綿的南方山區,受影響的多是老人,他們對高科技、新能源非常陌生,卻陰差陽錯地交付出了原本追求安穩的晚年。
文丨姜婉茹 魏榮歡
編輯丨陶若谷
土地
一輩子種地為生的高晴喜今年60歲了,住在陝西神木和榆林交界處的一個村莊,村莊不大,總共200多人,只有四個姓,姓高的最多。大部分年輕人外出打工了,剩下20多個老人還在村裡,分散地住在山腰上。
高晴喜是留守老人中最年輕的,他夏天早上4點起床,冬天則是6點,每天和老伴一起伺弄玉米、大豆、高粱。“五個老弟兄”300多畝的地荒著,高晴喜栽上一種叫「山大王」的牧草,幾乎種滿了山頭。他和老伴一整天都待在地裡播種、翻土、澆水,“土地就是農民的命”。
村裡還在種地的老人,大概剩6、7戶,在各自的田裡勞作,常常一整天下來,也見不著一個鄰居。高晴喜還養了60只大羊和約140只小羊羔,沒有別的經濟來源,一年大約能有2-3萬元收入。
今年春天,連續兩個月颳起了沙塵暴,沙塵灌進屋裡,高晴喜不敢盛出鍋裡的飯,餓著肚子等沙塵過去再吃。家裡的羊開始咳嗽、害病、拉稀,買了藥也治不好,時不時死上一隻,高晴喜思前想後,認為都怪沙塵暴,“羊吃的草上沾了太多土。”
村子就在毛烏素沙漠邊緣,但這樣的沙塵暴已經許久未見。去年林業局發訊息稱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已達93.24%,村裡人以為沙漠即將消失,但今年的沙塵大到讓人睜不開眼睛。49歲的村民成子恍然又回到了小時候——站在一兩米遠的地方,只能看見一個人影,認不出人是誰。
十二三歲的時候,成子就跟著父親治沙造林。那是上世紀70年代初,村民們把樹枝剪下來,插在地裡,過兩年長成筷子粗細的樹苗,再背到五六公里以外的山樑上去種。成子每次至少扛三捆樹苗,約有二三十公斤重,父親背的樹苗則至少有兩百斤,中間成子實在走不動了,父親就罵他,罵完還是背不動,他就會捱打。
除了背樹苗,成子還背過草種,也不拘於什麼種類的草,只要能防沙固土,便都算是合格。人們把草栽成一個個小方塊,中間種上樹苗。種完就得步行去山頂的一汪泉水處打水回來。離水近些的林子,打趟水不到一小時,遠一些的,兩三個小時才能往返一次。
這條挑水的路成子從十二三歲走到了十七八歲,挑水的擔子壓在肩上,一壓就是半日,肩膀總是腫著,每日的勞動能掙到2-3個工分。年底村裡統計,欠了工分就沒什麼糧食領。
第二年春天去林地驗收成果,很多纖弱的樹苗沒挺過去,只好再背樹苗、種雜草、挑水澆水,兩輩人反反覆覆地補栽,這樣過了三四十年,防沙林慢慢長起來,沙塵暴也漸漸消失了。
沙棒、楊柳、沙柳、桑樹高低錯雜地生長,高大的能有十幾米,枝葉茂密的地方,都沒給人留下透過的隙縫。春天,漫山的紫黃色野花和野桑果會引來小鳥、野雞、野兔和狐狸,還有村裡的孩子們,桑葚吃得臉上手上黑乎乎一片。大人們採摘桑葚,曬成桑葚幹,泡果酒喝。
高晴喜住的地方離這片防護林最近,去年四五月份,他看到山上來了幾十輛推土機,把林地上的沙柳、沙棒、桑樹、柳樹、紫穗槐推平放倒,聲音震天響。
一開始他還在觀望,後來眼看著推到自己的地了,高晴喜沒忍住,跟施工隊理論,“這地不能推,我種的草根還在裡面,春天還要發芽哩!” 這裡種著他的「山大王」牧草,夏天可以餵羊,冬天能收割約1000斤草籽,以24-25元一斤的價格賣給草原站,這是高晴喜老兩口的主要收入來源。他直接站在推土機前面,護著地裡的作物,不讓施工。
他是村裡第一個看到推土機的人,其他村民只要住在山坡高處的,也都能看到推土機在工作,但他們都以為是那件事 —— 2019年9月,村裡來了能源公司的人,要搞光伏發電專案,需要佔用村裡的部分土地。
這是一種利用太陽電池半導體材料的光伏效應,將陽光輻射能直接轉換為電能的一種新型發電系統。如今土地推平了,施工隊已經架起不少水泥管子,要在上面安裝光伏發電板。
推土持續了好幾個月,起初高晴喜習慣了跟在外務工的子女報喜不報憂,沒給他們打電話。偶爾碰上一兩個同村的老人,說了這件事,可也沒什麼好辦法,“只有看著”。直到今年春天,回村的中年人發現防護林沒了,才開始找“公家”討說法。
矛盾越鬧越大,村民一發現施工就去阻攔,直到上個月鬧到媒體上。幾乎每個村民都對記者說,知道光伏要進村,“不知道會毀掉林地、佔用耕地。”
熟人社會的「合同」
光伏專案早在2019年9月就計劃進入村子,但隨後發生的事情出現了兩個版本。
“我們只允許他們進村裡施工,不知道要毀林。” 村民成子說。他和多位村民都提到一次開會,2019年9月,村裡難得聚起來40多人,光伏專案的工作人員來了,說要租用土地建光伏電站,付給村民租金,還承諾修一條6公里的砂石路。
按村民的說法,當時他們的關注點在於租金多少錢,什麼時候修路,會不會僱他們施工。至於具體用到哪塊地他們不清楚,有人以為是在林地上架起高高的水泥樁建光伏,林子還保留。念沒念過合同條款,在那個時候更是沒人在意,總之他們理解的是——“對生活沒有影響,還給租地錢。” 於是多數人簽了字,在那之後,每人收到了2萬元。
直到今年找到村委會,大家才知道村裡已經和光伏公司簽定了正式的專案合同——以每畝租金140元每年的價格,將村裡近2000畝地租了出去,租期25年。兩代人栽種的林地,高晴喜和老人們種糧食、牧草的800畝「糧田」,都在其中。
但事情到了村會計劉強那裡,呈現出了另一個版本。他站在當時引進光伏專案的村幹部一方,“他們(村民)沒聽到念「合同」的話,怎麼會摁手印?錢分到自己兜裡了,花完了就開始胡說八道。” 參與合同簽訂的更上一級村幹部對瀟湘晨報回應稱,村民所謂的被佔林地和耕地,實際上全是沙地,“專案手續是齊全的。如果是耕地林地,連手續都辦不下來。”
村民一方則拿出《林權證》反駁,證件顯示林種為「防護林」,使用有效期至2039年。還有村民說父親當過護林員,職責就是看護林地,阻止砍樹、放牧,“如果不是防護林,怎麼會專門僱他守林?”
10月28日,村莊所在的陝西神木高家堡鎮就整件事回應媒體,表示將詳細調查。從後續的調查檔案得知,租給光伏專案的土地屬於「宜林地」或「草地」。按照林業局政策,「宜林地」可以用於光伏電站建設,但要「林光互補」,不能毀林。
800畝「糧田」也划進這兩類,但村民認為有330畝是有土地證的「耕地」,其他的地也已經種了十多年,“跟耕地沒區別”,同牧草穿插著種,多年養護下來,土壤已經肥沃。
陝北這個村子的留守老人大多沒上過學,識字的很少,對法律檔案更是陌生。他們反覆強調“在那次按手印(簽字)之後再也沒見過合同”,事實上,他們簽字的檔案並非正式合同,只是一份會議紀要,見過正式合同的人就更少了。
光伏專案往往深入農村腹地,在籤合同環節出現問題這個村莊並不是個例。在河北邯鄲肥鄉鎮的一個村子,56歲的李光明聽了堂弟歸納的三句話——“不用花一分錢”,“8年後裝置全歸你”,“虧了公司兜底”,就把養老錢投進了光伏專案。
和西北集中式發電系統不同,李光明所在村莊是在屋頂安裝光伏板,採用的是貸款模式——村民跟銀行簽訂貸款協議,光伏公司提供免費上門安裝和維修,光伏板發電賣的錢歸村民所有,用於還貸。在大部分宣傳話術裡,電費能掙不少,還了貸款還能盈餘。
去年初冬,兩名年輕的女業務員開著白色小轎車專程到家裡接上李光明,到鎮上的工商銀行辦理「光伏貸」。沒有合同,只有幾張宣傳單,業務員承諾8年之後光伏板歸個人,期間發電收入如果少於貸款,差價由光伏公司承擔。李光明沒覺得有什麼不妥,他認定這是“一個發財的專案”。
到了銀行,李光明在表單上籤了30多次名字,總共貸款11.53萬元。這把在一旁等候辦理的同村小杜嚇到了,說要回去再商量。李光明替他可惜,“有鄰居想裝還排不上呢”,自己和小杜是因為堂弟的關係,才成為村子裡第一批有資格安裝的人。
堂弟在鎮上當電工,是村裡第一戶裝光伏板的人,花了6萬多。去年九月裝上後,村子裡沒多少人去琢磨那些屋頂上亮晃晃的板子是幹啥的。兩個月後的一晚,堂弟跑來找李光明,問他願不願意加入。
家裡十幾畝田租出去了,每年收租萬把塊錢,李光明和老伴身體也還行,除了日常吃喝花銷,就是買點降壓藥,能存下幾千塊。但他擔心日後一旦生病,這些錢支撐不了醫藥費。按照堂弟的說法,國家補貼8分,一度電能賣0.44元,光照好的時候每個月還能掙錢——掙筆養老金,他幾乎是當下就做了決定。
堂弟在村裡選了另外八戶人家,基本都是親戚和發小,有鄰居主動去找他,被告知變壓器有容量限制,沒申請上。在李光明眼裡,連同自己在內的這九戶,是村子600人裡“被選中的”幸運者,有沒有合同無所謂。
跟河北鄭堡村一樣,光伏板在山東臨沂楊集鎮的一個村子裡,也是由熟人介紹帶動起來的,只不過這裡的“擔保人”顯得更為可信,是村支書。
今年清明節返鄉,在外打工的張青田見到村支書,對方詳細介紹了光伏發電的好處,還展示了自家光亮亮的房頂。與李光明不一樣,張青田不用貸款買光伏板,只把房頂租給光伏公司使用就可以,租用價格是一塊板18塊錢。張青田夫妻常年在外打工,子女也不住這房子,空著也是空著,就答應了。
節後,光伏公司的工作人員上門籤合同,離開老家的張青田打電話給已出嫁的女兒,“去籤個字。” 不明前因後果的女兒抓起筆在業務員手指的位置簽下名字,一連簽了三份,業務員全拿走了,自家一份沒留。
在城裡上班的小兒子知道時,光伏板已經裝好了,問起合同內容,姐姐無法回答。作為家裡的文化人,小兒子跟光伏公司交涉要求返還合同。對方起初承諾10月底,後來延期到明年1月,理由是“錄入資訊程式繁瑣”。小兒子越發覺得不靠譜,不過聽姐姐說,每年領錢的地方“在鎮上的一家公家單位”,稍稍有了一絲安心。
無論李光明還是張青田,在辦理和安裝光伏的過程中都極為順利,除了村幹部的參與,光伏公司的推動,還有銀行的免息優惠。自2013年底開始,光伏企業在政策扶持下發展迅速,一時間全國很多村莊的房頂上都安裝上光伏板,有日照充足的北方村落,也有陰雨綿綿的南方山區。
但近幾年電價不斷下調,國家電費補貼標準也從2018年開始降低,雖然地方補貼還沒有完全取消,也已減少很多。不過,像李光明這樣的老人是搞不清這些的,只看到“光伏養老”的字眼在網站、短影片平臺到處都是,沒過多瞭解就簽了合同,想為自己買下一份老年安穩。
晚年
對李光明來說,被選中的幸運感一直持續到90多塊光伏板安裝到房頂上——住在同村的兩個兒子才知道父親借了「光伏貸」,他們告訴李光明,天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李光明心裡開始嘀咕,嘴上仍舊為自己的光伏板爭辯。那時他已經從銀行辦了兩張卡,儲蓄卡用來收賣電的費用,信用卡用來還貸款,每個月25號要存1499元。
一個月後電費只收益900塊,還差600,“幸好光伏公司會兜底”,李光明慶幸。然而,在還款日第二天他收到銀行簡訊,說貸款逾期未交,還要另繳納滯金67塊。種了一輩子田的李光明人生中第一次貸款,不懂怎麼回事,去問堂弟,以為光伏公司會幫忙還款,沒再理會。又過了三天,收到第二條催款簡訊,新增28塊滯納金,他趕緊拿出存款還上。
村裡其他幾戶也是收到催款簡訊才發現沒有什麼“兜底”。幾個人找到堂弟,堂弟也不清楚怎麼回事,至於自家的差額一直是光伏公司補貼,堂弟沒敢再提——作為村裡第一戶安裝者,又是介紹村民加入的“擔保人”,公司給了他和別人不一樣的優惠。
李光明想找光伏公司問清楚,但總是被銷售經理結束通話電話,他到鎮上一處商貿城找到了這家新能源公司,只有一張工位和一個沙發,“和小賣鋪差不多大”。笑臉盈盈的客服不斷安撫他,“別急,今年的天氣特殊,來年天氣好了就好了”。和上次、上上次說得一樣,像被設定好的程式。
李光明每次在鎮上的光伏公司見到的客服都不一樣,經理也換了好幾任,只在電話裡打過交道,當初開著小車到家裡接他的業務員早就不幹了。
自那之後,他沒敢再逾期還款,又回到了種田觀天的日子,日日盼望晴天。據說會扭轉盈虧的夏天終於到了,在5、6月光照充足的時候,一天最高的發電量達到200多度,能賣百十來塊。明媚的陽光在李光明心裡生出了希望,“是不是能回本了?”
對於安裝光伏的家庭來說,天氣直接決定著收入多少。湖南常德山區的一個村民在網上記錄過,在一個難得的晴天,發電量有140度,當天收入42塊錢,陰天只有28度,收入不到10塊錢,雨天更慘淡,“只有4、5塊。”
這個村民算過,除去陰雨天,一年中光伏發電板正常執行大概200天,按每天最多90塊收入計算,一年下來除去租金和維修費,到手1萬5千左右,至少五年才能撈回成本。
李光明算不清楚這筆賬。他止不住地可惜,壞天氣似乎太多了,還沒等填平前幾個月的虧損,就又陷入倒貼的陰霾。眼看小半年的地租都搭進去了,老伴忍不住埋怨李光明,也對他堂弟不滿。他嘿嘿笑著,說堂弟也是好心。
11月7日,暴雪降臨北方,雪片斜斜砸在光伏板上。李光明冒雪在院子裡細細檢視,發現有一根固定杆被大風拽離牆面一公分。他拍了下來,在朋友圈寫道,“今年是老天和光伏安裝戶徹底作對的一年”。
而在陝北毛烏素沙漠旁的村莊,村民並沒有像李光明一樣盼望陽光,似乎是充足的日照時間吸引來了光伏公司,在他們看來是“帶來了災難”——推土機進來後,沙漠從綠色變回黃色。有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家祭掃墓地,想起墓前綠樹成蔭,現在成了一片荒土,心裡不是滋味。
有人見過一個老人坐在路邊大哭,痛罵家裡的年輕人是“敗家子”,一畝地140塊錢(租金收入),“就把辛苦種了一輩子的樹給賣了。” 還有一個種地為生的老人,親手種的林子和作物都推平了,他說,“受下這麼大的苦,這把年紀再種,可種不動嘍。” 在當地方言裡,「勞動」被稱作「受苦」。
比起心裡的難過,留守的老人們還面臨更現實的困難。防護林砍掉之後,沙子還刮進了村莊賴以生存的二里渠。大生偶爾會回去探望80多歲的母親,他記得小時候二里渠的水“可大了”,奢侈到可以用來澆地,後來水小了一些,但一直夠吃夠用。今年沙塵暴刮起來,堵了水井,水泵常常抽不上水,連喝的水都供不上,等上三四分鐘,“抽上來也就一坨坨水”。
夏天缺水的時候,等上三五天也沒有水,大生說,村民只好趕著犛牛、騎上三輪、開著摩托,去一公里外的地方取水。有人拿200升的柴油桶,也有人用十幾個礦泉水桶拉水喝,兩三天就要去拉一次水。
大生是一名泥瓦工,今年40歲,在鄰近縣市的建築工地上接一些零活,養著三個小孩。800畝「糧田」被推平後,他開始對自己的晚年擔憂,農民工“一個留不住就要回家嘛”,到那時在外打工的村民們上了年紀,如果紛紛回村,地也許就不夠種了,那800畝「糧田」是他們最後的退路。
莊稼和牧草被推平後,60歲的高晴喜找了些荒地,種了點高粱,還沒到收穫的時候。這些地不夠肥沃,夏天地裡乾旱,“收成不好,只能喂喂牛羊。” 比如「山大王」牧草,種下去第一年不會有收成,等待根系生長需要時間。
由於住在光伏專案開發地的東南面,每當西北風從消失的林地刮過來,高晴喜就感覺是電影裡的那種風,“躺在沙坡上一會兒,人都能給埋了”。羊病死的太多,也不賺錢了,高晴喜現在靠以前的積蓄生活,對未來的日子沒了指望。
村裡人都希望要回800畝「糧田」,恢復1200畝防護林——雖然等林子重新栽起來,長到能擋住沙塵暴的程度,少說也要十幾年的時間。
(為保護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版權宣告:本文所有內容著作權歸屬於搜狐享有,未經搜狐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宣告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