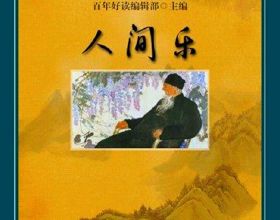偉大的靈魂在經受苦難時保持豁達與平靜,堅強、勇敢,永不會被絕望和庸俗的憂愁打倒。
面對苦難,不將過去看作是寂寞的,不將未來看作是恐怖的,而是一邊流淚又一邊大步向前。
“我是落花生的女兒”,在被現實一遍又一遍擊碎後,年已80的許燕吉落筆寫下這句話。
她沒有說自己是許地山的女兒,而是說了父親的筆名——落花生。因為她自己,就活成了落花生,一身傷疤,卻結出飽滿的果實。
深陷的痛苦的人,若是墮落,則跌入塵埃,隱沒於碌碌人間;若是奮起,則垂死掙扎,璀璨於短短一瞬。
可是許燕吉沒有選擇任何一條路,而是上善若水,任命運方圓。又沒有無動於衷,卻及鋒而試,擺脫命運桎梏。
這樣矛盾的兩種個性在她一人身上形成了和諧,才能使她在顛沛流離的日子裡,保留自己的一份赤誠的靈魂。
兵荒馬亂,人人自危,這樣的生活可以說是許燕吉記憶裡的常態,可讓人無法想象的是,她會迎來如此的飛來橫禍。
1950年,許燕吉考入北京農業大學,自父親死後,她和媽媽、哥哥相依為命,四海為家,如今考上大學,也算是圓了父親的遺願。
不僅學業有成,許燕吉還組成了家庭,並且孕育了一個孩子,幸福的家庭過得蒸蒸日上。
但是在那樣的年代,所有人的命運都無法自己決定,一雙無形的大手毫無預兆地壓下來,也不管這是誰的妻子,誰的母親。
1958年,許燕被單位開除,她只好去南京投奔母親,但是失去工作打擊和路途的顛簸讓她一個孕婦無力支撐,最終還是倒下了。
“生活在我們那個年代的人,說不清有多少人身不由己。人生被歷史的巨刃割得七零八落,如同摔碎在地上的泥娃娃,粘都粘不起來。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她在這次挫折中摔得粉碎,幾乎失去一切。
許燕吉流產了,當時月份已經很大,只能去醫院做手術,在母親肚子里長全了手腳的嬰兒,沒有啼哭地來到人間。
醫生告訴許燕吉,這是一個女孩。
一個女孩,許燕吉心靈的寄託。她想看她一眼,即使是沒有了生命的,但醫生不讓她看,怕她留下心理陰影。
當時許燕吉沒有堅持,因為她也不確定,此時虛弱的自己,能不能支撐住看這一眼,但是她當時不知道的是,這是她唯一的孩子。
“假如當時知道她是我今生的唯一,無論如何我都要看看她的。”即使許燕吉成為了古稀老人,時間也沒將這段傷痛帶走。
屋漏偏逢連夜雨,經歷了喪子之痛的許燕吉沒有丈夫的安慰,她的丈夫吳富融不僅沒有看她一眼,甚至對夭折的孩子都不聞不問。
1958年7月,一錘定音,許燕吉被判了六年的刑。此時吳富融在她的身上再壓一根稻草,與她離婚。
夫妻離婚原因很多,但鮮少有人直接是為了大難臨頭各自飛。吳富融就是這麼直接,他怕許燕吉拖累,在她定罪之後的五個月,提出離婚。
許燕吉最後挽留婚姻,寫了一封長信,她接受不了失去孩子又失去丈夫,但是吳富融沒留一點情面,直接將離婚鬧到了公堂之上。
吳富融的急切和嫌棄被許燕吉看在眼裡,尤其是吳富融對女兒的死竟然感覺慶幸,沒有留下後患。
於是許燕吉也清醒過來,吳富融絕非良配,他們之間的愛情與婚姻,也不過是紙做的堡壘,根本保護不了自己,更沒能保護孩子。
許燕吉終於碎得徹底,又終於無堅不摧,此時的她一無所有,只剩自己的生活,即使在牢獄裡,也是在過自己的人生。
面對時局的捉弄,無情的背叛,許燕吉沒有選擇怨恨別人,也沒有自怨自艾,始終保持內心的平靜和理智。
許燕吉自述,只傷心了一晚,從此就將這個人忘記了。
“五十流年似水,萬千恩怨已灰。萍聚何需多諱,鳥散音影無回。”她在之後寫下這首詩,送給了這段踽踽獨行的經歷。
她將打破她的拾起來,融在身體裡,成為她的一部分,在監獄裡新的一天開始後,許燕吉又是一個理性的人了,而此時,她才25歲。
監獄裡面有著規定,立功的人可以減刑,提前出獄,許燕吉畢竟是個讀書人,她很快了解這個政策,並且立下兩功,在她出獄一年前得到了提前出獄的資格。
五年的牢獄生活沒有把她壓垮,如今出獄在即,她望著看了五年的房頂,心裡是獲得自由的激動。
但是,就在她以為自己可以出獄時,一名獄警找到了她,獄警和她說,有一個犯人要五年才能出獄,而她還只剩一年,問她願不願意將名額讓出來。
這是多麼殘忍的選擇!
許燕吉五年裡心心念唸的,就是能夠離開,重新開始生活,可是就連這個願望,都不能順利實現。
但是她還是將機會讓出去了,她自己也是坐了五年牢的人,她明白,這是怎樣的煎熬,她自己淋過雨,如今也想為別人撐傘。
許燕吉默默將機會出讓了,她沒有把悲傷給別人看,而是讓淚留在了心裡。
她還是和往常一樣,和獄友一起起床,勞動,旁人也都無法想象,如此平和溫吞的她,做了如此無私的決定。
許燕吉不是一般的人,她不愛去遺忘,不愛去發洩,而是做人間的體驗者,鈍鈍地去感受,讓七情六慾都留下痕跡。
這是她一貫的做法,不讓悲傷流於表面,而是,把它放在心裡,那樣悲傷不會隨著淚水蒸發,可以銘記一生。
許燕吉這樣的性格,不是後天養成的,而是早在她8歲時,就有所展現了。
1941年8月4日,這是許地山帶著家人來到香港的第六年,他出差回家後就洗漱睡下了,誰知好好的人突然就面色青紫,沒了反應。
一家人亂成一團,強硬地拽來了護士,對他進行搶救,護士一邊對許地山的妻子急切地說:“你負責啊!”一邊將針扎入了許地山的胳膊。
這個瞬間放慢了一百倍,許燕吉睜著眼睛定定地看著,藥緩緩進入了父親的身體,哥哥捂住了眼睛,媽媽顫抖的手放在胸前。
這一切像一把沒有刃的刀,慢慢割著許燕吉的心臟,她沒有逃,她還在看,記清楚每一個細節。
死一般的寂靜後,許地山悶哼一聲,還是死去了,死因是猝死,搶救無效。
許燕吉的母親將手死死攥在胸前,指節都青白起來,微微顫抖,哥哥一邊哭一邊投入母親的懷抱:“爸爸死了呀!爸爸死了呀!”
母親將他攬在懷裡:“不要緊,還有我哪!”母子二人哭作一團,而許燕吉呆呆地站在旁邊,不哭不笑,彷彿局外人。
許燕吉她回憶時說,母親告訴她:當時她聽見哥哥的哭聲,突然醒了過來,明白自己還有責任,這讓許燕吉十分震動。
許燕吉摸著爸爸的手,沉默不語,周圍人的哭聲越來越遠,她只知道,父親回不來了。
她自始至終沒有掉一滴眼淚,任憑旁人哭成什麼樣。因為她此時已經陷入自己的悲痛之中,這是父親留給她最後的東西。
但是這樣的許燕吉並沒有受到理解,母親看著聲淚俱下的哥哥,又看見平靜的許燕吉,她大罵許燕吉沒有感情,屬無情無義之輩!
許燕吉把這句話連同母親的責任一起記了許久,她沒有反駁,因為她的文字就已經告訴了世人,她有多愛她的父親。
“如果上帝允許,我希望時間永遠停在前一天,父親不要走,我也永遠不要長大。”
只是這些寫得太晚了,許燕吉的母親沒有看到,她自許地山去世後,就對女兒不鹹不淡了。
其實這些早有預兆,他們的全家福裡,母親從來沒有攬著許燕吉拍過,甚至連一個手都不會搭在她的身上。
所以也能理解為什麼許燕吉說,沒有了父親,自己就只能長大。失去了父親,許燕吉幾乎失去了一個家。
就在許燕吉終於在1964年出獄後,仍然沒有和母親團聚。
此時的她已經31歲,人生最美的年華已經過去,按理來說她應該去投奔母親,療愈一下這麼多年的傷痛。
可她卻是再一次選擇監獄,並且遠離母親所在的南京,去了河北第二女子監獄工作。
有人說她是怕自己罪犯的身份連累母親,但是作為母親,怎麼可能忍心看著自己從小嬌養長大的女兒過那樣的日子呢?
因為此時母親已經認為女兒是個冷血無情的人了,她對許燕吉沒有一絲瞭解的慾望。
隊長將許燕吉的戶口轉到許燕吉的母親那裡,讓人沒有想到的是,母親不僅沒有接收,還將許燕吉的戶口給登出了。
母親當時說許燕吉鐵石心腸,是不仁不義的人,但是在母親這樣的對待下,許燕吉卻沒有埋怨。
被父親拋下,陰陽兩隔,她沒有哭。被母親拋棄,視若無物,她也沒有哭,還在脫離社會六年後,仍獨立找到了工作。
是多大的修煉和磨礪後,才讓許燕吉的生命起了厚厚的一層繭,波瀾不驚地去獨自面對慘淡的現實,仍然赤誠、理性、堅韌。
或許就是許地山的那一篇《落花生》,給小小的許燕吉無限滋養,讓她不懼怕人生受難,只願做一個內心豐盈的人,一個溫暖的人。
父親的去世,就是第一課,她把這一課的經驗用在失去孩子;婚姻破裂;母親拋棄等坎坷上,直到下一課,她用一生去完成。
1969年,許燕吉被疏散到河北省新樂縣一個偏僻、封閉的小山村裡,為了生存,她又開始了每天沉重的勞動。
因為這個村子十分貧困,許燕吉即使起早貪黑的勞作,賺的公分還沒有一頭豬多,甚至無法維持基本的溫飽。
這樣的日子她默默過了兩年,最後,她實在無法支撐了,就去陝西投奔在馬場工作的哥哥。
闊別17年,兄妹倆見面還有些生疏,看著對方滄桑的臉,兩人都有些唏噓。
只是,久別重逢的喜悅沒有維持多久,現實再一次壓了過來,許燕吉想要留在陝西,就必須和本地人結婚。
許燕吉此時沒有覺得自己多高貴,大學生、才女,這樣的稱號已經一文不值,此時她想要的,只是安穩的生活。
她和哥哥說,隨便找一個人嫁就行:“咱也不跟他談古論今。”
哥哥一夜未眠,自己的妹妹也是從小嬌養長大的,究竟是怎樣的磨難,才把她打磨成了這個樣子。
最終,許燕吉嫁給了大她10歲的農民魏振徳,他不僅是個文盲,還是二婚,帶著一個9歲兒子。
許燕吉沒有覺得不甘,反而深感生活終於穩定下來,從此她就有了一個地方歇腳,不用再四處漂泊,她與一切苦難都和解了。
一行淚從許燕吉的眼眶裡流了下來,她的淚很純淨,沒有悲傷的物質,只有多年內修後,提純出來的清澈——苦盡甘來。
或許是因為她的樂觀豁達,上天終於垂憐了許燕吉,魏振徳雖然目不識丁,卻勤勞、善良、忠厚,可以說是另一個落花生,兩人雖沒有愛情,卻可以相互扶持。
1979年,燕吉起早貪黑地辛勤工作,還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學習,終於又得到了一份公職工作。
此時的許燕吉不再是沒有戶口,沒有工作的人,這段婚姻也變得不那麼般配,可是她卻不這麼認為。
“我們就是過日子,不需要引經據典。我很坦然,覺得是命該如此。”
許燕吉抓住時機,結束了動盪的生活,但她不貪心,得到之後就滿足了,又回到平淡的生活。
1981年,根據政策,許燕吉被調回南京,在農科院從事專業研究,一年後評為副研究員,並且加入南京市臺盟當選為市政委員。
而魏振徳沒能和她一起,很多人勸她,給魏振徳一筆錢,結束這段不合適的婚姻,可是被罵作“無情無義”的許燕吉卻不同意。
“我和他可是一根苦藤上結出的瓜啊,我怎能丟下他呢?我當時被人踹了一腳,心痛了大半輩子,現在我可不能傷他的心。”
許燕吉都記得,那背叛的苦楚,所以如今她願意以己度人,為陪伴過她的老頭,撐起一把保護傘。
“我們的結合,就是各按各的方式活著,就像房東與房客,過去在關中,他是房東我是房客;現在在南京,我是房東,他是房客。”
許燕吉果然遵守了自己的諾言,將魏振徳接來南京,並且贍養他直到最後,兩人的生活也平淡喜樂。
許燕吉說自己是“麻花人生”,沒有多苦,只是比別人多了擰了幾圈。“快樂得自己給自己找理由”,這份豁達和溫和,成就了她的幸福。
她去世後,哥哥為她寫下一副輓聯。
“曾經風高浪急歷千苦,依然心平氣和對全生”,橫批“豁達君子”。
豁達君子,四字概括許燕吉一生足以。用溫鈍之心,品人生百味,用君子之德,行人世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