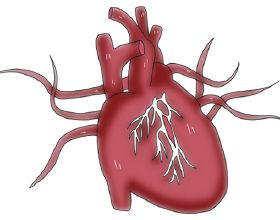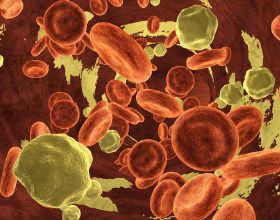對於那些些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我是個局外人,始終置身其中又置身其外,大多數情況,只是站在旁邊看看。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如今回首繁華如夢緲,寫這些時仍覺心驚膽寒。
我叫冷子興,都中一古董商人。往來於權貴之間,做些個金石買賣。做我們這行,沒個靠山膀臂如何生存,於是我蹉跎到二十大幾,終於娶了周瑞之女為妻,她藉此消了奴籍,我賺她孃家人脈,也算各取所需。所幸婚後和睦,彼此有個照應。
岳丈周瑞在賈府是個有體面的,管榮府春秋兩季地租,閒時帶少爺們出門。當年王家二小姐出閣,岳丈一家作為陪房,便一同跟著進了賈府。這位王家二小姐管過幾年家,不拿大,會待人,只是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後來王家長子的千金王熙鳳也嫁入賈府,深得賈母歡心。她姑母就把管家的重任交給了她。同是來自王家,鳳姐自是對岳丈岳母信任親厚些,那些銀錢賬目,出入來往,都肯與岳丈商量,故此賈府帑儲虛實沒有人比他更清楚的。
我愛喝酒,請勿見笑,酒品還不怎麼好。一次喝醉了酒,不知怎麼就得罪了人。對方拿住了我原籍不在都中這個短兒,把我告進衙門,說來歷不明,要把我遞解還鄉。可知他有靠山,我便沒有嗎?無非讓岳母向賈府說個情,稍動些關係使些銀子,哪有不了的。倒是內人沒經歷過什麼大陣仗,一副慌張摸樣,如今想著,著實可愛可憐。
我曾有個朋友,名叫賈雨村。我慕他斯文之名,只是愧覺彼此身份懸殊,不好攀結,他讀書清貴,我卻是混跡生意場的。他對我卻不擺什麼斯文架子,反倒讚我有大本領,我們倆說話投機,最相契合。惺惺惜惺惺,很做了些年的朋友。沒雙勢利眼如何在勢利場中混跡。雨村兄的勢利貪酷我是知道的,只是他不把這面對著我,也算看重我們的情分。
我這朋友初入官場不懂規矩,不久便被革去官職。為了生計,不得已去鹽政御史林老爺家作了西賓。他雖是讀書人,人情世故卻沒我通,權貴間錯綜的關係更是半點不知。巧的是當時我也在維揚地面,遇著他便給他尋了條出路。令他央求林老爺,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也就是王家二小姐的老爺,林老爺的內兄。果如所料,此後他一路發達。
世事一言難盡,誰曾料轟轟烈烈的賈府,說倒就倒了,百年大族的根基,垮起來竟這麼快。抄了家,坐了牢,我岳父岳母也受了牽連,從還好禍不及出嫁女,內子躲過一劫,雖日日擔憂父母,但也無可如何。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金石買賣的營生讓銀子如流水般進來,讓我窺見了賈府衰敗,也讓我攤上了官司。賈府過我手轉出的物件被查出是犯官財物。賈府是我主要的靠山,但是靠山如今倒了,連雨村兄都落井下石,我這商人又能奈何?無非是能推則推,散盡銀子保了條命。
經歷此劫,雨村的真面目我也見著了。戲文有一語‘公門雖好是非窩,穩便何如車下坡’,形容得再貼切不過。那雨村最終,也落得個身陷囹圄的下場。回想起當初和他小酒館對飲,他提到正邪兩賦,高談闊論,何等的意氣風發。我也是聽得人傳言,說雨村在牢內,每日唸唸有詞,重複來重複去,都是一句話: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冷子興寫於太平不易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