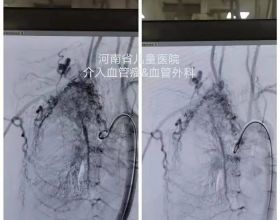一
能夠知曉天之所為,亦能夠知曉人之所為,這是知的極至了!知曉天之所為的人,能敏感地察覺到哪些內容是天生的自然的;知曉人之所為的人,能夠以其所知,保持對未知的敬與畏。人若能終其天年而不中道而亡,足以證明其知之充沛。
雖然如此,依然有疑惑。知天與知人的前提是已能區分天與人,然而天與人尚未區分開來,怎麼知道認為屬於天的內容就不能屬於人呢?或者屬於人的內容就不能屬於天呢?
正因為如此,有真人才可能有真知,是真人區分了天與人、區分了知天與知人。那怎樣的人才是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順其時。萬物皆有來時,有去時,有盛時,有衰時。時,是生命的歷程。若然,則過其時而不悔,當其時而不自得。若然,則登高不懼,入水不溺,入火不熱。這是因為真人趨近於道,既得天,又得人。
古之真人,眠入清寧,醒來無憂,其食淡,其息深。真人之息通透深沉,眾人之息淺顯薄弱。凡屈服於奢欲的人,其氣不壯。凡嗜慾深的人,其天機淺。
古之真人,泰然面對生死。出生也好,入死也好,不套牢於心。悠然而往,悠然而來。不忘生之所始,不求生之所終。受生而喜之,忘生而復之。人之心不湮滅於道,不追逐於欲,兼顧天人,這就可以稱謂真人。
真人其心忘懷,其容靜寂,其貌寬宏。真人和合於天然,悽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真人與萬物相宜。
萬物的本源是萬物之所歸,變化的萬物是眾生的表相。你喜歡的內容終歸於本源,你不喜歡的內容亦終歸於本源。一永遠為一,萬物的本源是永恆的;不一歸於一,是萬物歸於本源。本源與天共永恆,人與萬物共存。作為本源是屬於永恆的範疇,作為個體的萬物是短暫而差異的。天與人不相勝,永恆與短暫、同一與差異,本就集於萬物之體,並不矛盾。這就是天與人的統一,這就是萬物的本真。體悟萬物潛藏的本真,是為真人。
二
生死是生命的簡寫與究極。生之所來,死之所去,如夜之所來,旦之所去,由天不由人。許多事情由不得人,這就是世界的現實。人們以天為父,故而敬天,更何況卓然於天的存在!人們對於超越於己的人傑,尚且願為其獻身,更何況體悟本真之人!水源將枯,魚困於泥潭之中。與其像魚那樣陷於絕境之中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深陷於堯桀留下的是非,不如相忘於大道。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以為這樣就能安心了!若夜深之時有神力者把它偷走了,沉睡的人是不會察覺的。藏小於大,是合適的,但仍不能免於遺失。而藏天下於天下,就不會遺失了,藏己於己是物之真實。[人因自己的形骸而喜不自勝,但像人的形骸的內容有萬萬千千,那喜悅能算得清楚嗎。]故而聖人遊於物之必存,則人與物皆存。對於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之人之物,人們尚且效法,更何況那萬物之所繫、萬變之所依的終極內容!
道之於人,有情有信,無為無形。道之本可心傳而不可以物受,可心得而不可以形見。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之時就已存在;道造化鬼,造化神,道衍生天,衍生地。道先於時空,未有空間,你如何用空間的高深來形容道呢!未有時間,你如何用時間的久遠去形容道呢!
三
南伯子葵問女偊說:“你已年長,而神氣神卻如孩童一般,生機盎然。為何?”
女偊說:“我聞道了。”
南伯子葵問:“道可學得嗎?”
女偊說:“不!不可以!你不是學道的人。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沒有聖人之才。我想教他,或許他可以得道而成為聖人吧!即便不能成為聖人,以聖人之道與具有聖人之才的人溝通交流,亦容易領悟。
外天下是透徹人的紛繁,外物是透徹萬物的紛繁。生,是物的終始,對於生命而言就是生死,是物存在的整個過程。透徹生死,透徹物之短暫,透徹物之有窮有限,即達外生之境。達於外生之境,而後能朝徹。一切真實皆短暫,一切真實皆有窮有限,一切真實皆是表象,朝徹就是徹悟一切皆相。達於朝徹之境,而後能見獨。一切表象都潛藏著屬於無窮的本源。見獨就是見到這個本源。達於本源的無窮,即能達於穿透時間的永恆。永恆者不生不死,無生無死。
殺生者,生命終結的歸因。生生者,生命起始的歸因。殺生者與生生者,皆屬一源。此源不死不生,同於永恆,其謂道也。道之為物,將迎毀成,既陳述過程,亦陳述結果。道之將,物之迎;道之毀,物之成。道物之間,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這稱為攖寧。攖寧是道物的衍化。攖之於道,寧之於物。道之所虧,物之所成。攖而後成。攖是分,是毀,是虧。寧,成也。”
南伯子葵說:“你是從哪裡學得這些內容的?”
女偊說:“我聞於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於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於瞻明,瞻明聞於聶許,聶許聞於需役,需役聞于于謳,於謳聞於玄冥,玄冥聞於參寥,參寥聞於疑始。”
四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談:“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誰能知生死存亡為一體,我就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於是結為好友。
不久子輿生病了,子祀去看他。子輿說:“好神奇,造物者能把我變成如此奇葩啊。”子輿的身體已離常態,嚴重畸形了。他的身體已陰陽錯亂,可他依然閒若無事,信步來到井邊,看著自己的影子說:“偌!造物者又把我變得更奇葩了。”
子祀說:“你不覺得排斥嗎?”子輿說:“不,我為什麼要排斥呢?若我的左臂化作雞,我就用它來報曉;若我的右臂化作彈丸,我就用它去打鳩燒烤;若我的尻骨化作輪,我的精神化作馬,我就乘著它們出行,哪還需要車馬呢!得者,時也。生命的誕生是世界的偶然。失者,順也。生命的逝去是世界的必然。接受生命的誕生,然後安然面對生命的過程,最後坦然面對生命必然的結束。如此面對生命則哀樂不據於心,自然而然。古時稱如此坦然於生死為解於生死。生命不能超越生命而達於永恆,物皆有極,生命皆有極,這是生命的死結,是物之必然。物不能超越天,本就應該如此,有限怎麼可能超越無限。我又怎會排斥天的造化呢。”
不久,子來病了,氣息奄奄,人之將死。妻兒環繞著他,悲傷哭泣。子犁前往探望,見狀,對子來的妻兒說:“噫!請回避!造化將至,別驚擾造化之變!”子犁敬而遠之,對子來說:“偉哉造化!你將化為何物!你將往何處!你將變為鼠肝嗎?你將變為蟲臂嗎?”
子來說:“子女於父母,東南西北,唯命是從。陰陽變化於人,無異於父母,自然的死亡將近。我不接受,悍然反抗自然造化,而造化又有何過?天地的冥冥者啊!誕生我的生命啊,承載我的靈魂;讓我得以靠自己的勞動活在這世界;用歲月讓我歸於寧靜;用死亡讓我的生命歸於熄滅。善於創造生命的存在,亦是善於熄滅生命的存在。
大匠鑄金,那金忽踴躍地說:‘大匠!大匠!一定要把我鑄成鏌鋣神劍!’大匠必定認為這是不祥之金。現造化者將鑄形,我就喊著:‘變成人吧!變成人吧!’造化者必定認為我是不祥之人。[獲得人形就萬分欣喜。而如人一般的形骸萬萬千千,無窮無盡,那歡樂可算得清嗎!]天地為大爐,造化為大匠,我可以成為任意的存在!”
逝去如安睡,新生如覺醒,是一個獨立的新的開始與存在。
五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互相談論道:“我的相與,看似不及於你,其實終會及於你。我的相為,看似不及於你,其實終會及於你。大道無形,它像一隻無形的手、一個精密的系統,能傳遞你我之間的相與相為。誰能透過大道傳遞自己的相與,達到了無痕跡的境界?誰能借助大道發揮自己的相為,達到了無痕跡的境界?誰能乘霧遍遊天地,直到世界的盡頭?誰能圓滿地活在世上,直到時間的盡頭?”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於是結為好友。
不久後子桑戶去世了,將要下葬。孔子聽聞後,讓子貢去幫忙處理喪事。子桑戶家中,有兩人正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桑戶啊!桑戶啊!你已歸於本真了,而我們還是塵世之人啊!”見到此情此景,子貢很震驚,問道:“你們在友人遺體旁歌唱,合禮嗎!”二人相視而笑,說:“你還不懂得禮的真意。”
子貢回去後,將所見告知孔子,不解地問:“他們是什麼人?品行如此不端,衣衫不整,不顧形象,還在友人屍骨旁歌唱,對友人的逝去毫無悲傷,我都不知怎麼形容他們了!他們究竟是什麼人?”
孔子說:“他們是遊於形之外的人,而我們是遊於形之內的人。外內不相及,我讓你去吊言,是我的不該。他們能與造物者為伴,遊於天地之精華。他們將生看作多餘的肉瘤,將死看作潰爛的膿瘡。像他們那樣的人,又怎會在乎生死呢!生又如何,死又如何!生也好,死也好,不過是他們無限旅途的一站。道假於物,道物相融,同於一體。道物相忘,相忘以生。道物的完美相融,而生者自生。肝膽自在,耳目自在,人自在。自在即相忘。道物其實是一體的。道物相化,故物有始終,方生方死。道無窮,故物之始終亦無窮。同於大道者,縹緲玄妙,彷徨於塵垢之外,逍遊於無為之業。同於大道者又怎麼可能恪守世俗之禮,以滿足眾人的觀感!”
子貢說:“那麼您依從哪方?”
孔子說:“我是受著天之刑戮的人。雖然如此,我與你應共求天之大道。”
子貢說:“那有什麼方法嗎?”
孔子說:“魚相適於水,人相適於道。相適於水者,暢遊而自養;相適於道者,應物而自生。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大道。”
子貢說:“可否細說如此異人嗎?”
孔子說:“他們是異於世人而合於天道。故而,天之小人,足可以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只能算是天之小人。”
六
顏回問孔子說:“孟孫才的母親死了,他沒有痛哭流涕,不悲慼,居喪期間也不哀痛。他這樣子卻以善於處喪而聞名魯國,難道徒有虛名嗎?我覺得很奇怪。”
孔子說:“孟孫氏已盡得生死之實,他已透徹生死。世人皆求至簡之本而未得,而孟孫氏已達於至簡之本。孟孫氏不執著於生,不執著於死。不覺生之為先而死之為後。一旦化之為物,則已在萬化之大流,何所去何所往,皆為變數!
變化將至,你能確定不變又將如何嗎?變化未至,你能確定變化後又將如何嗎?我和你皆在睡在大化的夢中而未醒。同於大道大化者,形骸雖化而無損其心,無亡其情。孟孫氏在大化的夢中醒來了,面對生命的流化,他雖哭,但不戚不哀。
世人都說這就是我,但你怎麼確定這是真的我?你夢作鳥則翱翔於天,你夢作魚則潛游於淵。那現在談論著的我們究竟是醒著呢?或是在夢中?你能確定此刻的我就是真我嗎?
被動的應對不及積極主動的適應,積極主動的適應不及認清大勢所在,認清變化的大勢而不為變化所惑,即達於大道之本。”
七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問:“堯教你什麼?”意而子說:“堯告訴我,‘你須躬行仁義,明辨是非’。”
許由說:“那你還來這裡做什麼呢?堯既用仁義給你燙上烙印,又用是非給你行割鼻之刑。你還能遊於逍遙、自在、萬化之境嗎?”
意而子說:“雖然如此,我還是渴望遊於此境的邊緣。”
許由說:“不行。心瞎之人無法體會到世人的美好,眼瞎之人無法觀賞色彩的華美。”
意而子說:“美者無莊失其美,力者據梁失其力,知者黃帝亡其知,皆在造化大爐的淬鍊間變化了。你怎麼知道造物者不會磨掉我身上的烙印,修補我被割的鼻子,洗滌我的仁義是非,使我形神重獲新生,以追隨先生呢?”
許由說:“唉!也許吧!那我給你說個大概:吾師!吾師!調和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這就是遨遊的極致之境!”
八
顏回說:“我進步了。”孔子說:“如何進步呢?”顏回說:“我相忘於禮樂了。”孔子說:“好,但還不足。”
過一段時間後,顏回又對孔子說:“我進步了。”孔子說:“如何進步呢?”顏回說:“我相忘於仁義了。”孔子說:“好,但還不足。”
又過一段時間後,顏回又對孔子說:“我進步了。”孔子說:“如何進步呢?”顏回說:“我坐忘了。”孔子驚奇地問:“什麼是坐忘?”
顏回說:“突破形與實的約束,探求屬於生命的永恆;突破形與實的表象,探求生命的至真,謂之離形。知為一切經驗,穿透一切經驗的表象,觸及至真的存在,謂之去知。離形去知,同於大道,這就叫坐忘。”
孔子說:“同於大道之源,則萬物齊一。隨於大道之化,則萬物無常。你果真得到了天地之正啊,我願與你一起追隨於大道!”
九
子輿和子桑是朋友。雨一連下了十多天,子輿憂慮地說:“子桑恐怕要餓壞了吧!”於是帶上飯菜給他送吃。到了子桑的家門,傳來若歌若泣的聲音。原來是子桑鼓琴而唱:“父邪?母邪?天乎?人乎?”聲音孱弱而悲嗆。
子輿進了門,問道:“你為何如此悲唱?”
子桑說:“自己為何如此困窘,我百思不得其解。父母豈會希望我陷於貧困?天無偏私之覆,地無偏私之載,天地豈會特意陷我於貧?我想知道自己為何而貧,卻得不到答案。如今我面臨著如此絕境,這是我的悲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