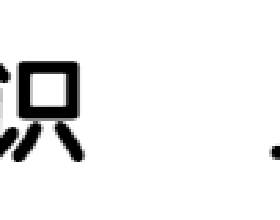馮沅君出身名門,與她的大哥馮友蘭、二哥馮景蘭,堪稱“一門三傑”;她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新文壇上才華橫溢、獨具風格的女作家,與蘇雪林、廬隱、冰心齊名,也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她與學者陸侃如的結合,曾被人稱作是一部充滿著“愛、自由和美”的奇特羅曼史。可以說,馮沅君的一生碩果累累,精彩傳奇。
才華初綻
馮沅君原名恭蘭,後改淑蘭,字德馥,筆名淦女士、大綺、吳儀、漱巒、易安、沅君等,1900年9月4日生於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上一個頗為富有的封建官宦之家,家中約有1500畝土地,是一個封建大家庭。祖父馮玉文,字聖徵,父親馮臺異,字樹侯,一生寒窗苦讀,追求功名,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中了第三甲進士,分發到兩湖總督張之洞幕下辦事。此時張之洞正在湖北武昌辦洋務,其中一項便是辦新式教育,馮樹侯就被委派為武昌“方言學堂”會計庶務委員(即外國語學校的總務長)。梁鼎芬當時為武昌知府,雖兼任方言學堂的監督(相當於校長),卻因公務繁忙,無暇顧及學校事務,而由馮樹侯一人負責。之後,馮樹侯又出任勘測粵漢鐵路的“彈壓委員”,不久,終於在他四十一二歲間被任命為湖北省崇陽縣知縣,成了主宰崇陽一縣事務的“父母官”。隨後,吳氏夫人便攜帶年幼的沅君及其長兄友蘭、二兄景蘭赴崇陽與父親團聚。
馮樹侯先生注重對子女的教育,在家設了書房,請了“教讀師爺”,給3個孩子上古文、算學、寫字、作文課。對沅君來說,讀古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古文讀起來有聲調,有氣勢,頗令人興奮。算學則是加減乘除,她覺得很乏味。此外是寫毛筆字。作文每週一次。年幼的馮沅君尤其愛讀唐詩,她喜歡讀詩可追溯至5歲的時候,父親教兄長們學唐詩,她便躲在一邊偷聽,幾遍下來便能一字不差地背誦。久而久之,到十一二歲時,她不僅能背誦大量的詩詞,而且還能夠吟詩填詞,故有才女之譽。馮家歷來有作詩家風,馮沅君的祖父馮玉文著有《梅村詩稿》,伯父馮雲異著有《知非齋詩集》,父親馮樹侯著有《復齋詩集》,姑母亦著有《梅花窗詩草》。馮沅君很會作詩,在山東大學袁世碩與嚴蓉仙教授合編的《馮沅君創作譯文集》中,收入了馮沅君大量的詩詞作品。
馮沅君
馮沅君的母親吳清芝,是位通曉詩書、思想開明的知識分子,曾擔任過當地女子小學的校長。吳夫人教子有方,除對子女親授詩書經傳外,還特聘請了一位名師嚴加訓練,即使對年齡最小的沅君,也從不因愛而廢嚴。這就使馮沅君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並打下了研究古典文學的堅實基礎。母親訓導她說:“不能徒恃聰明。讀書要紮紮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就像你大哥一樣。你大哥雖不如你二哥聰明,但他在不停止地往前走,從不間斷,這就厲害。”慈母的教誨,對馮沅君後來走上文學創作和古典詩詞研究的道路,起了啟蒙作用。可以說,馮沅君的未來是她母親的早期教育所奠基的。所以馮沅君後來每念及母親時,總是一往情深,念念不忘母女之愛。
馮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暫,在她剛滿8歲的時候,父親馮樹侯突發腦溢血,病逝於崇陽縣衙任中。那是1908年夏天,即馮樹侯出任崇陽縣官的第二年,正是春風得意之時,死神卻把他帶走了,儘管他走得那麼匆忙,那麼不情願。儘管馮沅君是那麼愛自己的父親,心裡充滿對父親無上崇敬、仰慕和愛戴,但無奈人生無常,事至可悲。
在父親病逝後的幾年裡,馮沅君跟母親及二位兄長,又返回到了唐河縣老家的大家庭中。自此,她只好在母親的教導和兄長們的幫助下自學詩書。沒過多久,她的兩位兄長紛紛離家遠赴開封、上海,進了大、中學堂。
馮沅君的這兩位胞兄都是新學堂的學生,在學校接受了一些新的東西,思想都比較開明。所以,他們平素在家中的言談及經常從外地寄來的新派報刊,使馮沅君逐漸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響。她不再滿足於深居閨中讀書習字的生活,她熱切地企盼像兩位兄長那樣,到大城市去讀書,受教育,汲取新的文化知識。
說來也巧,機遇從天而降,北洋政府決定將原來慈禧太后創辦的女子師範學校改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並於1917年開始招生。馮沅君得知這一訊息後,欣喜若狂,她與其兄說服母親,毅然隨兩位胞兄進京投考。當時,北京女高師入學考試只考國文一門,馮沅君自幼學習國文,有較好的基礎,自然是一舉考中了。就這樣,17歲的河南姑娘馮沅君成了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從此,她也開始了嶄新的學校生活。
名滿京華
馮沅君就讀北京國立女高師之際,正是五四運動席捲中國知識界的時候,“新潮派”和“歐美派”的教師們給女高師帶來了新的思想,所以當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紛紛走上街頭遊行、抗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的時候,北京女高師的學生便積極響應,投身到時代波瀾壯闊的革命熱潮之中。當時,北京女高師的方校長是一個思想頑固的老官僚,他不準學生上街參加愛國遊行,並下令緊閉校門,還特意派人在校門上加了一把大鐵鎖。然而,馮沅君卻無視學校的嚴束,第一個搬起石塊砸碎了鐵鎖,全校同學奪門而出,與北大、清華等校的師生會師。這件事使馮沅君在北京女高師獲得了一個勇敢無畏的好名聲,受到廣大師生的讚揚。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喚醒了一代有頭腦、有作為的男女青年。馮沅君,這個內心一直嚮往著自由與解放的青年女性,受到這個偉大運動的感召,勇敢地拿起筆,將樂府詩《孔雀東南飛》改編成古裝話劇,並親自登臺演出,主動扮演了劇中眾矢之的的封建專制家長的典型人物焦母(馮沅君的同屆同學程俊英飾劉蘭芝,孫斐君飾焦仲卿,陳定秀飾小姑)。女大學生登臺演戲,在20年代的中國,不能不說是一種極為大膽的行動,她也得到執導此劇的李大釗先生的稱讚和《戲劇雜誌》社陳大悲先生等人的支援。女大學生登臺演戲在北京是頭一遭,故而轟動了整個北京城,演出獲得了意外的成功,連演3天,盛況空前:第一天滿座,第二天以後就連窗戶外邊也擠滿了人。北大、清華的師生們還開了專車前往觀看,李大釗先生的夫人帶著女兒前去助威,魯迅先生和川島先生也都來看過戲。《孔雀東南飛》的演出,使馮沅君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寫文章說馮沅君此時是“名滿京華”。
李大釗(後左三)與女高師學生合影
女高師是北京的一流學府,這裡人才濟濟,集聚了不少優秀的教師。馮沅君的班級主任陳中凡,是位國學底子深厚、學識豐富的飽學之士,著名的經學專家;李大釗教授給學生們講社會學、倫理學和女權運動史,在課堂上宣傳馬列主義,號召學生反抗封建的忠孝節義,推翻舊的社會制度;胡適教授給她們講授《中國哲學史》,他是第一個把《新青年》雜誌介紹給同學們讀的老師。學者、名師們大膽的議論,深邃的思想,使青年馮沅君自幼受四書五經薰陶的內心世界大為震撼,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感覺、新體驗油然而生,一條嶄新而又廣闊的治學道路呈現在她的面前,這奠定了馮沅君的學術根基,也啟發了她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和對社會問題的關注。
馮沅君讀書有一股靈性,一旦用心,成績上升是立竿見影的事。她於1922年夏天從北京女高師畢業後,隨即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做研究生,研習中國古典文學。這樣她便來到“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宏材”的中國最高學府,開始了嚮往已久的大學研究生的生活。經過3年的勤奮學習,她又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而且是北大國學門唯一的一名女研究生。
時代的思潮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精神品質和審美情趣。在馮沅君就讀北京大學研究所期間,頗值得一提的是她以“淦女士”的筆名,發表在上海創造社刊物上的以《卷》為名的系列小說。這是她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特別是讀了創造社出版的新文藝作品之後,大開眼界,從而激起了無法遏制的創作熱情。此時,她表姐吳天的愛情悲劇,更給了她極大的刺激,於是她便以自由戀愛和封建包辦婚姻衝突為主題,從1923年的秋天開始,接連寫了《隔絕》《旅行》《慈母》《隔絕之後》4篇小說。這4篇小說雖然各自獨立成篇,而其內容、思想卻息息相通,其中心主題就是爭取婦女從封建壓迫下解放出來。
馮沅君文筆犀利,她向舊社會禮教挑戰的勇敢精神和爭取戀愛自由的大膽行動,深得魯迅先生的賞識。後來,魯迅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時,就選了《旅行》《慈母》兩篇,並給予了肯定的評價。
1924年冬,孫伏園得到魯迅先生的支援,在北京創辦了《語絲》。魯迅當時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學術委員,對馮沅君自然是十分熟悉的。因此,馮被聘為《語絲》的特邀撰稿人。馮沅君從《創作週刊》轉向《語絲》之後,由於受《語絲》的社會批判的影響,她的視線從單一的戀愛自由掃向了更廣闊的生活,文筆有了變化,署名也由“淦女士”改為“沅君”。於是,她便在《語絲》上連續發表了若干篇小說、雜感或考證文章。她寫的雜文,短小精悍,立意鮮明,語言犀利,表現出了一個追求博愛思想的女作家對現實不滿、憤世疾俗的態度,轟動了北京的新聞界,更轟動了文壇。可以說,馮沅君在文學創作上獨特的才能和驚人的魅力,主要是靠她的十多篇中短篇小說,在深受後代讀者讚賞的20年代中國新文學中佔有了一席光榮的地位,進入了蘇雪林、廬隱、冰心、謝冰瑩等女性作家的不朽行列。
珠聯璧合
馮沅君和陸侃如的戀愛,是從1926年秋天開始的。當時的陸侃如是清華大學研究院的高才生,英俊瀟灑,才華橫溢。他的《屈原》《宋玉評傳》等在學術界頗引人注目。他比馮沅君小3歲(陸侃如生於1903年11月26日,江蘇海門人),是年夏天從北京大學國文系畢業後,隨即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他除了研究《楚辭》,還協助梁啟超校注《桃花扇傳奇》。當時,馮沅君已是文壇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贏得了陸侃如的愛慕。由於業務上的相近,使他與馮沅君有接觸的機會,這位風度翩翩的江南才子,也深得馮沅君的好感。兩人雖然不是青梅竹馬,卻是一見鍾情。他們相識之後,就開始了頻繁往來、交談、通訊。陸侃如反覆向馮沅君表示純潔的友誼,接著就是純潔的愛情。每逢星期日,陸侃如都到北大來找馮沅君,他們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談心,或者在北海泛舟,有時也相約去遊長城,流連徘徊於頤和園的水榭、圓明園的古蹟堆中,或者是香山幽靜的小路上。經過海闊天空的侃談,雙方就再也分不開了。
馮沅君敬重陸侃如的品德、才學,她誠懇而又含蓄地向陸侃如表露了自己的感情:“我主張朋友間的感情要淡而持久。然而我們的友誼何以發展得如此快,我也不知道。鮮豔的花兒,祝你戰勝了一切風霜!”(《春痕》十四),文章雖短,但含情脈脈。從兩人“愛苗初長”到“定情”這一段愛情生活的歷程,約略地烙印在馮沅君於1927年寫的、由50封書信組成的中篇小說《春痕》中。馮沅君就是在這樣的創作與愛情的交織中,結束了為期3年的大學生活。
馮沅君和陸侃如
1927年秋,馮沅君到上海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大學部任教。不久,陸侃如也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應邀到上海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大學部、復旦大學任教。此時,兩人既是戀人,又是同事,從而也就開始了學術事業上的合作。他們共同研究詩詞、元曲,共同撰寫《中國詩史》,愛情的花朵也就由此而開放。然而,當馮沅君向大哥馮友蘭要求同意她與陸侃如的婚姻時,這位大哲學家卻未置可否,最後還是由蔡元培和胡適兩位先生出面寫信給馮友蘭,“請不必多問”,才終於成全了這樁婚事。1929年1月24日,馮沅君與陸侃如在上海一個春光明媚、喜氣洋洋的吉日裡舉行了結婚儀式,永結百年之好。
就這樣,馮沅君作為一個有才華的女作家,時代的洪流把她衝上了文壇,但傳統的負重和學者的生活卻又將她完全地拉回了書齋。此後,轟動文壇、為讀者熟悉的“淦女士”也便銷聲匿跡了。
婚後,他們仍專心從事教學與學術研究,終於結出了第一個合著的學術研究成果,就是1931年《中國詩史》的出版。這是繼王國維先生的《宋元戲曲史》、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之後的又一部具有開拓意義的中國古典文學專著。此著作被魯迅指定為重要的參考文獻,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直到今天,這部放射著耀目光彩的《中國詩史》,仍然是中國唯一一部詩歌史專著。繼這部書之後,他們夫婦又合著了《中國文學史簡編》,1932年由上海大江書鋪出版,列為“大江百科文庫”之一。此書是一部全面系統地敘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專著,是一部難得的佳作。此書多次再版,並譯成多種文字向國外發行,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馮沅君是個事業心很強的人,自然不甘心婚後充當一個有文化的家庭主婦的角色。於是,她又隻身應聘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學國文系任教,這是1930年秋天的事。北京大學是全國名牌大學,等級森嚴,以往沒有女教師登過講壇,而年僅30歲的馮沅君卻開此先河,登上北大講壇給學生授課。她講得充實而嚴謹,令人肅然起敬,從而腳踏實地地站穩了大學講壇,成為當時中國屈指可數的大學女教師之一。也正是由於這種強烈的事業心,她和陸侃如才節衣縮食,把工資和稿費節儲下來,計劃湊足1萬銀元后,一道去法國留學。
馮沅君夫婦是1932年夏天,從上海坐“達特安”號郵船離滬赴法國留學的。船經香港、西貢、新加坡、科倫坡、吉布提、蘇伊士等港口,經過一個月的航程,終於進入了馬塞港。抵達巴黎後,他們一起考進了舉世聞名的巴黎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班。馮沅君夫婦這次到法國是自費留學,沒有足夠的資金,也沒有顯赫的靠山,過著清貧而緊張的生活。生活的步履儘管艱難,但他們對知識的渴求並未減弱。1935年,他們學完了全部課程,並透過嚴格的答辯,終於以優異的成績,取得了文學博士學位。在當時,能夠取得法國文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可謂風毛麟角。
應該特別提到的是,馮沅君夫婦在留法期間,曾參加法國著名作家巴比塞組織的“反戰反法西斯同盟”的活動,這個同盟下設中國留學生支部,參加的人中除了馮沅君夫婦,還有著名詩人戴望舒、李健吾等人。他們在巴黎創辦了一張油印小報,由馮沅君夫婦負責編輯,為反法西斯的偉大事業盡了綿薄之力。他們還經常聚在一起討論世界形勢和文藝問題,討論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法文譯本問題。在這裡他們結交了法國和中國很多朋友,拓寬了思想和文學視野。他們的心胸和眼界,逐漸經歷了一個由民族擴充套件到世界,由世界擴充套件到全人類的過程。此刻,在馮沅君夫婦的心底,正醞釀著更為廣闊的發展宏圖。
報效祖國
1935年夏,馮沅君夫婦滿懷海外學子學成歸來報效祖國的希冀,乘坐華僑辦的中國郵船回到了闊別3年的故國。回國後,陸侃如去北平燕京大學任教,馮沅君則應聘到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院教書,直到抗日戰爭爆發。
這兩年間,由於生活的清閒,馮沅君夫婦對古籍文物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在課餘之暇經常去琉璃廠閒逛,在北平這條古老的文化街上,見到中意的古書、古玩,便買回家賞玩,常常把每月的工資花得精光,卻變成了收藏家。馮沅君夫婦在琉璃廠搜得古籍中,有一部世所罕見的《九宮正始》,於是,他們合作完成了這部南戲曲文資料的輯遺工作,編成《南戲拾遺》一書,在《燕京大學學報》刊出。正是這個偶然的機緣,使馮沅君的學術研究興趣,由詩文詞曲轉移到古代戲劇上,開始了對古劇的探討研究,並於1936年10月發表了著名的《古劇四考》等論文。
但是1937年七七事變盧溝橋的炮聲,中斷了馮沅君夫婦象牙塔的書齋生涯,隨之流離顛沛的生活開始了。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刻,馮沅君在北京耳聞目睹日寇入侵的種種暴行,悲憤不已,不禁沉痛地吟出“地室避兵朝復夕,親朋生死兩茫茫”、“連連槍聲疑爆竹,兼旬臥病意為哀”、“兩日悲歡渾一夢,河山夢裡屬他人”的詩句。次年春,馮沅君夫婦離開淪陷的北平遷到上海小住,後又取道香港、越南河內,改乘滇越鐵路的火車迂至昆明。由於戰雲密佈,局勢緊張,不久,陸侃如無可奈何,隻身應聘去了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馮沅君則去了暫遷到峨眉山下的武漢大學,而樂山很快也遭到日本飛機的大轟炸,他們只好輾轉迂迴粵北的坪石。1942年夏,馮沅君夫婦毅然再度入川,投身設在三臺的東北大學任教。3年後,終於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在抗戰的8年間,馮沅君的足跡遍及雲、貴、川、粵,飽受流離奔波之苦,但她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國家的危難和民族的存亡。在四川三臺期間,馮沅君夫婦積極投入愛國的抗戰文藝活動,他們受老舍先生的委託,組織在東北大學任教的文化名人姚雪垠、丁易、趙紀彬、楊向奎等,成立了“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川北分會”,由趙紀彬、馮沅君分別任正副主席,會址就設在三臺東門內陳家巷馮、陸住宅內。他們經常在馮、陸寓所聚會,研究抗敵宣傳,救濟進步學生,組織演劇活動等。1943年“三八”節,馮沅君在三臺婦女大會上,作了題為《婦女與文學》的長篇演說,生動地介紹了愛國女詩人許穆夫人、蔡文姬、李清照等人的不朽事蹟,激發了與會的千餘女青年的愛國熱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終於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馮沅君夫婦同千百萬同胞一樣,沉浸在無比喜悅和激動之中。不久,他們夫婦就隨東北大學覆校抵達瀋陽,1947年夏又應聘轉到青島山東大學任教。馮沅君一直嚮往風光如畫的海濱,此時,她的精神生活平衡了,物質生活也得到了保證,她的一顆需要慰藉的心,感到了舒適與溫暖。就在忙於教書、理家的間隙之中,她繼續進行古劇的研究,從而一鼓作氣寫出了《元雜劇中的〈東牆記〉》(1947年)、《記侯正卿》(1948年)、《唐傳奇作者身份的估價》(1948年)等文。在此期間,馮沅君還寫了一部專著《古劇說匯》(商務印書館1947年初版,1956年作家出版社修訂重版)。陸侃如則完成了《中古文學系年》的浩繁工程,這部80餘萬字的學術鉅著,直到1985年才得見天日。馮沅君的嘔心瀝血之作《古劇說匯》是繼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之後,中國戲曲史上又一輝煌鉅著,她的研究成果,解決了宋元戲曲的形成、創作和演出中的許多具體問題,對研究中國戲曲史有著重大的參考價值。
1974年6月17日,馮沅君因患直腸癌,被病魔奪去寶貴生命的,她從此帶走了74年的痛苦與歡樂,奮鬥與追求,告別了這個錯綜複雜的社會。
馮沅君逝世後,陸侃如曾寫過一篇深情懷念的悼文《憶沅君》,在這篇悼文中,他深情地回憶著他們相識、相愛與結合,以及馮沅君死前的悲慘情景。愛情猶如人生,是一本永遠寫不盡也讀不完的書,陸侃如的這篇悼文,充滿著他對愛情,亦是對人生的體味和啟示。為了安慰馮沅君的在天之靈,臥病在床的陸侃如打算整理出版馮沅君生前的著作。他們夫婦從30年代合著《中國詩史》起,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並肩戰鬥了大半個世紀,共同經歷了顛沛流離的歲月,也共享過一部部學術著作完成後的喜悅。但是,誰也沒有想到,僅僅過了4年,陸侃如也與世長辭了。
馮沅君和陸侃如生前立下遺囑,把他們數十年的全部積蓄6萬餘元人民幣及兩萬冊珍貴的藏書,全部捐贈給山東大學,作為優秀古典文學研究成果的獎勵基金。20世紀70年代的6萬元人民幣,是一個巨大的數字。這筆存款,是他們夫婦多年來積累的稿費和工資。
這對學術伉儷,生前是值得人們尊敬的學者和導師,死後則長眠在自己熱愛的祖國土地上。他們是幸福的。
來源:各界雜誌2021年第10期
作者:高夙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