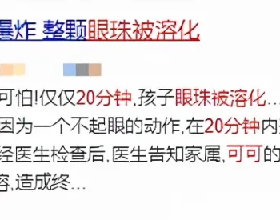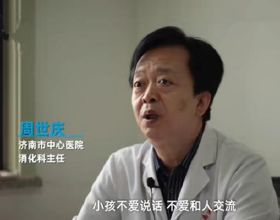“每個人到這世上來,同樣是歷劫,也是走一趟,也是經歷紅樓一夢。”
白先勇如是說。
多年後的白先勇在文壇已經是里程碑一般的人物,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沉醉於《紅樓夢》,鍾情於崑曲。這些哀怨纏綿陪伴他度過漫長的孤獨歲月,也讓他在文學中尋覓到悲憫與恕道的出口。
但更讓人津津樂道的,還是白先勇的顯赫家世,和他在特殊年代“逆流而上”的感情。
作為桂系軍閥白崇禧之子,白先勇無疑是戰爭年代的幸運兒。他的眼睛看過硝煙戰火,卻僥倖身在高處,鮮染塵埃。
他與同性愛人王國祥之間從年少相戀到攜手半生,直至天人相隔。時至今日,也是勇士行徑,相愛典範。
天命昭昭,半生浮沉。此去經年,白先勇的餘生即便孑然一身,也依舊熠熠生輝。
一、成長的反面意義是自我一部分的死亡:少時轉折
1937年7月11日,盧溝橋事變後的第四天,白先勇出生在風景如畫的桂林。作為國民黨高階軍官白崇禧的第八子,他卻沒來得及得到父親一個擁抱,白崇禧便被調任南京。
戰亂年代,人人都身不由已。白先勇僥倖生在軍官家庭,家境稍好,免受亂世之困。
自此白先勇就與母親馬佩璋生活在一起。父親在前線戎馬硝煙,母親在後方,操持家務,打理著一家老小的生活。
七歲以前的白先勇作為無憂無慮的軍二代,生在桂林,長在桂林,踩著桂林的晨曦夜幕長大。
桂林的一草一木,人文情懷,深深烙印在白先勇幼小的心上。直到白先勇開始在文學界初露鋒芒,他筆下流瀉出的鄉土人情,風光樣貌,濃墨重彩的字字句句,無一不是對桂林入木三分的熱愛與懷念。
桂林安放著白先勇回不去的無憂童年,像是一個分水嶺的另一邊,成了七歲後的白先勇可望不可即的安適時光。
即便是人間天堂,也無法在全國混戰的時代背景下獨善其身。一如白先勇,出身高貴,依舊在戰火燃燒之際,泯然眾人。
1944年,湘桂大撤退。敵機的呼嘯打破桂林靜謐的風光。白崇禧在炮火連天中,帶著家人一路撤退到重慶。自此,白先勇離開桂林,結束了他安閒隨意的時光。
就在他跟隨父母一路顛簸的途中,白先勇感染上肺癆。在無法立即治癒的情況下,他被隔離在外。
此時的白先勇不過是年幼稚子,昨日的自由歡樂猶在,今日僅剩自己和一間老舊的房間。在這樣的落差中,他獨自走過恐懼,孤獨,無助,最終在一本本書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出口。
《紅樓夢》和《西廂記》就是在此時進入他的世界,點亮了他澄澈卻黯然的眼睛。他深深嗟嘆於書中的情感,也在書中人的命運裡,看透世間人都無法避開的殘酷命運。
書捧在他手裡,而窗開在他的眼前。
讀書之餘,獨屬他的一隅也有一扇開往江對岸的窗。他被隔離,卻衣食無憂,可一江之隔的地方,日日在上演戰火中的流離失所,飢寒交迫。
文字以外的世間之苦,如此鮮明地扎進他的心。對文字敏感的白先勇自然對情感更為共情,生與死,貧與富,光鮮與落魄,逐漸讓他生出超越年齡的悲憫之心。
後來他在書裡寫道:成熟的人生必須能從多方面去了解人生,而對眾生產生一種悲憫與恕道。
被隔離四年裡,白先勇孤獨痛苦過,卻也無形中塑造出自己的樂觀心境。即便滿目瘡痍,他依舊有一顆面向朝陽的心。
在與自己獨處的時光裡,他一點點從童年的懵懂中剝離開來。但他清醒地明白,這是成長必須的經歷的蛻變。
成長是痛苦的,因為成長的反面意義便是自我一部分的死亡。
有死亡才有新生。
二、文學是有用的,它是一種情感的教育:親情與事業
戰爭是掌權者的慾望。戰爭沒有勝利,因為它一開始,代價就是和平。
白先勇是這場漫長戰爭的見證者。
他沒有浴血沙場,卻一次次被眼前的滿目瘡痍刺痛。文人的一顆七竅玲瓏心,使他備感痛苦。他憎惡戰爭,對祖國愛得深切。
無關政治立場,他與他的父親白崇禧如出一轍。然而時代的洪流下,他們被動盪時局,推動著背井離鄉。
1948年,白崇禧舉家搬遷至香港。白先勇在此接受西式教育,這座繁華的城市短暫地棲息過白先勇渴望安定的心。
好景不長,1952年,隨著時代翻天覆地的變動,白先勇跟著父親穿越海灣,定居臺灣。從抗日戰爭到內戰,白崇禧一直在前線,白先勇也一直在移居的路上。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白先勇感受得分明。無根浮萍一般漂泊半生,跨越海峽離開故土後,這才真正的安定下來。
定居臺灣後,戰火裡奔波一生的白崇禧也得了空閒,作為一個長年缺席孩子成長的父親,此時終有空閒拾起父親的責任,和妻子一起教養兒女。
但此時12歲的白先勇不再是承歡膝下的稚子,少年的獨處時光讓他有著不符年紀的沉默寡言。他沒有討父親歡心的甜言蜜語,能帶給父親的,僅僅是一次又一次的好成績。
白崇禧自幼貧困,深知知識的重要,因此對教育十分上心。白先勇的優秀,讓他內心十分自豪,然鮮少宣之於口。父子間的默契,可見一斑。
定居臺灣後的白先勇終於擁有心無旁騖的求學時光。他熱愛文學,但遠離故土的他,並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他的目光關注著大洋彼岸,當祖國籌劃修建三峽大壩的訊息傳到他耳中,他幾乎立即就做出決定,報考水利工程系,將來建設祖國。
白先勇順利被保送,可一年後,他發現自己終究對文學懷抱著更大的期待。於是毅然退學再考,最終考入臺灣大學外語系。這裡成為白先勇初露鋒芒的地方。
才華橫溢的人無法被埋沒在人群中。白先勇在唸大學以後,便一發不可收拾的進行文學創作,到了大三,在臺灣文學界,他已經是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
也是這一年,意氣風發的白先勇與同學合作創辦《現代文學》雜誌。
真正將白先勇推到臺前的,是1960年的一篇文章《月夢》。這篇文章將向來隱匿在暗處的同性之愛擺上檯面,一時間引發巨大的輿論。
即便在今天,這個話題依舊是遊走在社會邊緣。況且是保守的上世紀。文壇的談論和質疑同在,反感和不屑更是甚囂塵上。
白先勇就這樣,頂著巨大的壓力,將對這種感情的認同和悲憫,坦坦蕩蕩地昭示於眾。少年心性,盡是逆流而上的淋漓盡致。
白先勇無疑是那個時代的幸運兒。他的家庭對他的包容和沉默的支援,一直都在。
當白先勇以一個勇士的姿勢站在陽光下的時候,他的家人,對此保持著心照不宣的沉默。
多年後,白先勇寫出關於同性戀的長篇小說《孽子》時提到父親。他說:“父親大抵是知道我的性向的,但他對我很尊重。”
在臺灣這片土地上,白先勇盡情地揮斥著自己蓬勃的熱愛與才華。而背後的家人,給予他潤物細無聲的支援,使得他沒有在大環境裡變得怯懦而畏懼。他懷揣著悲天憫人的心,活得積極樂觀,自信灑脫。
他以先驅者的模樣照亮著同類的路,而他的家庭,一直為他亮著那盞不怕迷失的燈。
隨著母親離世,出國留學。三年後父親離世,白先勇回頭看,自己的港灣已經是空空如也。
還好,身邊還有一個人,將於自己一同分擔風雨,共享虹霓。
三、初戀像出天花,一次就是一生:愛情
如果說移居臺灣是給予多年輾轉的白先勇一個安定的棲息地,那他在臺灣遇到的這個人,則讓他遊離於世的心從此脫離孤寂,有了為之嚮往為之無畏的方向。
白先勇的17歲,和所有少年一樣,青春洋溢,暢遊知識的海洋。上天垂簾,他與他的愛情,不期而遇。
與王國祥的相遇充滿命中註定的意味,補習班的樓道上不經意地相撞,撞出兩個少年人洶湧的愛情。一見鍾情猝不及防地發生在他們身上。
雖然王國祥和自己擁有同樣的性別,他們也沒有退縮。這個時間這個地點,剛好是你,那就很好。
兩人順理成章在一起。少年人的愛情向來直白又純粹,但似乎二人都沒有畏懼過可能艱難險阻的未來。白先勇說:“不過初戀那種玩意兒就像出天花一樣,出過一次,一輩子再也不會發了。”
他們互為初戀,也互相守護,直至半生。
勢均力敵的愛情令人豔羨。白先勇想就讀水利工程系,王國祥便報名考入同一院校的電機系。一年後白先勇想轉學讀文學,王國祥隨之努力,成功轉校,成為臺灣大學物理系唯一招收的轉學生。
雙向奔赴,尤為可貴。愛情無關乎性別,他們的相愛相守,和普通人一樣。而比普通人更勇敢。
兩人在生活上相濡以沫,學業上齊頭並進。神仙眷侶,無非如此。然天不遂人願,命運的劫難,晴天霹靂一般落到他們頭上。
大三的時候,王國祥患上“再生不良性貧血”,一個復原率低達5%的疾病。白先勇開始與死神賽跑,一邊兼顧愛人和學業,一邊遍尋名醫。
終於讓他們找到一種特效藥,這才控制住病情。劫後餘生的兩人相擁而泣,似乎從命運的手裡爭取出了相守的時光。
病情隱沒在生活以外。兩人順利畢業,一同定居美國。他們延續著國內時候的生活方式,買下一處草木茂盛的房子,打理花草,品茗讀報,坐看雲起,一轉眼就是半生。
愛情會趨於平淡,但相知相伴的知已情,越發深刻。王國祥專研物理,白先勇便打磨心性,以他對同性戀群體的理解和期望,寫出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本長篇小說《孽子》。文中的主角,因為特殊的性取向,被人不齒,放逐。
白先勇寫的,不僅僅是書,更是社會現實。
他擁有著家人的理解,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同樣勇敢的愛人。可這個群體,像他這樣幸運的人,少之又少。
白先勇的悲憫,一直都在。他對世界的善意與溫度,都在他筆下的字字句句裡。
可他和他的愛人,卻沒能得到上天的憐憫。
55歲那一年,王國祥的血液病再次復發。他不再是身體機能優異的少年,年過半百,他只能看著自己的身體猶如入秋的枯葉,一日日的衰弱。
白先勇沒有放棄,他踏上尋醫問藥的路。只要有一分希望,他也願意為愛人去闖一次。
然而一次次的失望,一次次的反覆折磨,白先勇漸漸接受了愛人無力迴天的事實。
最後的日子,他們都很平靜。這一晃而過的半生,他們攜手相伴。即便不能白頭到老,卻也不枉此生。
1992年8月7日,王國祥安詳離開。直到最後一刻,他們都沒有放開彼此的手。
許天長地久可以做如是解:你一生中只要有那麼一刻,你全心投入去愛過一個人,那一刻也就是永恆。你一生中有那麼一段路,有一個人與你互相扶持,共御風雨,那麼,那一段也就勝過終生了。
王國祥離去後,白先勇異常平靜。與愛人這風雨與共的半生,於他而言,足夠回味。但思念來的猝不及防,在辦理完王國祥的後事,白先勇回到闊別已久的家,才發現,到處都是愛人的痕跡。
世間之苦,愛別離,恨長久,求不得,放不下。他一人獨佔其三。後知後覺的懷念最為難熬。曾經鬱鬱蔥蔥的草木一片蕭索,夏末時分,寒意由心而生。
白先勇寫下《樹猶如此》,突露些許心聲,愛人離去,是“女媧煉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
四、揹負著命運的十字架,踽踽獨行下去:餘生
愛情是歡愉夾雜著苦楚,是生命的一場盛宴,更是火焰熄滅後燎原的火花。
愛人離去,生命與熱愛還在。
白先勇嚐遍命運給予的悲歡得失,繼續迎頭直上。少時悲憫的眼神猶在,他看過去的,不僅僅是芸芸眾生,更是他自己身在其中的黃粱一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