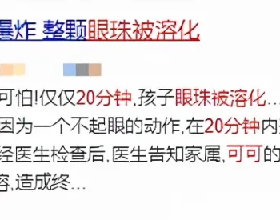記得兒時姥姥曾經讓我猜過一個謎語“石頭山木頭域,走一天出不去”,這謎底便是推碾子。姥姥多次告訴我,她的老祖宗是如何舂米,她說:“你們這些娃娃真幸福,一睜眼就有碾子了。老古時,米都是用碓臼舂的,活活乏死人呀。”
長期住在大城市的人,特別是現在的孩子們,很少有人知道碾子了,不才在此權作介紹:石碾分上下兩部分。上面的叫碾砣、下面的叫碾盤,碾盤架在石頭或磚頭壘就的臺子上。碾砣和碾盤上分別由石匠鑿刻著很有規則的紋理,其目的是增加碾制糧食時的摩擦力,透過碾砣在碾盤上的滾動達到碾軋加工糧食的目的。
碾砣固定在碾框裡。碾框是用硬雜木打成的架子,四邊形。碾砣兩頭的中央有兩個向裡凹的小圓坑,裡面固定著一個小鐵碗兒,叫碾臍。碾框的對應位置固定著兩個圓頭鐵棒,與碾臍相對,凹凸相合,能自由轉動。碾框的一邊有孔,碾柱插在孔中,碾柱是栽在碾盤正中央的木質或金屬圓柱。
這一切組合就緒,最後還要安上碾杆。碾杆是兩根一米左右的木槓,分別插在碾框兩端,呈對角線分佈。當逆時針推動碾杆,碾砣轉動,石碾就開始工作了。
穀子、糜子、黍子等的帶殼的糧食,就是在碾砣和碾盤的轉動壓軋中,去除外外殼,變成小米、糜米、黃米的。這個過程就叫碾米。值得述說的是磑面都用石磨,而唯一壓糕面用碾子。其奧妙一般人說不清。
製作碾子,大多用花崗岩。這種石料質地堅硬、細密、耐磨。即便如此,碾子用的時間長了,碾盤碾砣上的溝槽也會磨平。添在碾盤上的糧食雖經碾壓卻仍完好無損,推碾人也明顯感覺比原先輕快多了。這種情況就是告訴主人該請人鍛碾子了。鍛匠經常在各村轉悠,哪村有多少碾子、多少磨,什麼時間該鍛,他心裡有數。鍛碾時,鍛匠的一招一式都特別認真,鍛鑿的叮噹聲不斷,孩子們圍在四周探頭探腦、嘻嘻哈哈。靠得太近時鍛匠會大喝一聲,孩子們立即散開,不一會兒又會圍了上來。碾盤碾砣鍛好後,壓面的人家一家接一家,又恢復了往日忙碌的情景。
得勝堡正北的堡牆下,早年有座官衙,從我記事起官衙就塌毀了。在官衙遺址的東北仡嶗裡,有一座碾房。碾房不大,四面是土牆,房頂覆瓦。每到秋天新谷收穫後,這裡的碾子就閒不住了。一盤石碾要供數十戶人家使用,忙碌的程度可想而知。每逢此時,有的人夜裡一兩點就起來佔碾子。佔碾子的形式各有不同,有的放把笤帚、有的放個笸籮、有的放只簸箕。時間長了,人們對每家的標記都爛熟於心,一般不會出錯。一進臘月,搶碾子的事經常發生。吵起架來你推我搡、劍拔弩張,急高蹦低地互相指著鼻子喊爹罵娘,就像公雞鬥架一般。
其實,得勝堡西堡牆下也有一盤碾子,但建成不到一星期,便出了怪事。有一村民半夜經過碾子時,竟發現那碾子自己在轉動。他起初以為,一定有人在後面彎著腰推,可過去一看才發現根本沒人,碾子就是自己在轉。這村民當時就嚇掉了魂,連滾帶爬地跑回家中,據說還連發三天高燒。這事過後,晚上再也沒人敢去用那盤碾子了,周邊的住戶哪怕第二天沒米吃也緊鎖大門,蜷縮在家中。
哪裡都有膽大不信邪的人。得勝堡有個曾參加過抗美援朝,死人堆爬出來的人,對這些鬼怪一說,向來是嗤之以鼻。一天晚上,這個老兵揹著一袋子黃米去了。他心想,既然你自己能轉,那乾脆幫我壓成糕面好了。
去了以後,老兵便將黃米鋪到了碾子上。自己則坐到了十幾米外的一塊石頭上,等著怪事發生。那天晚上,月朗星稀,一片寂靜,他剛要丟盹,突然耳邊傳來沙沙的摩擦聲。老兵睜開朦朧的雙眼,見那碾子竟然真的轉起來了。他慌忙上前檢視,這不看不要緊,一看著實嚇得不輕,那碾盤子上竟然在冒血。緊接著,他感覺有什麼東西在抓自己的腿,仔細一看竟然是一雙腐爛的手,從磨盤底下伸出。老兵頓時頭皮發麻,踢開那雙手,拔腿就跑。當時的恐怖,可見一斑。
有老人說,那鬼是得勝堡初建時戰死計程車兵,一直沒有轉世的冤魂。
得勝堡東牆下還有一盤碾子,也沒人用。因為那些年有人做鞭炮,用來碾了火藥。
做火藥一般需要就地取材熬製硝。雁北路旁、河沿潮起的硝土很多,人們收集起來,裝入淋池,淋為硝水,再盛入鐵鍋內猛火熬煮,待水分蒸發盡淨後,就會留下一層白色的結晶體,這便是硝。至於木炭,也是就地取材,多用木頭、葵花稈燒成。只有硫磺得花錢到供銷社購買。雁北人稱加工火藥為“碾火藥”,即將硫、硝、木炭混在一起,攤在碾盤上用石碾反覆滾壓,為防止硫、硝在碾壓時磨擦引燃,需加適量水,以保藥材溼潤,什麼時候藥材成細粉末或片狀物了,這火藥才算製造成功了。
得勝堡有一家人碾火藥,突然爆炸,老兩口全炸死了。從那以後,得勝堡做鞭炮的人漸漸就少了。那盤碾子也就廢棄了。
推碾子,既是受苦的活兒,也有較高的技術含量。邊推碾子、邊掃碾盤、邊添新糧,隨時觀察糧食的變化。掌控得不好,不是碾不淨穀殼,就是碾碎了米仁。用簸箕簸穀糠,也需要用力均勻、簸動適當。其技術要領,不是三下兩下就能掌握的。
推碾子時,兩個人一前一後地推著碾槓。另一人手拿著笤帚,掃那些擠軋到碾臺邊上的糧食。人一圈又一圈地推、碾砣一圈一圈地軋。糧食放厚了碾的粗,放薄了就碾得細。碾碎了的糧食還需要一遍一遍地過篩,不時地用手指觸控檢查米粒碾壓的程度,直到完全脫殼為止。
往事不堪回首,1960年大饑荒時,得勝堡的人們餓的嗆不住,還吃過各種糧食作物的秸稈。玉米秸、高粱秸、綠豆秸、黃豆秸……人們先把這些秸稈切碎,然後,放在碾子上軋。碾完羅成細面後,放在水裡沉澱,然後倒掉浮水,把沉澱物摻在粗糧裡面,或熬粥、或貼餅、或蒸窩頭。再後來就顧不上沉澱了,直接把粉屑摻到米麵裡吃了。
雁北多禁忌,無論大人孩子,都不能在碾房裡大小便;也不允許坐在碾盤上休息;女人經期也不允許進入碾房。誰違反了這些規矩,就要受到責罰。一位嫁到得勝堡不久的寡婦,有一次洗完紅主腰子晾在了碾杆上,一下子犯了眾怒,鄉親們非要讓她離開村子不可。最後,經過眾人調解,她用鹼水把碾杆洗了兩遍,在眾目睽睽之下,磕頭求罪了事。
村民們認為石碾是有生命、有靈性的。誰家生了娃娃,都不忘在碾盤上掛個紅布條。傳說,石碾是青龍。春節時,人們不忘用一條紅紙,寫上“青龍大吉”四個字,貼在碾管芯上。記得得勝堡的一位私塾先生,每年都給碾房和磨房寫對聯,一副是“推移皆有準,圓轉恰如環”;另一副是“乾坤有力資旋轉,牛馬無知憫苦辛。”橫批“青龍永駐。”
推碾子既枯燥又勞累,既笨重又乏味。人們在碾道里轉了一圈又一圈,臉上的汗擦了一遍又一遍。即便是驢也要不時停下來歇歇,站在那裡喘著粗氣。不一會兒,人們用木棍兒敲一下它的屁股,碾道里又響起驢那無可奈何“吧嗒、吧嗒”的腳步聲。凡是年長些的人,只要提起推碾子,都會談虎色變。
少年時,我曾經幫大人推過碾子,因而深知推碾子碨磨,是所有家務事中最苦重的營生。尤其冬天的早晨,嘴裡呵出的氣變成了白霧。手摸住冰涼的碾杆,立刻就想著縮回到袖筒裡。回味著剛剛離開的熱炕頭熱被窩,推著推著就打起了瞌睡。我曾在黑夜裡推過碾子,一盞昏黃的煤油燈照著一張張滿是灰塵的臉。一圈兩圈、一簸箕兩簸箕,我們就這樣推著、數著。最後下來滿頭滿身粉塵,骨架子就像散了一樣。回家不洗臉不脫衣服,倒頭便睡。
現在看來,讓那些天生好動的娃娃們,重負之下圍著碾道繞圈兒,簡直就是一種折磨。但那時沒辦法,要想吃米,就只有幫大人推碾子,不推不行。
至今忘不了姥姥纏著一雙小腳,顫巍巍地圍著碾盤用笤帚掃米的情景。她老人家沒活到電碾出現的一天,否則不知會如何感嘆呢!
今天再讓孩子們猜那“石頭山木頭域”的謎語,肯定打死也猜不到。甚至會覺得“走一天,出不去”像莊稼人湊近電燈點菸一樣可笑。猜不到謎底也好、可笑也好,那畢竟是一段歷史,是一段漫長不容忘卻的歷史。(作者 韓麗明)
有詩云:
毛糧成米麵,碾砣擦碾盤。
富家把驢套,窮人抱碾杆。
不顧頭髮暈,哪管身流汗。
可憐農家人,從沒好茶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