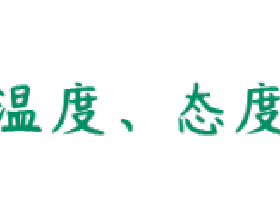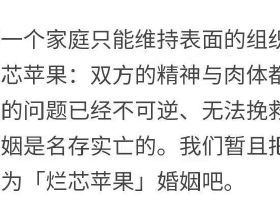排隊,掛號,檢查,住院。
她蹣跚著挪到產房,值班的護上問:“人呢?”
人?她有些懵,我不在這兒嗎,還問哪個?田美玲從蠟黃的臉上擠出一絲笑,對比自已年輕的女護士輕聲說:“我就是。”
“我問的是你愛人!”護士露著她那職業般的笑容。
田美玲感到身子似冷似熱,有一滴汗從腮邊流下來,打在胸前的衣衫上,溼潤了一片。雖是七月,她卻打了一個冷顫。
護士看著面前個兒不高,卻還漂亮的孕婦,又問:“你愛人怎麼不來?”
“他不知道!”美玲硬硬地說了一句。
“不知道?”產房裡的護士和醫生都笑,“羊水破了,骨縫也開了,你丈夫卻不知道?”他們的神情已完全是面對一個 未婚先孕的大姑娘。
她有些受不住了,嚷了一句:“他真的不知道!”
年紀大些的主治醫生說:“你愛人不來誰簽字?出了問題誰負責啊?”她答不出來,急得想哭。
只好躺在產床上,聽天由命。這時她發現外面的太陽在移動,肚裡的小東西也在動。
鄰床孕婦的呻吟聲越來越大,伏在床沿上打盹的丈夫抬起頭,急急地問“要生?”
“狗屁,我疼!”孕婦惡聲惡氣地說。
丈夫說:“那你抓著我的胳膊。”
“哎喲喂”孕婦扯長聲音叫了一聲,又罵,“都是你發壞,讓我遭這麼大的罪!”
丈夫低聲哀求:“是我不好,你掐我兩下吧!”
田美玲再不敢看,也不敢聽,但她想自己的丈夫要在身邊,她倒真想咬他一口,死死地咬,咬到孩子生下再鬆口。一份痛苦由兩人承擔,她就會有兩個人的力量。
又聽到鄰床上的產婦在哼。邊哼邊捶打自己的丈夫。
有兩串淚從田美玲的眼中湧出,朦朧中,她感到自己的丈夫也坐在床邊,她在家裡給丈夫留了條子,告訴他她要到醫院生孩子了。走廊裡響起一串腳步聲 ,田美玲心裡一緊:是他?但腳步聲消失在隔壁的產房裡。她的心裡又一緊:他還沒回家?關楓,關楓你在哪兒?
關楓在一個遙遠的地方當連長。丈夫是她個人的,連長卻是全連百多號人的。她不能怪他又不得不怪他。是啊,生孩子沒人照顧,不怪自己的丈夫又能怪誰呢?儘管她也知道他確實沒辦法。他太忙了,顧了連隊就顧不了她。她想起戀愛的時候,鄰居朋友親戚都勸過她,說找一個當兵的做丈夫,中看不中用,說不定什麼時候上了前線,傷了殘了得侍候他一輩子;不上前線平時也是守活寡。
可是她沒有考慮那麼多。那時,她有那麼多的幻想,覺得跟了一個當兵的會很幸福很自豪也會很驕傲。一個星期見一次面,每次見面都韻味無窮,都會留下很多眷戀很多企盼。
婚後,他和她在一間狹窄的小屋裡建起了屬於自己的窩。部隊駐地離市區不遠,只有四十里地。一個月不算長,可是有二十八九天她是在期待中度過的。那屋子因隻身孤影,就顯得空曠、寬大;那日子因寂寞、期待,就顯得孤寂、漫長。
她剛懷孕的時候,她喜他也喜。她喜她不再寂寞不再孤獨,時時刻刻都有了他的影子陪伴著她。他喜他要做爸爸了,沒必要再為是否有接班人的問題多費心思。
那天,他和她依偎在顯得窄小偏擠的屋子裡。她問他,“你喜歡男孩還是女孩?”“我都喜歡。”他說著想湊上去。
她用手擋住:“你先答應我一件事。”“什麼事?”
“到時,你一定要回來,我怕。”
“那還用說!”
鄰床的孕婦又在叫,那聲音軟軟的,摻著一半水分,讓人覺得不是在叫,是在唱。
田美玲也想哼。“哎喲....”只一聲,她自已聽了立即覺得刺耳,她怕被鄰床的孕婦聽到,第二聲沒有哼出,就嚥了回去。
靜靜在床上臥著想著反覺得不輕鬆,就開始下床在屋裡走,不停地走,醫生說孕婦多運動,生得快,她信,就在屋裡從這邊走到那邊。開始是胡亂地走,慢慢的,她就記得從門到對面窗戶是二十步,從窗戶到門也是二十步。有一趟走了十九步,她也記住了。
第二天,她躺在產床上,挺直身子,用盡自己全身的力氣,將在腹中孕育了九個月的小生命送到了人間。
她好累。但她還想哼一聲,像別的產婦那樣,帶著幾分幸福、嬌柔、憂怨,向自己的丈夫渲瀉一下無限的愛和甜蜜的恨。可是,她將這輕微的一聲嚥了回去。此時,田美玲既有做母親的自豪又有做母親的沉重。以後的日子還長著呢,養育孩子的重擔只有她一個人挑,那弱小且經常犯病的身子,挑著這副擔子能走多遠呢?
正是早晨,太陽像血團一樣慢慢地升起。一束光焰從窗戶射進產房。她睜開疲倦的雙眼,看著護士手中紅彤彤肉團似的小東西;她聽到小東西在啼哭,像唱歌一般。
給孩子餵奶時,田美玲又看見鄰床的那對夫婦在逗引著他們的孩子,她又惱又恨又怨。
有一滴淚掉下,打在懷中小東西的臉上。她用唇去吮幹。
她在心裡說:“關楓啊,你想過該怎樣當爸爸了嗎?”
此文獻給所有的軍人家庭
嚴禁抄襲,圖片來源於網路,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