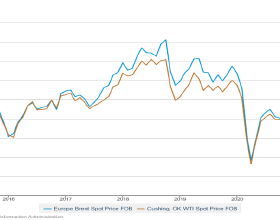本文系19年課程作業。
[摘要]因2018年馬克龍政府增加燃油稅而爆發的法國“黃馬甲”運動對整個法國乃至歐洲的政治局勢都產生了重大沖擊。本文作者希望透過結合近年來國內對“黃馬甲”運動的相關研究、資料與新聞報道,從現實和歷史兩個維度出發探尋其成因並進行反思。
[關鍵詞]黃馬甲 社會階層 政治文化 法國大革命
前言與背景
“黃馬甲”運動是一場席捲法國,震驚全歐洲乃至世界的大規模騷亂與示威運動。其單次遊行最高參與人數曾達到28萬人之多,被一些學者稱為自1968年“五月風暴”以來法國最大的社會動盪。這場運動自2018年11月開始,時至今日也尚未宣告終結。“黃馬甲”運動不僅在法國全境展開,還蔓延到了比利時、荷蘭、義大利等國。據部分訊息來源稱,“黃馬甲”運動最初只是一場小部分民眾對馬克龍政府關於燃油稅的改革措施表達不滿與訴求的集會遊行和示威活動。但極左翼和右翼分子利用集會時機實施襲擊警察等違法行為,擾亂了原有的遊行秩序。此外,部分社會底層人士如城市郊區的遊民等混入隊伍,並伺機打砸商店、焚燒車輛、搶劫財物,進一步加劇了這場運動的騷亂態勢。[1][1]
法國總統馬克龍自2017年上臺以來,採取了積極主動的外交內政方針。在國際方面,面對英國脫歐等歐洲一體化程序逆流的挑戰與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浪潮,其堅定維護歐盟一體化成果,並表示堅持多邊主義與自由貿易立場,其決心在他於巴黎和平論壇上抨擊國家至上主義的做法中可見一斑。在國內方面,其積極進行勞工法改革、調整社會福利政策,並積極落實《巴黎氣候協定》相關內容,提出了提高燃油稅的計劃,以此稅收收入為可再生能源投資提供資金。然而,馬克龍本人及其內閣成員低估了過往的改革措施對法國中下層民眾造成的持續衝擊,本次燃油稅改革最終成為了“黃馬甲”運動的導火索[2][2]。
2018年12月10日晚,迫於形勢壓力的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電視講話,對“黃馬甲”運動作出了一些讓步,包括上調法國最低工資標準(SMIC)、免除加班收入的相關稅收、停止增加對月收入較低的退休人員徵收社會普攤稅的稅率三項措施。在馬克龍此前的養老金制度改革中,他曾計劃提高該稅種的稅率。[3][3]除了上述幾項措施,馬克龍還呼籲企業主向員工發放年終獎勵,希圖透過這些措施平息示威者們對於日常生活水平和購買力下降的憤怒。12月17日,法國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在接受法國《回聲報》採訪時,也公開承認法國政府在處理過去五週席捲全國的大規模“黃馬甲”抗議活動時犯了錯誤。
2019年1月13日,馬克龍辦公室發表公開信,呼籲民眾參與討論稅收制度等事宜,希望藉助全國討論形式在各地市政廳和網際網路上徵集民眾意見。討論內容主要涉及稅務制度、綠色能源、制度改革和公民身份四大主題。在筆者看來,這已經可以說是政府對示威者的極大妥協。然而,這類舉措仍然未能使“黃馬甲”運動平息。不過,在2019年5月4日,“黃馬甲”運動爆發第25周進行的示威中,全法國共有約18900人參與遊行,而巴黎僅有1460人上街,創下了歷史參與人數的新低。由此看來,“黃馬甲”運動似乎已經透支了民眾的耐心與興趣。本文試圖透過社會階層分化和政治文化因素這兩個視角,對“黃馬甲”運動中部分耐人尋味的現象進行分析。
社會中下層群體的“塌陷”與焦慮
“黃馬甲”運動是法國社會各利益團體負面情緒的一個宣洩口。儘管大部分法國民眾對示威遊行中出現的暴力行為表示反對,但其對示威運動本身的支援率卻一直在70%以上。[4][4]這一資料反映了法國民眾對政府削減福利、增加稅收政策方面的敏感態度。這一態度背後的深層原因是法國在凱恩斯主義持續影響下的高福利政策傳統與現今全球化程序導致的產業分工與國內產業外流現象之間的矛盾。
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盛行在競選中以高福利政策承諾交換選民的選票支援。同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發達國家的科技水平與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為高福利政策提供了有利保障。但近年來由於全球化程序的日益深化、國內資本、產業的轉移以及國內產業競爭力的下降等因素,法國對外貿易逆差有所上升,國內就業壓力逐漸增大,民眾收入問題逐漸顯現。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的分析,進入21世紀後,法國家庭的平均收入大約每年減少400多歐元。這對中間階層、中產階級的影響較為明顯,其在社會地位與生活水平上的錯位導致的焦慮感與挫敗感由此被放大。此外,許多收入不穩定、教育水平較低、家庭負擔較重的工人與農民受國內經濟形勢影響較大,生活水平並不穩定。這些因素都為“黃馬甲”運動的爆發積累了一定的社會基礎。
根據歐洲統計局的資料,法國的基尼係數是0.295,而發達國家平均為0.315。在另一個機構的統計中,法國10%最窮的人每年約有7300歐元收入;10%的富人每年約45223歐元;1%的富人每年約106200歐元,大致相當於國民年收入中位數標準的5倍。1%的富人擁有法國人總收入的7%,10%富有者擁有法國人總收入的28%。[5][5]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法國的貧富差距問題相對而言並不太突出。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國民眾為什麼仍然要選擇以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呢?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法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有關。
“以下克上”的政治文化傳統
“政治文化”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於1956年8月所提出的。阿爾蒙德認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程序所形成。”[6][6]由此可以得出,法蘭西民眾對政府政策的態度受到民族發展的歷史軌跡與現實環境的雙重規制。
埃德蒙·柏克認為,法國大革命的一個最壞的後果就是使人們賴以生存的傳統被粉碎,而那些野心家憑藉啟蒙運動中高度抽象的政治原則來宣告他們的理想,愚弄這些苦難的法國民眾,最終達到他們的政治野心。而失去傳承物件的人們,實際上是無法在所謂“聖人”的指點下走向理性的自由的。建立在舊有體制基礎上的觀念與秩序被破除,而革命領袖和理論導師們帶來的新觀念與新秩序卻為接下來的埋下了種子。 [7][7]
在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的薰陶下,在法國人民攻佔巴士底獄和處死路易十六的“以下克上”式的光榮先例下,透過激烈抗爭的方式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思想已經根植於法國民眾心中。然而,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崇高理想由於時代的侷限至今未能真正實現。作為法國大革命時期綱領性檔案的《人權宣言》中有言,“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但實際上這種權利的平等是一種理想化的表述,在實際狀況中人民在政治社會地位上的“平等”狀態由於經濟基礎上的不平等狀態而始終無法完全達成。在對“自由”、“平等”理念進行過度渲染的歷史背景下,示威者們在遊行中採取的暴力舉動、對政府的示好行為拒不妥協的態度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8][8]
英國法學家詹姆斯·斯蒂芬在他的著作《自由·平等·博愛》中就係統地批判了羅伯斯庇爾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三大信條。他認為,這三大信條是對當時民眾訴求的一種模糊不清的概括與表達。自由應當是一種有秩序的自由,平等應當是被置於法律下的平等,而博愛則是一種與自由社會不相容的價值。他反對穆勒“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一部分才必須對社會負責,……對於他自己,對於其身體和心靈,個人即是最高主權者”的簡單自由觀念,並得出了大部分個體會因此而陷入人性固有的缺陷之中的結論。他還認為,自由只是一種追求社會福祉的工具,本身並不具備內在價值。 [9][9]
此外,斯蒂芬還從經驗主義出發,認為人與人在實質上是不平等的,很多時候人們追求平等的情緒只是為了拉平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差距。他贊同法律上的平等,而非結果上的平等。“既然人在天賦上和能力上是不平等的,社會就把這些差異體現出來。如果沒有財富和社會地位的差異,人們將失去工作的動力。”[10][10]我們不能完全否認民眾擁有爭取個體平等的意志,但這種爭取平等的行為應該基於不因個人努力而改變的客觀現實。換句話說,只有上升通道被截斷的個體才具有為自己的發展機會而抗爭的權利,而任何不經過努力爭取自我價值提升,僅僅寄希望於透過遊行示威甚至更嚴重的暴力行為換取政府補助的行為個體只能被歸類為懶漢與流氓。
而在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歷史上,馬克龍並不是第一位因推行改革舉措而遭到民意重創的領導人。從第五共和國的創始者、領導法國人民在二戰中透過鬥爭贏得民族自尊的戴高樂總統,到由於大刀闊斧推行改革,最終因觸怒民意導致總統連任失敗的薩科齊,再到曾經贏得大批民心,最後卻在《世界報》2016年10月民調中僅得到區區4%支援率的奧朗德,他們的落敗都與民眾的政治意見密切相關。但民眾的激烈抗爭帶來的始終是政策的暫時性退讓和政府首腦的個體性落敗,而當新的“眾望所歸”的領導人上臺後,又極易因希望對法國面臨的局勢有所作為的態度而遭致新的反對浪潮。這樣的迴圈與其說是民眾意願的勝利,不如說是國家治理的悲劇。
結語
綜上所述,“黃馬甲”運動是一場在法國社會中下階層群體整體生活水平下滑,民眾處於不安與焦慮狀態的背景下,因根植於法蘭西民族內心深處的平等意識與革命訴求而形成的群眾運動。“黃馬甲”運動不是第五共和國曆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群眾運動,同樣也不會是最後一次。要想改變這一現狀,或許只有寄希望於法國因某種原因實現的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復甦,或是新的外來因素對法蘭西固有政治文化傳統的改造。前者何其艱難,而後者又是何其浩大的一項工程。與之相比,打著“傳承優良傳統”的旗號為自身行為辯護又是多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呢?在研究義大利公民生活的著作《使民主運轉起來》中有這樣一則小故事:一位來自公民意識欠發達地區的地區長官,在聽到前來調研的政治學者對該地區公民意識的分析結論時嘆息道:“這真令人絕望!你是在告訴我,無論我怎麼做都沒有成功的希望。因為改革的命運早已在幾個世紀前就已經被鎖定了。”[11][11]
- [1] 王文新.“黃背心”運動:馬克龍改革的可為與不可為[N].第一財經日報.2018-12-10 A11 ↑
- [2] 秦藝丹.民粹主義浪潮與法國“黃馬甲”運動[J].唯實.2019,(04)89-92 ↑
- [3] 人民日報海外網.馬克龍提高最低工資對“黃背心”讓步 堅持繼續改革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9513606056704586&wfr=spider&for=pc ↑
- [4] 張驥.法國“黃馬甲”運動及其對法國外交的影響[J].當代世界.2019,(01),28-32 ↑
- [5] 環球網.扒下“黃背心”,法國貧富差距究竟有多大?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9807803084806247&wfr=spider&for=pc ↑
- [6] Gabriel A. Almond,G.Bingham Powell Jr..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26 ↑
- [7] 趙益晨.從《反思法國大革命》試論柏克的政治思想[J].才智.2017,(29),198-199 ↑
- [8] 魏南枝.法國大革命的內在矛盾與“黃馬甲”運動[J].文化縱橫.2019,(02),80-89 ↑
- [9] 羅翔.狂熱的魔咒 理性的自負——《自由·平等·博愛》讀後及對刑法學研究方法的反思[J].政法論壇.2018,36(05),162-172 ↑
- [10] 劉軍寧.保守主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47 ↑
- [11] Robert D. Putnam.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義大利的公民傳統[M].王列、賴海榕譯,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