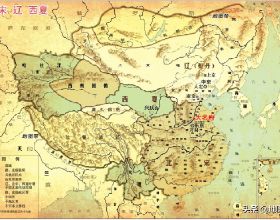我和二子
二子和我是同齡人,我倆算是光屁股長大的發小。輟學以後我倆整天無所事事,出來進去的滿世界窮晃晃,父母們都是普通工人,沒啥門路,對於安排子女就業真的是無能為力。
1994年的秋天,我倆每人從家裡拿了五十塊錢,借了我二舅的一輛三輪車,打算做水果生意。我們早上五點就到了石羊橋水果批發市場,打聽了各種水果的價錢後,發現100塊錢只能進兩件40斤裝的蘋果。
拉著這80斤蘋果繞著舊城,以三斤五元的定價開始售賣。由於沒經驗加之臉皮薄,根本不好意思吆喝,以至於一上午都沒賣出去20斤。好幾次二子遠遠的看見有熟人走過來,都是扔下我和三輪車躲得不知蹤跡。到了天擦黑的時候,才趁著暮色的籠罩,厚著臉皮吆喝起來……
之後連續的三天大雨,澆滅了我倆的創業激情,每人分了48.2元和15斤蘋果,還了三輪車,這一場買賣宣告結束。
1995年夏天,我租賃了一個遠房二姐夫的兩臺球案子,在 大雜院大門口當起了臺主。由於技術太臭,經常被獨自過來打檯球的客人退,所以收入很寡淡,每天也就十塊八塊的。於是便僱傭了二子當打手,二子水平不錯,幾乎是打一把贏一把。
隨著收入的逐步增加,我和二子開始“大吃大喝”。那時候家庭條件不好,肚子裡沒油水,又加之屬於長身體的最後衝刺階段,看見啥也饞的不行。我倆經常在半下午人少的時候,去小召前的熟肉鋪子買兩節灌腸,或是一塊兒毛蛋燻肉解饞。就這樣嘴吧越吃越饞,以至於每個月剩下的錢將夠付案子的租金。
過了八月十五,天氣逐步轉涼,不再適合擺野臺球啦。一夏天一分沒賺著,反而學會了抽菸喝酒。閒下來的我倆每天出來進去的,能感覺到鄰居們向我倆投來鄙夷的目光。
第二年的夏天,我和二子應聘,到一家叫“金火”的私人公司打工。那家公司專做保健品生意,員工們都要駐外。我只去大連幹了半個月就辭職了,就當是旅遊了一趟。回來以後經人介紹,去捲菸廠當了臨時工。二子卻很適應外地生活,一直在“金火”幹了下去。
二子的“刀尖嘴”
二子每三四個月回一次家,待幾天就走。他在家的日子,我下了班就和他聚在一起,聽他聊外地的各種見聞,他也詢問我院子裡發生的人和事兒。
有一次談論到院子裡面一個叫“老山東”的磨剪子老頭,他說:“我看老山東不行了,快死呀……”他走了不多久,那老頭真死了。半年後二子回來,我說:“你走了不久老山東就死了!”他說:“老山東的老闆子(老伴兒),也快!”那一年不到春節,老山東的老伴兒也去世了。
二子回來過年,家裡面支起了麻將攤子。一個叫朱金梅的鄰居老太太過來打麻將,打的過程中總是用手絹兒擦拭嘴裡留下的口水,散場後二子囑咐他媽說:“朱金梅不行了,以後不要叫過來打麻將啦,鼾水擺帶的,死的咱們家,那算屙的皮褥子上啦,擦洗不乾淨……”
二子走後不久,朱金梅在老梁家打麻將的時候,猝死在牌桌上。據說死的時候,手裡面還摳著一張能暗槓的發財。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院裡面打麻將的人們,摸到發財往出打的時候,嘴裡都說‘朱金梅’。我勒個去這也是牌友們對她的懷念吧……
有這三件事兒,二子媽就囑咐二子以後不要瞎說,她說:“你這種行為民間叫‘刀尖嘴’,說好的不應,說賴的可準呢。”二子自己也感覺到有點愧疚,多年來就一直也不敢瞎說啦。
十二閻王的由來
2002年的時候,大院後大門緊挨小鎖家的小院子裡,搬來一戶人家。據說是清水河縣的,兩口子四十多歲,帶著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兒。搬來不久就開始“興風作浪”,那女的和院子裡的家庭婦女們說自己是頂大仙的,能看吉凶禍福,能治疑難雜症。時間長了這些家庭婦女們,都聚在她家的小院子裡,聽她裝神弄鬼,等待施捨靈藥……
有一天下午,二子回家找他媽拿東西(那時候二子已經結婚搬離了大院),家裡沒人,全院找遍了也沒找見,後來有人說你媽估計是去了大仙家啦。二子問清緣由,推開大仙家院門,看見他媽夥同一群家庭婦女,圍坐在小院內,中間那個所謂的大仙,正自閉著眼睛,口中唸唸有詞:“閻王叫你三更死,只有我敢留人過五更,如若不聽真,打上兜率宮,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聽到此時二子怒不可遏,走上前去提住那大仙脖領子,乒乓就是兩個軍用逼兜(max耳光)。嘴裡罵道:“你個吃求的命將扎掙,跑得爺這兒裝神弄鬼來啦!還閻王叫三更死,你能留人到五更。爺要是個閻王,攔腰一刀就砍死你個泡啦……”說罷拉著他媽就走出了院子,留下大仙和一群家庭婦女們在風中凌亂……
此事過去不久,那夫妻二人,被小召前派出所民警教育了一次,以後再也不敢自稱大仙了。如此過了半年多,那個女人得病死了,死於病毒性帶狀皰疹的併發症。這種病,民間也稱“蛇纏腰”。人們都私下議論:“老徐家的二小子日惡(厲害)了,你看看說讓誰死誰就死,那可是個二閻王,惹不起……”得知這訊息的二子久久不能平復,他總認為冥冥中這位大仙說不得真的是死在了自己的嘴下……
二子現在過得挺好的,他結婚早,孩子也上高中啦。如今我倆還是經常見面的,屬於無話可說又無話不說的兄弟。
張老太太
張老太太是我奶奶那一輩的人,她曾是一名棄嬰,由舊社會歸化城(如今的呼和浩特)天主教的育嬰堂撫養,取名“瑪利亞”。成人後,嫁給走西口來歸化城的張姓人家,便也隨著丈夫姓了張。
張老太太身形矮小,目光陰騭,總是神神道道的。按說她理應是信奉天主教的,可是他家院牆上卻用紅色油漆寫著“泰山石敢當”幾個大字。每到下大雨的時候,總是能看見他站在屋門口舉著一把菜刀,對著天空不斷落下的雨滴劈來砍去,劈砍一陣,噹啷一聲將菜刀丟在院中,陰惻惻的笑一聲回屋……我奶奶說那是避雨呢,怕下的太大屋頂漏雨。
貴天和富天
貴天和富天是張老太太的兩個兒子。貴天長得很像華國鋒,在呼和浩特華建公司上班,是一名抹灰工。據說級別很高(8級工),工資相當於兩三個普通工人。貴天有好幾把大小不一“泥壓”(灰抹子),鋥光瓦亮的,用紅布包著放在大櫃裡面,輕易不用。我曾今見過貴天抹灰,先用大泥壓抹平,中號泥壓抹光,然後手裡捏著一撮水泥,用嘴吹響潮溼的牆壁,同時用小泥壓拋光。看著泥壓在他手裡揮舞,簡直就是一種享受。
富天是貴天的弟弟,別看他叫富天,但是樣貌卻苦哈哈的,遠不及他哥哥富態。最記憶猶新的是,他兒子出生就患有先天性疝氣,有一個蛋特別大。四五歲了還收不回去,穿著開襠褲。我那會兒十一二歲,經常把他叫過來摸一摸,青嘭嘭的挺好玩兒……
有一年秋天陰雨綿綿,張老太太的菜刀扔出去沒管用,雨就是不停,下了兩天兩夜。窗臺下的地基被雨水灌得有點下沉,貴天和富天二人來給整修。他們拆窗臺的時候,從磚縫裡面找見一個現大洋。這一下把兄弟二人的積極性調動了起來,他們判斷這所民國年間的老房子裡,必然藏有不少寶貝。於是二人用柱子撐住前房梁,幾乎把房子的前臉全拆了下來,毛也沒找見一片兒。那時候院子裡面有個叫劉大學的老人,當時有九十歲了,得知此事後過來阻止說:“窗臺有大洋,那是蓋房定主位放的,是個講究,就放的一個,哪有那麼多呢?”聽了這話二人才罷了手……
說不得又花錢請人重新修整了房子,弄了個得不償失。此事兒一時成了全院人茶餘飯後,談論的笑話兒。
九十年代末貴天被查出患有心臟病,需要做手術,後來死在了手術臺上。貴天這名字不好,歸天啦!富天很早就搬離了大院,也許是拿到了他哥的醫療賠款也不一定……
四戶人
大雜院的前院和後院,有一個連線處。這是一個長方形的小院子,四間正房的對面是四間涼房。這裡住著四戶人家,戶主們的年齡相仿,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他們都三十啷噹。在當時來說,這個小院子是整個大院裡面,是最具朝氣的一片小天地。
(1)小李子一家
小院子最西面的一戶人家,男人姓李,大家都叫他小李子。他是個紅臉膛,個子高高的,是內三建的一名技術人員。常騎著一輛紅色的鈴木125摩托車,由於平時老搞點兒外接營生,所以小日子過得很不錯。
他老婆姓陳,是某國營糧站的會計。他們有一個女兒小名叫毛毛,比我小兩歲。年輕的時候這兩口子也經常吵架,我記得有一次小李子喝多了,兩人吵得很厲害。小陳說:“你一天也不回家,回來就醉醺醺的,也不知道心疼老婆親親孩子……”接著就聽小李子說:“爺親你們了?爺噠抵倒頭親球呀……”
他家是四戶裡最早搬離大院,入住樓房的。後來聽說小李子走後門,把毛毛弄去北京當長跑運動員,呆了幾年由於成績上不去被刷了下來,錢也白花啦。現在在某中學當了體育老師,和一個同校的數學老師結了婚。前段時間聽父母說還見過他們,老兩口也都六十多歲了,退休後生活挺好的。
(2)小余一家
小李子隔壁就是小余一家,小余長得很富態,不愛多說話。是機床附件廠的工人,在當時來說那是個人人羨慕好單位。小余的愛人小楊子,是三里營糕點廠的蛋糕裱花工。我們小的時候,每到過生日,我媽就會拿一個盤子交給小楊子,託她買一個生日蛋糕回來。我記得那蛋糕好像是按斤賣的,一斤一塊四毛五,反正一個八寸盤的大約是不到三塊錢… …
小楊子個子很矮,挺有靈氣的一個人。她對待外人很謙恭,對小余卻很厲害。我有一次聽見小余在屋裡哭哭啼啼的,哀求小楊子說:“我的老婆呀,嗯嗯嗯,我錯了,嗯嗯嗯再也不敢了……”也不知道是鬧著玩兒還是真的。小楊子不生育,八十年代初,抱養了一個男孩,起名叫菁菁,長得白白胖胖方方正正的,和小余挺像的。機床附件廠分了樓房他們也搬走了,後來二十多年沒再見過這家人。
(3)我們家
小余家過來,就是我們家了。我爸是皮鞋廠的,效益很不好。我媽從烏盟農村上呼和浩特嫁給了我爸,一直沒有城市戶口。生了我和我弟弟以後,城市居民的供應糧就一直不夠吃,只能買議價糧。我爸挺辛苦的,除了上班,平時還在家裡面做鞋賺錢。家裡面平時我媽那一方的親戚不斷,什麼大舅、二舅、三舅、二姨、甚至於大舅二舅的小舅子也來住過,那時候負擔很重的。
為了給我們孃兒仨解決戶口問題,我爸求爺爺告奶奶的,派出所、公安局跑了不知道多少年。那時候,我們兄弟倆聽爸媽說得最多的,就是戶口問題。雖然年齡很小,但心裡也是為此焦急著。而且我記得那時候小學老師經常收戶口做記錄,我每當這時總是心驚肉跳的,我媽總是讓我和老師說戶口不在家,在父母單位,過幾天再給… …然後也就不了了之啦。
戶口解決了以後,我爸又在為我媽正式工作的事兒,跑關係託人。等正式工作指標落實了,我媽的眼病又犯了。那時候,他們倆總是往醫院跑,每次回來就帶著很多各式各樣的眼藥水,因為沒有冰箱,眼藥水都放在水缸旮旯,怕壞了。
我媽說我爸是屬貓的嘴饞,雖然人瘦吃不多,但是不吃肉就不行。我記得那時候有一種叫茄汁青魚的罐頭,是我爸的最愛,幾乎每天吃一罐,外面窗臺上滿滿的都是空罐頭盒子。那時候舊城大什字口子上,有個賣五香羊頭的回民老漢,人們都叫他“小疤子”,他一見了我爸路過就招呼:“夜尼個(昨晚)乃羊頭煮的咋說?今兒個再稍一個吃戚哇,不跟你要錢!”可見我爸買過他多少羊頭啦……
我爸年輕的時候總是恨世事不公,為啥讓他揹負這麼多的壓力,為此也經常和我媽爭吵。但是他們感情挺好的,現在我媽完全失明瞭,出入都是扶著我爸的肩膀。我爸前面走,她在後面絮絮叨叨的。我爸有時候聽得煩了就罵她兩句,我媽就很厲害地回嘴過去……
有一天我帶著我媽出去,她扶著我的肩膀說:“你太高了,手扶著胳膊很困,不如扶著你爸的肩膀得勁……”我覺得我媽雙目失明很不幸,但有我爸在她就很幸福……
(4)小金一家
小金一家是回民,住在最靠外。小金長得很像趙本山,是齒輪廠的職工,單位很一般。小金的妻子姓白,年輕的時候很愛打扮,是南馬路國營菜市場的職工。
小白很能幹,一般的打碳劈柴壘碳倉,這些活兒都是她操持。小金多數都是喝著嚴茶抽著煙,在旁邊當指揮。但是小金很會做飯,他家的飯多數都是小金做的,每到飯熟的時候,滿院子都能聞到香氣。
他們有個兒子小名叫東子,比我小四五歲,經常跟在我們兄弟屁股後面玩耍。有一天下午我在屋裡寫作業,小金和我爸坐在沙發上喝茶聊天。東子跑進來,手裡拿著一個開了封的避孕套和他爸說:“爸爸你看我撿住一個氣門芯兒。”小金當時就尷尬啦,愣怔了兩秒說道:“你從哪兒撿來的啦?歡歡兒給爸爸蠻(扔)了哇,乃(那)不是氣門芯兒,爸爸說劇團(涼房後面是晉劇團)的人們才用乃(那)呢……”話音未落東子兩手拍著屁股絕塵而去,兩個大人笑得前仰後合。那時我已經上初中一年級啦,多少知道點兒意思。趕緊跑出屋子在外面笑夠了,平復了心緒才回來。
東子後來長得很高,有一米九,成了一名公交司機。小金和小白單位倒閉以後,在回民區寬巷子西口,賣肉夾饃和煎餅。我路過的時候,還總招呼我吃點東西再走。後來聽說東子有了孩子,老兩口伺候孫子就不出攤兒了。小金在公園遛彎兒碰見我爸說:“老啦擺不行攤兒啦,掙上多少錢貼補人家,東子兩口子也不說你個好……”
後記:
小金家是於2000年搬離了大院的。我們家由於生活條件太差,無力購買樓房,一直守著這個小院子,住到2006年集體拆遷。拆遷後無力支付回遷款,所以放棄了回遷資格,只領了4萬元的拆遷款自己安置。對於我們家來說,那是一段灰黑色的記憶……
(大院的故事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