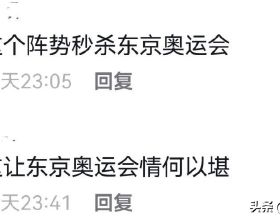我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在我們那個年代,雖然物質還不富裕,但家家戶戶都生養了一大堆孩子,多的七八個,少的也有三五個。
村裡孩子最多的人家要算鄰居黃大根一家。黃大根是個木匠,常年在外幹活,撫育孩子的擔子自然就落到他媳婦肩上。他媳婦粗胳膊粗腿,性子又大大咧咧,對孩子們難免有些溺愛,無論他們說什麼,她總是用大嗓門一口一個“好好好”的應承,久而久之,村裡的晚輩都管她叫好好嬸子。
好好嬸子一共生了八個孩子,除了老二和老四是男孩,其餘都是丫頭片子。
他們家老二叫金生,老四叫秋生。
金生屬龍,年長我們三歲,彼時是村裡的孩兒王。秋生屬羊,和我同齡,我倆都愛粘乎金生,是他屁股後面不折不扣的跟屁蟲。
俗話說:小孩身上三把火。我們渾身有使不完的勁,閒不住,也坐不住,天天跟著金生瞎折騰。
那時候,樹上長什麼,我們就順什麼,枇杷、桃子、楊梅、李子、柚子、桔子、柿子……這些水果常常還沒熟透就塞滿了我們的書包,自己吃膩了,就拿去跟別人換小人書或者滾珠輪子,能夠擁有一輛四個輪子的小板車是我們那時的最大夢想。樹上沒有果子可摘的時候,我們又把戰場轉移到田間地頭,挖花生,掘芋頭,刨紅薯,生上一堆火,把戰利品煨著吃,賊甜,賊香,賊過癮。
那時,我們樂此不疲的幹這些事情,雖然有嘴讒和飢餓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尋求小偷小摸過程中帶來的那份驚險和刺激。我們常常把戰利品上交給金生,金生為了犒賞我們的忠誠和勇敢,他有時講一段小故事,有時給一本小人書看看,有時給一份承諾——下次去外村看電影讓你坐中間位置。
我們這些小毛賊雖然大錯不犯,小錯不斷,但能堅守一條兔子不吃窩邊草的原則,從來不在本村偷雞摸狗。
我們不偷,鄰村的孩子常常跑來我們村裡偷,村裡人以為是我們乾的,投訴到我們家長那裡,害得我們不少人都吃了一頓“竹筍炒肉絲”(竹板子打屁股)。
平白無故捱了一頓打,金生決定要好好懲治一下鄰村的小毛賊。
一個月亮皎潔的晚上,他帶著我們在通往隊裡西瓜地的路上挖了幾個陷阱,然後我們躲在附近等著他們上鉤。不一會兒,他們果真來了,但他們沒有走我們設定的路線。為了阻止他們偷摘隊裡的西瓜,我們只好出面干預,雙方互相埋怨指責,結果大動干戈,好幾個人的腦袋都被開了瓢。
金生是我們的頭,大家都眾星拱月地圍著他轉,他吩咐我們做的事情,我們從來都是不打折扣地執行。
後來我和秋生上學的時候,金生已經是四年級的學生。從村裡到學校,從學校到村裡,我們天天形影不離地跟著他,尤其說是他在保護我倆,不如說我倆是他的馬弁,對他的依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一天在放學的路上,金生把兩個拇指粗的鞭炮插到一堆稀溼的牛糞上,說是為了鍛鍊我們的勇敢,叫我倆把“敵人的碉堡”炸掉。我們兩個傻冒接受了任務,各自點燃了一個鞭炮,結果鞭炮一響,我倆躲閃不及,全身上下都沾滿了糞末子,一路臭烘烘回家,還不敢把實情告訴家人。
類似的糗事枚不勝舉,很多我都忘了,但有一件事情影響太大,我至今記憶猶新。
一天下午,我們比往常提前來到學校,到了金生教室,裡面沒有別人,金生掏出一支毛筆和一瓶墨汁,說是他的課桌前沿掉了漆,不好看,叫我和秋生幫他上上色。秋生端著墨瓶,我用毛筆蘸上墨汁,左一下右一下刷起來,直到把課桌前沿全刷黑了,這才作罷。
剛上完一節課,校長把我和秋生叫到老師辦公室,看到一個穿白襯衫的女同學站在那兒哭哭啼啼,我還以為女同學的哭跟我們沒關,可當她把背轉過來,看著白襯衫上一大片黑乎乎的墨跡,我馬上知道這次闖了大禍,金生那傢伙把我們帶溝裡去了。為了洗刷自己的清白,我和秋生一五一十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校長。
金生被校長叫去批評了一通,下午放學以後,還被留下來給女同學洗衣服。他洗不乾淨,只好帶回家給好好嬸子洗。墨汁沾染性太強,嬸子也不能把衣服洗白,只好登門女同學家賠禮道歉,還照原價賠了四塊五毛錢。後來黃木匠從外面回來,得知金生幹了不少壞事,狠狠地把他修理了一頓。
這事發生以後,金生責怪我和秋生出賣了他,很長一段時間不搭理我倆,還號召村裡的小夥伴們把我倆當叛徒對待。
過了不久,金生被他家裡過繼給了城裡的伯父,從此以後我們就很少見面了。
多年以後,金生結婚,當年的小夥伴們去城裡喝他的喜酒,席間談起往事,我問金生當年為什麼要把墨汁弄到女同學身上?金生訕笑著說:她有一個萬花筒,一次也不讓我看。
新娘過來敬酒,我感覺有些面熟。
秋生對我說:你還不知道吧,我的這位嫂子就是那位衣服被我們弄髒的女同學呀。
不是冤家不碰頭,世間的事情居然真的這麼巧。
哦,童年,純真、幼稚而又妙趣橫生的童年,真的讓我非常懷念。
2021-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