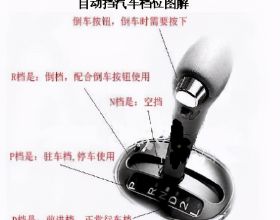文:楊曉光
立冬當天,從凌晨開始下了今年入冬的第一場大雪。幾天前氣象部門就預報了這場雪。先是下的雪米粒,落下來刷刷有聲,像漫天朝地上撒鹽。後來飄落的雪花,是奶奶形容的“棉花套子雪”,厚厚的,一片一片,飄飄灑灑,無邊無際地鋪展著。雪屑飛舞在樓宇之間,猶如裹天卷地的白色霧團,翻卷的雪霧宛若銀蛇狂舞,擦著樹梢迴旋而下,又掃過地面騰空而起,盪滌著天地間的汙濁與陰霾。
不由得想起刀郎的一首歌《2002年第一場雪》。日子過得真快。從當年的一首歌到今天這場雪,19年的漫長時光,猶如漫天飛舞的雪花,雪落無聲。這日子過得,就像如今越修越多的城鐵、高鐵,越來越多,越跑越快。
歲月是條單行線,義無反顧不回頭。記憶則不然,童年的雪人、少年的情愫、遠去的青春依然活在記憶裡。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記得歌手劉歡唱過一首木心作詞的《從前慢》:記得早先少年時,大家誠誠懇懇。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
從我記事起,鄉下的冬天冷,雪下得也早,一場雪覆蓋了另一場雪,冰雪覆蓋了一個冬天。一個冷字,足以概括漫長而又緩慢的冬季。當年地處冀東的昌黎縣曬甲坨故鄉,冬天一望無際的田野和鄉間小路,都被凍出深深的紋,長長的縫,彎彎的溝。北風那個吹呀雪花那個飄,衣服凍透,手腳凍裂,屋裡屋外的溫度幾乎相同。但冬天裡的皚皚白雪,美得令人懷念。
鄉土散文:回憶早年大雪天
雪落鄉村,小巷白了,房屋白了,田野白了,林梢白了,北風呼呼地夾著雪花,冷冰冰地撲打在臉上,人們並未感覺到冬天的寒冷,卻彷彿看到了來春的好年景。生產隊的社員家家戶戶,熱熱鬧鬧地把房頂上的雪掃到院心,再用平鍬鏟進抬筐,一筐一筐抬到院子外面。接著互相打著招呼,說著瑞雪兆豐年的吉利話,紛紛自掃門前雪,掃出一條出門的路,連通村路,通向村外。場院裡,麥秸垛、柴火垛上也下了厚厚的雪,一個個兒臃腫得成了不用堆的大雪人,非常好看。
那年月靠天吃飯的人們,忙著將糧歸倉、菜入窖之後,就像久別的人盼重逢那樣,巴望著天降瑞雪。雪大了田地水分大,可以蓋住冬小麥。麥田裡的雪被風踅得丘壑綿延,麥苗在雪下,雪擋住了寒風。人們說麥苗覆上雪如蓋一層棉被,真是既準確又傳神。待到春風化雪時,浸溼了麥田,灌溉了春苗。
樹枝上也裹了一層厚厚的雪掛,遠望虯枝樹掛,是平日難得一見的美景;散佈荒丘的墳塋披掛了雪裘,荒跡不見蹤影,平添一派聖潔;田園阡陌中溝滿壕平,雪地上難覓路的痕跡,急等著外出趕路的人,只能手拿一根木棍探路,深一腳淺一腳小心翼翼體會著行路難。人們根據樹行的指向判斷路徑走向,前邊的腳印,成為接踵而至的路標。
下雪的鄉村靜謐而安詳。雪給鄉村的孩子帶來了無盡的快樂,小夥伴們在雪中瘋玩,在雪中跑跳,捂雪花、堆雪人、打雪仗、滾雪球…… 名義上幫著大人剷雪,卻偷偷地把鐵鍬拿走,三五成群用鐵鍬攢雪堆,發揮鄉下孩子的豐富想象力,將雪堆拍拍剷剷、修修補補塑出雪人身子,再將滾出的大雪球安放成雪人腦袋,將掃把頭兒做雪人的手臂,用黑煤核做雪人的眼睛,戳個白薯吊子就是嘴巴,插上一截棒秸稈充當鼻子,一個有模有樣的雪人呈現在大家面前。我們學著電影裡圍著篝火跳圓圈舞的樣子,手拉著手繞著雪人轉呀樂呀,小臉、小手凍得通紅通紅的。手指凍麻了,索性搓一搓雙手攥雪球,拉幫結夥分兵對壘打雪仗。玩得髒了衣服,溼了鞋襪,通身是汗,頭頂冒熱氣。
在我的童年時代,冬天是一段漫長又緩慢的閒散時光,整個冬天都像生活在冰雪世界,就像多年後看到的電影《冰雪奇緣》,純粹而又美好。如今,追憶起那不復重來的生命軌跡,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小蟲的《雪花》:啊今年下起雪啦,白茫茫的雪花,一朵一朵的落下,告訴她我在想她。啊白茫茫的雪花,可不可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