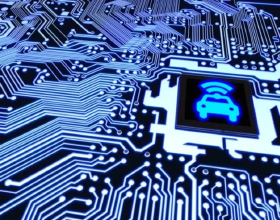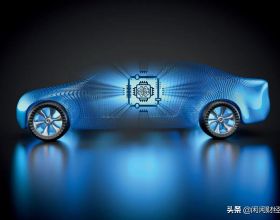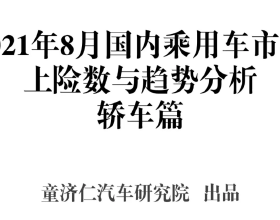李月
曲村-天馬遺址位於山西省臨汾市曲沃、翼城兩縣的交界處,地處曲沃盆地北部邊緣,南、北兩面與絳山、塔兒山相望,西臨汾河,滏河經遺址東南角繞過,地勢低而平坦,水土豐沃。遺址範圍東西約3.8、南北約2.8千米,面積近11平方千米,包括北趙、張、曲村等自然村。
曲村-天馬遺址作為晉國早期都城而聞名,1996年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百處重要大遺址”,遺址的重大發現晉侯墓地曾於1992、1993連續兩年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2001年列入“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今年適逢中國考古學誕生一百週年,晉侯墓地及曲村遺址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一、流淌的歷史,接續的文明:曲村-天馬遺址發現概況
曲村-天馬遺址是晉國的早期都城,周成王兒時“桐葉封地”的戲語在此延續。叔虞之子燮父由唐遷晉後,晉國逐漸經營壯大起來,幾度成為稱霸中原的地方大國,並創造出獨具風格、影響深遠的晉文化。曲村-天馬遺址自仰韶文化時期至元明時期均有遺存發現,尤以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的材料最為豐富,遺址範圍最為廣大,表明在晉景公遷都新絳(今侯馬市)之前,此地或一直為晉都之所在。
遺址的周代遺存主要有居址、墓葬兩部分。其中居址區被髮掘者分為六期12段,對應西周和春秋早、中、晚各三期,每期2段,文化面貌連續而未有中斷。雖尚未發現都城城牆、宮殿等標誌性建築,但出土筒瓦表明當地曾有大型建築存在,遺址內製陶、制骨和鑄銅等手工作坊遺蹟也說明遺址作為都城的重要性質。
遺址內墓葬材料尤為豐富,既發現西周春秋時期中小型墓葬六百餘座,又有兩處高等級晉侯墓地。其中北趙晉侯墓地共發現清理了9組19座晉侯及夫人墓,與之隔河相望的羊舌晉侯墓地現已探明5座大墓,發掘了其中的1組2座。晉侯墓地出土了數以千計的青銅器、玉器和原始瓷器等高等級隨葬品,有銘銅器中還記載了6位晉侯的名字,為墓主身份的確定和遺址性質的判斷提供重要證據。這些墓葬年代連續、形制多樣且儲存較好,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早期晉國墓葬發展演變的可靠序列。
二、從曲村外來,到曲村中去:曲村-天馬遺址的工作歷程
曲村-天馬遺址的考古工作可謂有兩大“戰場”,一個是以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為主進行的田野考古發掘“正面戰場”,一個是各級文物部門與地方群眾通力合作開展的文化遺產保護“敵後戰場”。
20世紀60年代前後,侯馬遺址作為晉國晚期都城的認識基本成為共識,而晉國早期都城的所在地尚不明確。1962年,國家文物局與侯馬工作站的工作人員在調查中發現了曲沃張村的戰漢古城,同年翼城縣清理出西周銅器墓,表明附近可能有重要遺存。1963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的張萬鍾先生指導四名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學生進行試掘工作,這是曲村-天馬遺址的第一次考古發掘活動,彼時還未將此地與晉都相聯絡。
1979年秋,鄒衡和李伯謙兩位先生帶領北大考古專業76級學生到晉南開展工作,在後續公佈的《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記》中,鄒衡先生明確提出曲村-天馬遺址為晉國都城的推斷,認為此地既是始封地唐,又是遷都新絳前的故絳,而晉國西周時期未曾有多次遷徙。此次調查發掘活動明確了曲村-天馬遺址的重要性質,為此後大規模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礎。
1980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將曲村-天馬遺址作為學生田野實習基地,開始進行隔年一次的大規模發掘活動。1980-1989年,基地先後進行了六次發掘活動。發掘集中在曲村北部和東北區域,全面揭露了遺址各時期文化遺存,並以西周春秋遺存為重,基本弄清了早期晉文化的面貌。這一階段的發掘成果集中體現於大型考古發掘報告《天馬-曲村(1980-1989)》。這套四冊、1124頁的發掘報告是十年辛勤工作的結晶,不僅全面呈現了發掘材料,其進步的發掘整理理念、科學的書寫體例、嚴謹的研究態度也為商周考古的發掘和報告編寫工作樹立了榜樣。1992-2001年,基地又陸續開展了六次發掘工作,將北趙晉侯墓地探明的大型墓葬全部發掘,包括附屬的祭祀坑和其他相關遺蹟。此外,2005-200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新發現的羊舌晉侯墓地進行調查發掘,探明的5座大墓已清理了1組2座,另有3座分組尚不明確。目前認為,羊舌晉侯墓地是北趙晉侯墓地的繼續。
圖四 《天馬-曲村》考古報告
當年的考古工作不僅有著學術任務,也在與時間競爭,與猖獗的盜墓活動鬥爭。80年代末,國內掀起規模空前的盜墓之風,曲村-天馬遺址亦罹此難,考古工作愈加艱難危險,也格外緊急重要。為保護珍貴文物、守護民族瑰寶,考古人表現出了不懼危難、勇於鬥爭的責任擔當。鄒衡先生和學生們四處奔走呼籲,於1992年就遺址多年遭受盜掘的現象向國務院提出彙報,同時在發掘中以繁重的日常值守工作保護珍貴文物。1994、1996年,山西省開展大規模打擊盜掘古墓犯罪的行動,當地公安部門與文物部門合作,收繳了大量盜墓犯罪文物。此外,當地民眾也有著文物保護的自覺意識,當深夜傳來盜墓賊炸墓的爆破聲,村民緊急出動將其趕跑,使得墓葬不至被徹底盜掘。
可以說,曲村-天馬遺址在艱苦惡劣的環境中被堅定支援,在危難緊急的關頭被牢牢守護。這片考古寶地培育出眾多優秀的考古工作者,將珍貴的文化財富回饋社會,同時也讓人魂牽夢縈,不斷地吸引著人們前來求學問教,贏得了行人駐足的目光,牽動著華夏兒女的心。
三、曲村為我,我為曲村:曲村-天馬遺址意義的思考
曲村-天馬遺址是晉文化研究的重要材料,是考古寶地,也是中華文化的寶貴財富。
從學術研究來看,該遺址的豐富發現推動了西周與晉國的年代學討論,使我們對早期晉文化的面貌有了直觀的認識,為進一步探索晉文化的來源與發展、晉國與宗周及其他封國的關係等問題提供了線索。晉侯墓地的發現為我們瞭解西周時期的喪葬制度和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提供了極佳的材料,出土的大量青銅器、玉器等珍貴文物推動了古文字、冶金、制玉工藝、原料來源與區域間文化交流等問題的討論。
對於考古學的學科建設,曲村-天馬遺址也有著重要貢獻。作為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實習基地,當地複雜的文化堆積是訓練田野考古技能的好材料。據統計,僅80年代的六次發掘中,就有147位不同年級的學生在此實習,是很多考古人夢開始的地方。與曲村有過“生死之交”的徐天進老師曾說道,在這裡的訓練“奠定了我之後能夠勝任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礎,從此,我才算是真正走上了考古的正途”。從曲村出發,北大的考古學子磨礪了意志、堅定了信念,逐漸成長為合格的考古工作者、優秀的考古學者,奔赴到江南塞北的田野工作中去。曲村-天馬遺址的考古工作也讓考古工作者積累了發掘、記錄和報告編寫的經驗,提高了田野考古工作的水平。
曲村-天馬遺址對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也有重要作用。依託於遺址的晉國博物館在展廳陳列之外,積極探索線下活動、線上交流、專家與網友互動等方式,充分展示遺址的文化價值。當地文物工作部門也與其他地區開展合作交流,透過館藏展品的互借、國家文化類節目宣傳等方式增強遺址的文化影響力。人們先是驚歎於出土重器的精美絕倫,進而好奇器物背後的故事,瞭解一段歷程,感悟一段歷史,自然而然加強著自己與民族文化的聯絡。
在新時代的歷史座標上,曲村-天馬遺址的價值還在書寫,我們與曲村的故事也將繼續。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