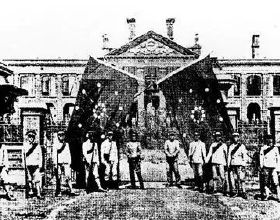我的 軍 人 生涯
(自序)
戎馬倥傯精神爽,戰鬥一生談笑間。
我作為黨的一個兵,已經度過了六十多年的軍人生涯。為了真實地記錄自己的鬥爭生活,使我們的後代能從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東西,這首先要求我們這些撰寫回憶錄的老同志,要有對歷史高度負責的精神。為此,我想談談自己的主要經歷,為讀者起個穿針引線的作用。
我的老家在湖北麻城的乘馬崗區許家象(現屬河南新縣)。自古以來,河南和湖北為兵家用武之地。從我記事起,軍閥連年混戰,你打他,他打你,鬧得烏煙瘴氣,哀鴻遍野。貪官汙吏和土豪劣紳趁火打劫,橫徵暴斂,魚肉百姓。
貧苦農民“一 年 到頭 忙,還是精打光”,賣兒熙女,顛沛流離,終年不得溫飽,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
壓迫愈深,反抗愈烈。一九二六年,大別山爆發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四鄉農民捉豪紳,殺土劣,抗租稅,砸煙館,搗當鋪,分錢糧,把那些穿馬褂的老爺們統統打翻在地。種田佬掌起了印把子,挑糞的當上了大委員。窮弟兄們一個個爭先恐後,要打出個自己的天下。革命是這樣的解恨,這樣的紅火。不幹革命幹什麼!
為了保衛革命果實,我們這些“泥腿子”建立了自己的武裝。由於我學過少林武功,還懂得一點軍事知識,被選為乘馬崗六鄉的農民義勇隊大隊長兼炮隊隊長。從這時起,我這一輩子就同槍桿子結下了不解之緣。
我們這支農民武裝號稱擁兵數千,但經常作戰的只有二三十人,稱作炮隊。平時發現有敵來犯,只要鳴土炮報警,就會四方呼應,八面來兵,連婦女和小孩也拿著木棒、竹竿、菜刀,趕來“呵嗬!呵嗬!”地吶喊助威。那時的武器是十分簡陋的,除了我們炮隊有幾支鋼槍以外,土槍、土炮、大刀、長矛、梭鏢是主要作戰武器。儘管如此,也能夠對付反動地主武裝的騷擾和進攻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形勢起了變化。蔣介石叛變了,汪精衛叛變了,我們黨內也有人跟著瞎嚷 嚷:“你們以前鬧錯了”儘管我們說不出多少革命大道理,但認準了一個理:不打不能安身,不打沒有出路!
不久,黨的“八七”會議精神 傳到了我們這裡。這年十一月,在湖北省委和黃麻地區黨組織的領導下,我們舉行了著名的“黃麻起義”,在大別山南麓燃起了武裝起義的革命烈火。這是繼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湖南秋收起義之後,又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起義失敗後,黨領導一部分起義武裝上了木蘭山,我們乘馬區有不少同志則留在本地繼續堅持著鬥爭。
當時,革命正處於低潮時期。有的人不幹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人叛變了。對於我和炮隊的 戰 友 們 來說,也面臨著關連身家性命的抉擇。
一年多來,我們這些世代為牛馬的農民,腰桿直了,說話粗了,去縣衙門裡可以大搖大擺,有錢人見了點頭哈腰,這還不是因為有共產黨的領導,還不是因為我們手中有槍桿子。放下槍桿子無疑是縱狼入室,自引殺戮。
在白色恐怖下,繼續鬥爭下去,隨時都有可能掉腦袋。但是,與其等那些劊子手殺上門來,還不如提著腦袋去殺出一條生路。人死算什麼?殺頭不過碗大的疤。
我們不能指望那些“老爺”、“大人”們發善心,施仁政,這些統統靠不住。靠得住的是自己,是鬥爭,是槍桿子。我們來自民眾,為了民眾,與其魚水相依患難與共;我們生在這裡,長在這裡,可以利用地形任意 迴旋;加上與我為敵的土豪劣紳死的死,逃的逃,反動勢力較小,堅持鬥爭的條件是具備的。據此,我們橫下一條心,豁上一身剮,在深山密林裡和敵人打起了遊擊。
一九二八年春,起義軍重返黃麻,我們這支游擊隊即與他們會合。不久,起義軍被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三十一師。從此,我開始了在軍隊的漫長生涯。
我們那時的鬥爭條件是相當艱苦的,常常靠葛根、毛慄、楊桃、山果、竹筍充飢果腹。長期吃這些東西,兩腿發軟,渾身沒勁。但戰鬥卻十分頻繁,今天圍個寨子,明天打個埋伏,後天再來個晝夜百八十 裡的急行軍,幾乎是天天打仗,有時一天要拚殺幾回。
儘管這樣,大家並沒有怨言,沒有人開小差,沒有人當孬種。那時,黨的領導很堅強,人們的思想也比較單純,風氣正,紀律嚴,團結好。大家常說:我們為了革命走到一起,雖不同生,可能同死,同志之間沒有什麼值得計較的。這些,都是我們紅軍隊伍能在惡劣環境中生存、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
這段時間軍事鬥爭的主要特點是游擊戰。我們的裝備給養大都是取之於戰,求之於民。軍事理論有不少則來源於《三國演義》、《水滸》、《封神榜》這些古典小說。戰術上也不太講究,一般都是見機行事,“賺錢就來,賠本不幹”“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當然,也有死打硬拚的時候。記得我們後來曾經打過一個叫大山寨的地方。這個寨子是光山西南(現屬河南新縣)一帶地主武裝盤踞的九里十八寨中最反動的一個,處處與我們作對,不打不足以除心頭之患。大山寨築在相連的兩個山頭之上,青石壘寨,牆堅溝深,易守難攻。我當時是攻寨的敢死隊隊長,看準了守敵槍少彈缺,帶著隊員們硬是往上衝。敵仗居高臨下,扔石頭,澆開水,砸尿壺,潑大便,把我們打了下來。
接著,我們頂著桌子,裹著被子,舞著大刀再往上衝。在這次戰鬥中,我被敵人從寨牆上一槓子打了下來,連傷帶摔昏迷了兩天兩夜。我醒來後,雖然渾身疼痛,心裡卻感到很舒坦,就好象睡了一大覺。死而復生,就是幸事。打仗總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燈,沒有什麼了不起。
在鄂豫皖根據地,我先後當了五次敢死隊長,帶了六七次彩。那時的醫療條件很差,掛了彩一 般 都 是 先取出子彈,再找點窩瓜瓤子糊上。就是負了重傷,也常常得不到及時的治療。不少同志就因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如今,打仗用上了飛機、大炮、坦克,用上了導彈、鐳射、核武器,象當年這些近於冷兵器的作戰方式,是顯得太簡單,太平凡了。不過,這些正是我們人民軍隊的起家之本。就象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的那樣:“它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
我年輕時去武漢,第一次看到了長江,感到真了不得,家鄉的小河小溪相形見絀了。其實,那時還不懂得,正是小河小溪才匯成了滾滾洪流。沒有紅軍初創時期的游擊戰,就沒有後來的運動戰、陣地戰,也不會有現代化的立體戰爭。我們不要妄自菲薄,總覺得外國這也好,那也好,別忘了自己也有傳家寶,也有拿手好戲。
仗越打越大,部隊也越打越強。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我們連續粉碎了敵人“羅李”、“鄂豫”、“徐夏”三次“會則”,在鬥爭中成長壯大了自己,不僅能消滅 敵人雜牌部隊和反動地主武裝,而且能夠成連成團地消滅敵人的正規軍。一九三〇年四月,我們紅三十一師和三十二、三十三師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我們師改編為紅一軍的紅一師。我在紅一師一團任連長。
這段時期我們打的仗相當多。打過楊家寨,打過楊平口,打過孝感花園,打過雲夢縣城,打過光山、羅山,還打過新洲、金家寨、六安......粉碎了敵人的多次大規模“圍剿”。
一九三一年元月,我們紅一軍與紅十五軍在長竹園會合,奉中央之命,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我在第十師二十八團任營長。此後,我軍主動出擊,飄忽自主,克新集,襲柳林,出齒京漢線,大戰雙橋鎮,生擒敵師長嶽維峻以下官兵五千餘人,獲得了鄂豫皖紅軍誕生以來進攻作戰的空前大捷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部隊再次擴編。在黃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我在十二師三十四團任團長。這時的紅軍已發展成擁有三萬餘人的雄師勁旅,對“圍城打援”等戰略戰術,也已經駕馭自如,運用嫻熟。緊接著,方面軍連續發動了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等四次進攻戰役,活捉趙冠英,痛打湯恩伯,生擒厲式鼎,嚴懲陳調元,重創張鍅,連戰皆捷,聲威大振。根據地日益擴大,鄂豫皖鬥爭達到了極盛時期。
在這短短三年裡,我由一名普通計程車兵當班長,當排長,直至當了團長,用現在的話來說,是比較快的。為什麼快呢?
人被打得沒有了,你是共產黨員,不幹不行。從戰士到團長,我打了上千次的仗,有些小仗一天打幾次,算也算不清。
從當戰士打到當幹部,我逐步學會了帶兵打仗的本事。我們的指揮員都應該具有豐富的鬥爭經驗,年輕幹部更需要經過嚴格的 實 際 鍛 煉。因為,戰爭不是兒戲,有無經驗,在戰場上完全是兩回事。
有人說,官好當,兵難帶,我看是官難當,兵好帶,難還是難在幹部。過去我們常說:強將手下無弱兵,兵好兵孬看幹部。有帶頭衝的官,就有不怕死的兵。
部隊好的戰鬥作風,是靠打仗打出來的,是靠好指揮員帶出來的。現在,部隊的成份有了變化,學生兵多了,文化水平高了,如何在和平環境中帶出過硬的隊伍,這是值得我們每一個幹部重視和研究的課題。部隊是要打仗的,軍人既要流汗又要流血,必須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獻身精神,這一點,我們任何時侯都不能忘記。
一九三二年秋,蔣介石親自出馬,調遣嫡系,糾集重兵,對我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起更大規模的“圍剿”
而當時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張國燾,沉湎於已得勝利,盲目輕敵,不作準備,指手劃腳瞎指揮。在其命令下,我團隨全師再出京漢線,攻打雞公 山,兩次圍麻城,佔領倉子埠,進逼黃陂城,四處出擊,車殆馬煩,連續作戰達八月之久。當敵情日益嚴重時,張國燾又慌了手腳,戰略方針連連出錯,以我疲勞之師倉猝就精銳之敵。我軍雖經馮壽二、七里坪、胡山寨、河口等處浴血苦戰,予敵沉重打擊,但終未能夠打破“圍剿”,被迫離開了鄂豫皖根據地。
今天回顧這段往事,仍覺心有餘悻。鄂豫皖鬥爭的失敗,雖有其客觀原因,但張國燾難逃歷史責任。
我以為,作為一個地區的高階領導者,萬萬不能只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張國燾只見區域性小勝,不察全域性安危,根本不懂得中國內戰發展中“圍剿”又“圍剿”、打破又打破的這種長期反覆的規律,順利時冒險,被動時失措,緊急時拚命,退卻時逃跑。我軍受如此機會主義者的嚴重干擾,豈有不挫之理。
一九三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我們出湖北,過河南,入陝西,抵四川;兩次越秦嶺,破冰涉漢水,冒雪翻巴山。我團時而前鋒,時而後衛。
一路上,草行露宿,荊棘載途,飢寒交迫,苦不堪言。加上敵人對我圍追堵擊,險情迭出,方面軍數次身陷絕境。在徐向前等同志領導之下,全軍上下患難同心,英勇奮戰,終究擺脫重圍,化險為夷,為以後的鬥爭儲存了一萬五千人的戰鬥骨幹。
我們經過兩個月的“大流動”,倍感根據地重要。西征以來,部隊猶如龍困沙灘,虎落平陽,受盡了窩囊氣,打夠了被動仗毛澤東同志說過:“革命根據地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儲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沒有根據地,游擊戰爭是不能夠長期地生存和發展的”,“一切戰略任務的執行和戰略目的的實現就失掉了依託”。紅四方面軍西征以來的切膚之痛就在於此。
四川人民飽受軍閥欺凌,迫切要求革命,只要有火種,遍地乾柴就會燃起燎原烈火。早在一九二六年,這裡就建立了黨的組織。
我軍抵達以後,立即受到了熱烈的歡迎當時,四川軍閥們正在成都、內江一帶混戰。方面軍總部審時度勢,順應軍心民情,作出了建立川陝根據地的戰略決策。從此,紅四方面軍進入了發展壯大的新階段。
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我軍迅速佔領通、南、巴,粉碎田頌堯三路圍攻,在川北站穩了腳跟。這年七月,部隊擴大了,我所在的紅十二師三十四團編為紅九軍第二十五師,我任九軍副軍長兼二十五師師長。接下去,打儀隴,打南部,打營山,打宣漢,過關斬將,連克數城。短短兩個半月,我方面軍各部共殲敵兩萬,繳槍萬餘,根據地得到猛烈擴張,方面軍也發展到八萬餘人,形成了方面軍發展史上的新高峰。
帶的兵多了,打的仗大了,對指揮員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實戰中,我逐步跳出了猛打猛衝的小圈子,注意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努力提高自己帶兵打仗的本領。只有把區域性與全域性、戰術與戰略、目前與將來緊密聯絡起來的指揮員,方可堪稱大智大勇,魯莽的軍事家是不足仿效的。
戰爭還告訴我們,兵無常勢,戰無定規。拘泥於“老套套”,滿足於老經驗,不足為取。在鄂豫皖時,由於諸多因素,我們常常以進攻為主,在進攻中求發展。到川陝以後,情況起了變化。
四川軍閥部隊眾多,地形熟悉。雖說彼此明爭暗鬥,矛盾重重,但在反共上卻是一致的。我軍新來乍到,雖已取得很大勝利,但終不象在鄂豫皖那樣,土生土長,深深植根於群眾之中。
這些不同的情況,決定了我們必須採取新的戰略戰術。如果我們只知主動出擊,不知積極防禦,勢必要吃虧碰壁。
反三路圍攻時,方面軍察情觀態,提出了“收緊陣地、誘敵深入”的方針。
在敵強我弱、優劣懸殊之時,先避不利決戰,儲存軍力,疲憊敵人;拖到敵竭我盈,即集中主力,進行有利決戰,畢全功於一役。此舉經實戰檢驗,頗見成效。其實,道理很簡單。打人時,拳頭直來直去,總不如收回再出有力。在後來的反六路圍攻中,“收緊陣地、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日臻完善,在我軍的戰略戰術經典上,增添了精彩的一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川大軍閥劉湘秉承蔣介石旨意,空全省之兵,集結二十餘萬人馬,分兵六路,對我發動了長達十一個月的大規模圍攻。方面軍不為敵氣勢洶洶所嚇倒,不為前所未有的困難所沮喪,不為某些挫折而灰心;避其銳氣,擊其疲憊,有頂有放,先防後攻,最後大獲全勝。
當時,我率九軍二十五師,堅守萬源以南的 大 面 山 陣地。劉湘在這裡掏出了積蓄二十年的老本,集中精華,孤注一擲,以求一逞。
我們和兄弟部隊一道,抱著橫豎有敵無我,有我無敵,誓與陣地共存亡之志,憑險固守,浴血苦戰,先後頂住了數萬敵軍的輪番進攻。
待敵再而衰,三而竭,我軍立即轉入“最精彩、最活躍”的應政,以摧枯拉朽之勢,快刀斬麻之捷,橫掃了四川六路軍閥。
就我參加過的堅守防禦而言,大面山一戰,規模大,時間長,很殘酷,以後再也沒有打過那樣的仗。
前些日子,我到了川北的通南巴和其他幾個縣。雖然河山已改,面目一新,但當年的戰場仍依稀可辨,戰鬥情景又歷歷在目。站在今天看昨天,是有不少經驗體會值得總結的。
堅守防禦,重在一個守字。守住一點不走,這是敵人最頭痛的。部隊特別是幹部,首先要有寸土不讓拚命頂的決心和人在陣地在、絕不後退一步的氣魄。在緊要關頭要咬住牙,我困難,敵人更困難,勝利往往就在最後五分鐘之中。
大面山打得好,還因為部隊覺悟高,紀律嚴,士氣旺,作風硬。那時,我們上至軍長下至戰士,每人一把紅纓大刀。情況緊急時,管你師長、軍長,八角帽往下一拉,帶著部隊就往上衝。人人眼睛都朝前看,向衝在前面的同志看齊。活不繳槍,死不丟屍,不消滅敵人不回頭。
反六路圍攻勝利後,我調至四 軍 任 軍 長。爾後,部 隊 北 進 陝南,攻克寧強縣,佔領陽平關,進逼漢中城。接下去又強渡嘉陵江,攻南部,破梓潼,戰江油,克北川,打得四川大小軍閥焦頭爛額,防不勝防。記得那時有首歌
“紅軍過了河,羊子奔索索,冬瓜遍地滾,猴子摸腦殼,矮子挨鞭打,劉湘怕活捉,請問委員長,你看又如何?”
這首歌維妙維肖地勾畫出了楊森(羊子)、田頌堯(冬瓜)、鄧錫侯(猴子)、李家鈺(矮子),劉湘等人的窘相醜容,至今想來,仍然忍俊不禁。
張國燾這人很“特別”,我們明明勝利了,他卻看成是失敗。反六路圍攻勝利後,他認為根據地遭到敵人嚴重破壞,紅軍待不下去了,說什麼:“與其被敵人趕走,不如主動撤走。”
並乘我主力部隊在前線浴血奮戰之際,他在後方不經任何會議討論,自行由東到西收攤子,把黨政機關和地方武裝一鍋端到了嘉陵江西。我們為之奮鬥兩年的川陝革命根據地,就這樣被其輕易葬送了。我軍又陷進退失據的困境,開始了艱難曲折的長征。
歡迎關注|更好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