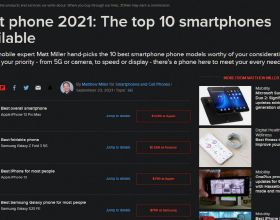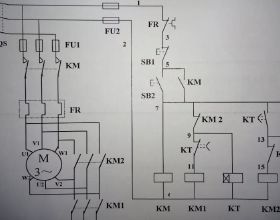近日,中國嘉德2021秋拍陸續發出拍品公告,中國書畫版塊依舊綻放張大千晚年潑墨風采,但此外,還見一件大千“生貨”,畫中款識“黃鶴山樵夏山高隱圖”,公告推文出於雅俗共賞、通俗易懂之用,另題:《致李秋君夏山高隱圖》。(以下稱《致李秋君》)

圖1致李秋君夏山高隱圖 張大千161×63 cm 設色紙本立軸1947(49歲)
出版:1、《張大千學術論文集》/P151“王蒙筆力能扛鼎六百年來有大千—大千與王蒙”/臺北歷史博物館1989
2、《壬申新春書畫展》封面/圖編1/香港集古齋/1992
展覽:“壬申新春書畫展”/香港集古齋/1992-1
圖片/中國嘉德
為了便於理解作品的現實美學意義,筆者查閱相關資料,逐層剝殼,從純視覺角度與讀者共探本體的創作秘密,即對作品怎麼看的問題。此畫為張大千1947年49歲時臨摹元代王蒙1365年繪製的《夏山高隱》,時隔582年,王蒙畫這張畫時57歲,贈與一個叫“彥明”的友人,地點在蘇州寓舍;張大千繪這張畫時在上海,送給紅顏知己李秋君,兩位畫家不曾穿越時空,但都為人情世故見證友誼而作。關於這張畫收藏中的兩個重要人物李秋君和謫仙館主,文末再做故事梳理。

圖2夏山高隱圖 元代 王蒙149×63.5cm 絹本設色立軸1365(57歲)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片/網路
張大千中年所繪《黃鶴山樵夏山高隱圖》處於中高等水準。何為中等,將所臨畫件視覺影象層面的問題都完成了,在傳統美學中歸於“有形”的範疇,從具體造型而言,各個物象佈局完整,形體描繪適度,依照原創者的經營位置理念“複製”一遍,這在科班教育中處於第二、三年的習作要求。不過,張大千雖然從臨摹學習角度所創這件王蒙的巔峰之作,但他畫中在造型上還是做了多處更改,沒有完全按照王蒙理想中的虛構世界。
先看畫中的人物活動,王蒙畫了6個人、1只鶴和1條小狗,分3組空間勾勒情節,彼此關聯又相對獨立。右側一高士在榻上乘涼,手舉羽扇,旁邊一個童子端著水盆,做出等候服侍主人的姿勢,這時主僕二人突然被院外另一個童子的調鶴行為吸引,調鶴的小孩跟仙鶴一同展開臂膀,引導仙鶴展開“白鶴亮翅”,這個時空的行為一下子把我們拉回到古人的生活,神秘有趣;往左走,過了河,叢樹中若隱若現一個帶篷的小船,這種“視點”有好幾處,顯示王蒙理性又絕對的空間理念,雖然被樹林擋住了目力,但透過斑駁的枝葉間,還是透射出隱藏空間中的可能故事,順勢左上,山中行走一個穿官服的中年男子,手捧敕令,不知是徵召高士還是來祭山;最左側繪製一山中農家,婦女在屋內盤坐,丈夫手端浴盆走向畫外,中間一隻小狗靜臥院中,豎起雙耳,頭轉向官人入山的方向,好似聽到客人將至。不論我們了不瞭解古人的生活,但是聽到這樣世外桃源的無爭景象,大概就羨慕起古人的思想高度吧,王蒙在創作的高峰期,畫了很多山中隱居的理想世界。面對這個夢想的藍圖,張大千更改了模樣,整體來說是簡略了原畫中的故事情節。
張大千畫中只有3個人物。右邊屋中主人撫琴,旁邊立一侍童;遠處走來的官人換成了策杖而行的隱士;左側茅屋門口模糊一個人影,不知是站立的婦人還是門廊的裝飾;至於童子調鶴、農家夫婦日常的2個場景都沒有了。為什麼張大千簡略了人物勾勒?一是500年前的古代生活與當下社會完全兩個形態,古今文人共鳴未必全部合拍,細節之處,今人沒有盲從的必要,可以理解張大千在細枝末葉處不拘小節;還有一個解釋,凡畫過中國畫的人,尤其臨摹古人作品時,人物新增都是最後才釀氣落筆,沒有充分心手合一的準備,便不會輕易下筆,人物勾勒本來就幾根線條,十分洗煉,畫錯一筆傷及整幅大作,達不到形神兼備就放過筆墨,因此張大千有“祛難”的嫌疑。可能讀者覺得第二個分析有些犀利,不繪者沒有親身體會,繪者自然心中有數。但這也符合張大千的學習邏輯,將每個大師的優點都研習一遍,在大精髓處用心力,小處多有收手,不耗精力。
既然提到“精髓”,那麼都知道王蒙以“密體”聞名於世,張大千學習王蒙,真的達到王氏密體的功夫了嗎?沒有,張大千還是省了力氣,不怪傅雷對大千山水從不看好,點評處處充斥貶義,認為他是“投機分子”。不過此文不在過往文字糾葛中明是非,就來看看,張大千習作與王蒙原作有多少距離。王蒙《夏山高隱》遠山最能體現用線之“密”的特徵,比較二人筆墨的具體,王蒙的“密”:淡、疏、寫,張大千的“密”:濃、密、染。王蒙寫密不求密,在密中見疏朗、見淡泊,反覆積累解索皴,形成視覺上的密密麻麻,其實中核還是皴寫出來的;張大千遠山用墨更濃,且分量十足,染大於寫,缺乏王蒙的疏朗和透氣,比較看出,王蒙筆墨為“疏密”,張大千為“密”。不看原作,不瞭解王蒙畫風,就品不出張大千中年筆墨的成長性,所以說“中等”不為過。
為何又中上等?因為張大千即使沒有完全“複製”,也還是融入了自己的面貌,在設色上體現了張家面孔。張大千早年隨哥哥去日本學習染織技術,對染色有著深切領悟,再者小時候他的母親和姐姐都畫花鳥,對他埋下藝術啟蒙的種子,40年代又去敦煌臨摹3年工筆重彩,這3個閱歷足以闡釋他對設色的敏銳和鍾愛。以至晚年變法時,還是走了自己最拿手的臻技,讓如今拍賣市場的大千潑墨回回敲出高價,凡是帶色的都比純水墨貴。
這件畫的不足在哪裡?既然張大千摹王蒙之作,我們還是要到原作中找密碼,或許有人認為繪事風格是個人行為,接受各家面孔是藝術該有的包容原則,與古人做絕對比較太過苛刻,不近人情,此言論者不懂“摹寫”之事,不予辯駁。大千中年山水的最大遺憾是深度不夠,當然這個深度是跟真正的大師相比擬的,他這期間學的就是傳統,在歷代古人身上汲取各家招式,將所有獨門秘籍瀏覽個遍,這就像金庸筆下的青年楊過,早年因命運不濟而吃百家飯,每次跟高手對招時,花樣百出,但多打幾套招式就走下風了,連牛鼻子金輪法王這樣講他時,他內心也是承認。好在這種人又聰明無比,打不過對方卻總能化險為夷,找到竅門走為上策。張大千年少時被土匪抓去當文書,虧他寫得一手好字,出入匪窩盜窟,為保命他不得不假意隨從,後來被二哥救出,張大千靠智慧保全自身,不是一般人的膽量。但不論對於武俠之人,還是繪事而言,最終面對的還是真本事,需具備自家面孔,才能成為一“家”,否則就是平常工匠,沒有藝術史論和文學的高度,入不了正宗,也稱不上宗師。
我們看《致李秋君》的中景和王蒙畫的中景,這個比較起來就有點殘忍。張大千不光筆墨有廢,而且耐性還不夠,在沒有足夠深入時,就急於往“高處”走,可以這樣理解,王蒙從側面看是立體的直角狀,而張大千是立體的弧狀,王蒙功夫打進深處,流出最清澈的泉水,張大千力度有欠,淌出的是河水。這個比喻不漂亮,但便於理解。王蒙中景的溪流是寫出來的,留白形狀渾然天成,張大千染的技法比較多,刻意描出山泉形狀;前者系自然主義,以石頭的強烈體感襯托山泉之柔性,剛柔相濟,後者筆墨粘連在一起,沒有自然主義中格物致知的純理性精神,石頭三維體感沒完成,汩出的泉水沒有著地,非王蒙畫中靜水深流的境界;這是研習的韌勁,過去人們把張大千比喻成明代仇英,但張大千沒有仇英的極端耐性,可能大千幾天就完成一幅畫,仇英一幅畫需要數月。不光是大的中景顯現這個問題,每個小的空間,都能體會出這個深淺之比較,大千用墨用色之多,試圖加入更多元素與風格,但是也丟掉了最本真的東西。中國畫到深處講陰陽,是思想的層面,單靠純視覺並不能夠達到那方境界。
這件作品成於1947年,正處抗戰結束不久,那時他很有眼光,出重金收購一批宋代山水,且他以北派山水為研習正宗,40年代末他在西南地區寫生時,畫風也是北派之雄氣,但融入西南地區的秀潤和奇險,這是張大千骨子裡的氣質,跟隨他一生的創作。但是整體而言,40-50年代是大千學古期,有些作品甚至有泥古端倪,用筆和用墨的法度並不嚴謹,但寫生有自家新意。至於後世刻意誇大他“造假畫”的極端能事,想來大千本人也不甘承認,甚至說他的“假石濤”瞞天過海,騙過鑑定高手黃賓虹,純屬扯淡。黃賓虹是個一生講究院體法度的人,寫文章、畫畫甚至制墨都有理有據,可以說過分理性的人,還在故宮做過書畫鑑定工作,怎麼可能辨不出深淺,簡直笑話。到了60年代,張大千走遍名山大川,加上前期努力的資本,出手就有畫的感覺了,並且他想到一定要創新,以完成自己此生的繪畫使命,潑彩是他展現自我的真正天地。耗時一生,撇開世俗,有理想的畫家都以代山川而言為終身使命。
中國嘉德公告推文中介紹關於此畫流傳過程,李秋君作為張大千粉紅知己,併為他提供上海畫室自由創作,情感之深切,成為佳傳。臺灣著名導演謫仙館主楊凡的親筆文章又為此作增添傳奇色彩,一來見證畫之真偽,二對世人瞭解張大千的生活閱歷添磚加瓦,包括篆刻家陳巨來、中文教授臺靜農、哲學家莊慕陵等人,都參與大千藝術世界的腳註,對今人瞭解大師做出了人文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