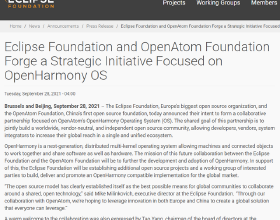多年以前,周家莊的周澤彈的一手好琴。他上有兩個哥哥,俱已成家,因二老年事已高,弟兄三人從不外出,都在床頭盡孝。周家三兄弟中,周澤年齡最小,剛滿十六歲,從小喜好彈琴。當哥哥的疼愛弟弟,託人從遠方給他買回一張古琴,周澤愛如生命,從不離身。
這一日,周老太由於久病不愈,一口氣沒上來,撒手西去。周府上下都十分悲痛,人人泡著眼淚辦理喪事。周家平時待人寬厚,人緣極好,所以弔孝的親友川流不息。
這些親友中有些年輕人好事,聽說周澤琴彈得好,就把他約至後堂再三央求彈奏一曲。周澤說:“那可不行,既讀孔孟之書,必達周公之禮,我正在守孝,哪能彈琴作樂。”周澤雖然一再推辭,但架不住那些官宦子弟軟磨硬泡,高帽一頂一頂的送,自己一時被說的技癢,於是摘下古琴,調好文武二絃,輕舒五指,一曲《病中吟》端的是如泣如訴。
再說老大老二在靈棚披麻戴孝的忙著給弔唁的人遞香遞酒還禮,突然聽到琴聲從後堂傳來,聲音怨慕低垂,撼人心魄,知道定是老三在撫琴。
老大繞開眾人,趕至後堂,見老三一曲終了,兩眼正呆呆的看著琴絃,不由一陣光火,說:澤弟,你是糊塗了嗎,古禮有云:親喪三年不聞歌樂。現在母親屍骨未寒,你在這彈琴,豈不讓親友恥笑。
周澤自小受寵,父母哥嫂對他從來都是好聲好氣,哪受得了這一番重話,一時語塞,想想,辨無可辨,不禁滿臉通紅,愧悔無地,少年人心氣高,抑鬱之氣無處宣發,漸成心結,從此之後,周澤茶飯不思,終日枯坐,一天天的消瘦下來。
家裡最心細的,要數大嫂子,這些天周澤的變化沒能逃過她的眼睛,只道弟弟是乍逢人生大變,心神皆亂的緣故,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便找到周澤,問:“老三,這幾天你書不念,飯不吃,天天躲屋裡不見人,到底咋了,是想成家了,還是想媽了?跟嫂子說說。”
周澤說:“都不是,就覺著心裡悶,想外出逛逛,散散心”。次日,嫂子把老三的心事和老大老二說了,哥哥疼慣了弟弟,何況如今沒了母親,更不想對他太過約束。
倆人商量好把周澤找來說:“給你一匹馬,一百兩銀子,到姑姑、姐姐、姥姥家逛逛吧,散散心就回來。”周澤謝過哥嫂,縱馬而去。
上哪去呢,他沒有譜兒。親戚家裡,他不想去,去了肯定受拘束,不如一個人,天馬行空,浪跡天涯。想起那天的事,依然無法釋懷,心裡想著:反正自己成了不孝無德的人,隨便走到哪兒,自生自滅好了。
縱馬行出一里之遙,來在一座廟前的大柳樹旁。他下馬放了韁繩,朝馬拜了拜說:“馬兒啊馬兒,從今以後天下之大,也只有咱倆相依為命了。”說著眼淚滾滾而下。
那馬像是聽懂了人話,馱著主人朝一個方向奮蹄而去,越走越快,轉眼已是百里開外,周澤坐在馬上昏昏沉沉,餐風飲露,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
這一日行至好大一片村莊前面,馬停住了,打聽之下才知道這村叫黃家莊,距家鄉已有千里之遙。
此時天色將晚,周澤走進一家客棧,店夥計迎上來問:客官是打尖還是住店?周澤說:“要間清淨的客房,我要住店。”店夥計栓好馬,領著周澤一連看了幾個屋子全不中意。
店夥計揣摸不透客人心思,有些著急:“不是小人誇口,黃家莊緊鄰官道,大大小小客棧也有幾家,不過像我們黃家老店這樣舒適乾淨的絕不會有第二家。不知您老想住什麼樣的房間?”
周澤倒沒聽出店夥計發急,隨口說道:只嫌不夠清靜,能有個獨門獨院才好。”店夥計眼珠一轉,露出一副古怪的樣子,笑說:“清淨不是嗎,容易,您跟我來,這回保您滿意。”說罷領著周澤穿過堂屋三拐兩轉來到西跨院。開啟院門,一溜三間上房果然十分清雅,東屋上著鎖像是無人居住,院中一株大槐樹枝繁葉茂。
店夥計把周澤安頓在西配房,重新清掃,然後放上明燈一盞,暖茶一壺,擺了四色小菜,一飯一湯,便退了出去。
周澤飯後一時睡不著,又想起了過世的母親,撫了會兒琴,灑落幾點傷心淚,直到三星將落才迷迷糊糊睡去。
次日起身備馬,不料那馬揚蹄長鳴就是不肯出門。周澤摸著馬頭說:“既然你不願走,那咱們就住著。”一天,兩天,一連二十幾天,那馬始終不肯離店。周澤每晚都是面對清燈一盞,暖茶一壺,彈琴解悶。他的琴越彈越好,後來連自己也醉進琴音之中。
這一晚,周澤正彈的出神,不知從哪兒來了位姑娘悄無聲息的出現在身旁。這姑娘長得眉清目秀,桃花粉面,人才出眾,相貌壓人。
周澤想:深更半夜一個姑娘貿然出現,決不可能是人。不過自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是鬼是人都無所謂了。於是,接著彈琴,待一曲終了,姑娘仍然沒有離去的意思,便問:“敢問芳駕何人,是人是鬼,想幹啥動手便是,反正我活著也是了無意趣”。
姑娘說:“公子想錯了,我家住隔壁,姓王,感公子琴聲優美,已至通幽之境,清遠雅緻,不禁心馳神往,特為聽琴而來,別無它意。"
這王姑娘既未說明自己是人是怪,周澤也不再深追,將手瀟灑一讓,說:“既如此,姐姐請坐。”
從此王姑娘每日夜半必到,聽上個把時辰就走。一來二去,兩人情意漸生。這一天,周澤早早要了一桌酒席擺在屋裡。天交子時,周澤起身望空一拜恭敬地說:“請姐姐!”
話音未落,王姑娘已在屋中。二人飲過三杯酒後,周澤說:“今日相請,專為辭行,請再滿飲一杯,就此別過。”王姑娘問:“為何忙著走?”周澤說:離家時帶的盤纏已所剩無幾,再住下去,只怕要凍餓街頭了。不瞞姐姐,我原本心頭愁悶,只想信馬由韁浪跡天涯,和姐姐數日相處,心中憂煩已去,思鄉之情日增。”
王姑娘說:“請問公子家住哪裡?”
周澤說:“數百里之外的周家莊。”
王姑娘說:“既然小女子可以讓公子消愁解悶,那我願追隨公子,長伴身邊,不知公子可願意?”周澤聽了大喜過望,不過馬上憂愁起來,說:“姑娘此番心意,我定不相負,不過我身上的銀兩不多了,到時候山窮水盡,還要連累姑娘捱餓,豈非有負姑娘厚意。”王姑娘說:“不怕,我身上還有些私房錢,足以到家了”。
周澤大喜,二人收拾停當,當夜就出發。一路遊山玩水,策馬揚鞭,路上又添一匹馬,沒多久便家鄉在望,周澤看著熟悉的景色,不禁感慨:數日之別,已是兩番心境。
此地距周家村不過半日行程,看天色已晚,二人就近找家客棧投宿。當晚,二人備好酒菜,王姑娘說:“今晚我彈一曲,請公子指教。”周澤驚奇地說:“你也會撫琴?怎麼從沒聽你說過?”
王姑娘說:“實不瞞公子,我早就喜歡撫琴,不過沒有公子彈的好就是了。”說著便對著月光彈了支曲子,琴音像是從靈巧的指尖流淌出來,時而如飛瀑般湍急直下,時而像泉水般幽靜流深,優美的旋律比之周澤別有一番婉約空靈。周澤想不到無意中得此知音良伴,更是高興。
次日,周澤到家見到久別的親人,尤其是還帶回一個知書達理的姑娘,家人歡喜不盡,紛紛拉著周澤,欣喜的打量著,當天殺雞宰羊,好不熱鬧。
大嫂子是個伶俐人,見兩人聯袂而歸,千里同行,其中定有故事,便私下對丈夫說:“王姑娘一個十八九的姑娘來到咱家,每日出入不便,時間長了街坊也要議論,我看她樣貌人才都配得上澤弟,不如早給他們把婚事辦了”,老大說:“也好”。次日全家一商量,廣發請帖,殺豬宰羊,大宴賓客,倆人正式拜了天地。婚後不久媳婦便有了身孕,闔家又是一喜,小夫妻之間更增一份恩愛。
新過門的媳婦事事勤快,活計做的一多,出奇的地方可就顯出來了,女工、針線樣樣拿的起放的下。繡花花瓣上能看到水珠轉,剪鳥鳥的毛會動。一來二去全村郡知道周家娶了個巧媳婦。
周家有個堂房妹子,今年二十歲上下,人長得倒還端正,就是手腳笨點。今年媒人給說了門親事,對方是官宦人家。本來是心滿意足的事,不想中間出了點意外,定親後男方要看看針線活計,送來一匹精綢,一匹錦緞,相約以十天為限,要看看周家妹子手上的活計。妹妹急忙來到堂兄家商量。大嫂、二嫂一聽都傻了眼,活倒不難,但是就怕手藝不出尖,入不了對方的眼,丟醜事小,耽誤了妹子的婚事,可誰也擔待不起。
這時老大說了句:“何不求求弟妹。"一句話提醒了大家。於是,找到周澤媳婦把事一說,王姑娘滿口應承,說:“妹子放心,包在我身上,十天之後,來取就是”。大家一看這樣,也都放寬了心,以王姑娘的手藝,自然不在話下。
誰知事不談巧,次日,王姑娘竟然一病不起。先是不能見光,繼而臥床不起,接著飲食俱廢,吃一口吐一口,大家都嚇壞了,這都是下世的光景,可憐她一個年輕人,還大著肚子。
家裡人急得團團轉,卻束手無策,郎中請了不少,每個人都撂下一句“脈象奇絕,見所未見”便落荒而逃,到第五天上,家裡來了個道士,不請而入,說是化緣,進了門便不走了,又說此處進了不乾淨的東西,恐怕與人有礙,要在此住上一晚。
老大見這道士滿口胡言,轟也轟不走,只得實言相告,說:“家中弟妹沉痾不起,實在不便留宿外客”。道士聽了,說“小道學過兩年醫術,或可一試”。聽了此話,全家人眼睛一亮,連忙引至王姑娘病床前,拜請道士拔苦救難。
周澤媳婦病了幾天,好似話都說不出了,只看著道士哀哀流淚,道士扶脈良久,不發一言,半晌,方喟嘆一聲:“也是孽緣啊”,轉身對周澤說:“彈琴給她聽,或許有用。”說完,出門便消失了。
周澤一聽,便連忙淨手,擺琴,對著媳婦便撫起琴來,說也奇怪,一曲未了,媳婦臉上已是回過血色,再彈一曲,已沉沉睡去,周澤也不嫌累,一曲接著一曲,日夜不休,那琴聲激烈處如萬馬奔騰,撕金裂帛,婉轉時如百鳥鳴春,餘音繞樑。王姑娘也一日好似一日,到第四天,已能下床走動,只是稍顯虛弱氣短。
這幾天,周家妹子也是坐臥不寧,她是為自己的婚事著急,可又不好去催,眼看期限只剩一天了,只好暗自垂淚,嘆自己命苦。
這些周澤都看在眼裡,為難地對媳婦說:“這事兒當初不如不應了。如今落得應人事小,誤人事大,可咋辦?”
媳婦說:“許人一諾,千金不易,我掙命就是了。”
周澤說:“可惜沒時間了”。
媳婦說:“我今晚就做,不過有一事相求,望夫君答應。”
周澤問:“我自然會答應,啥事?”
媳婦半認真半撒嬌地說:“第一,今晚做活夫君不許偷看,第二,我要借古琴一用。”
周澤奇道:“針線活還能用上古琴?”
媳婦也玩笑地說:“這把琴,你彈這麼久了,可知道它好在哪裡?”
這個,周澤還真不知道,自那日兄長把古琴買來,周澤是朝夕相伴從不離身,只知這琴用料上乘,音色絕美,還有什麼主貴之處他還真是未曾察覺。媳婦說:“這琴有三種調法。正調琴音可傳三里五村,反調可傳千里之外。正反互調,上可傳天庭,下可入地府,我這命,其實是夫君用琴聲幫我續的。”
周澤不信,問道:“這琴朝夕由我攜帶,你怎麼知道這些詳情?”
媳婦說:“這個嘛,以後再告訴你。三更將到我得趕快趕活兒了。”媳婦進屋後,不大會兒就傳來陣陣琴聲。周澤心裡納悶兒,究竟彈著琴是怎麼做針線的,忍不住從門外悄悄向內偷看。
只聽那琴聲時而激昂,時而低沉,時而靈動俏皮,充滿歡快的節奏。再看屋子裡放的十張桌子周圍,突然颳起了十個旋風,每個旋風中都有針線牽出,隨著琴聲在錦帛上穿插跳躍不停。周澤原本知道自己的妻子來歷不明,見此情景,也沒大驚小怪,輕輕走開,在院子裡賞月聽琴。
一直到東方破曉,那琴聲變得越來越尖,越來越細,猶如琴絃越繃越緊,周澤緊張的雙手是汗,終於,啪的一聲,四周一片寂靜,周澤暗道不好,慌忙搶進房內,抱起倒在地上的媳婦,此時,媳婦嘴角流血,氣若游絲。周澤強忍住眼淚,輕聲呼喚著媳婦名字。
半天,王姑娘悠悠醒轉,慘然一笑,說:“咱們夫妻緣分已盡,該分手了。”
周澤急得雙手顫抖,哭著說:“我們是恩愛夫妻呀,你怎麼忍心分開!”
王姑娘說:“蒙夫君不棄,為妻得以重享人間煙火,雖然你對我的來歷從未問過,但你我夫妻一場,臨別之時不能再讓你糊塗,我本是黃家莊黃員外的女兒,已死去三年。這把琴本是我家傳之物,小女子自幼與它相伴視如生命。不想一日家中失竊,古琴就此下落不明,我思念成疾,抑鬱而終,父母雙親,沒多久也相繼離世,宅院就此荒涼敗落。
“那一日聽周郎用我家傳古琴彈奏,覺得耳熟,便去拜訪,我連聽多日,已可借琴音穩住身形,不再怕白日見光,本想借此機會,收回古琴,但看公子人好,愛惜古琴,便生愛慕之心,直到今日。
周澤這時已成了淚人,啞著嗓子說:“那個道士…”
“對,那個道士,知道我的身份,本想滅我魂魄,看我無心害人,對你也是痴心一片,最終放過了我,如今,琴絃已斷,我命在頃刻之間,為妻有幾句話,請夫君千萬謹記,如此,我夫妻可能還有團聚之日。”
周澤說:“娘子請說。”
“此琴不同凡物,我本鬼魅之身,借琴聲加持,方結成肉胎,我去之後,會留下一個肉球,裡面就是我們的孩子,夫君撫養他長大以後,我衣箱裡有避腐珠一顆交給孩子,以便日後相認。這把古琴夫君好好儲存,你我夫妻再團聚全靠它了。”
王姑娘的氣息逐漸微弱,少時,一片青色火焰籠罩了全身,火光散去,剩下一個肉球,周澤拿刀切開一看,裡面有個男孩,哭聲洪亮,取名叫錦瑟,周澤看兒思母,後半生把心血都澆鑄在撫養兒子身上。
錦瑟自小聰明伶俐,長大一十八歲已是名震一方的才子,三試科場,均是頭籌,最後由皇帝欽點為狀元及第。回家探親祭祖時,按著爹爹囑咐來到黃家莊,住在了黃家店。
飯後他找來店老闆問某年某月是否有個公子曾經在這住過,那個店老闆即是當年那個店小二,此時已是鬍子拉碴半大老頭兒了。回說道:“是有這麼回事,就住在後跨院。”錦瑟說:“帶我去看!”
店老闆領路,來到當年周澤住過的地方,當年那個院子依然荒草滿地,院中那棵槐樹更加茂盛,對面屋的門仍是緊緊鎖著。
狀元問:“為何上鎖?”
店老闆說:“我也不大清楚,過去聽帳房先生說,這家本是員外,只因小姐早亡,家境敗落,不知道為什麼小姐棺材一直存放在裡面。二十多年了,這門一直鎖著,誰也沒有進去看過。”
狀元牢記父親的囑咐:一定要找到生身之母。一聽裡面有停屍的棺材,哪肯放過,命令店老闆開啟房門,啟開棺蓋,只見棺內躺著一個相貌十分美麗的女子,緊閉雙目,像是睡著了一般。那女人胸前掛著一顆發光的珠子,和父親給自己的那顆一模一樣,知道這就是母親了,想到這麼多年,母親一個人孤零零的躺在這棺材裡,頓時五內如焚,忍不住撲上前抱頭大哭起來。
次日,狀元派人飛馬傳書,把周澤從千里之外的周家莊接了來。周澤一見妻子的面就哭得死去活來,哭著哭著猛然想起妻子化去之前曾說過:“將來要團聚全仗古琴了。”連忙開啟琴套按著妻子說過的方法,把琴正調一遍,反調兩遍,靜靜心,然後選擇一支夫妻原先共同喜歡的曲子彈了起來。那悠揚的琴音彷彿射出千萬條水線凝結成一顆大水珠把女屍籠罩起來。
大約過了一柱香的功夫,曲子彈完了,奇蹟終於出現了。水裡的女人逐漸睜開了眼睛,接著慢慢從水中坐了起來,清水芙蓉般美麗的面容更勝從前,一家三口又是一次抱頭大哭,這一對由琴生愛,劫後餘生的夫妻終於在多年後再續前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