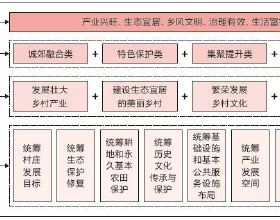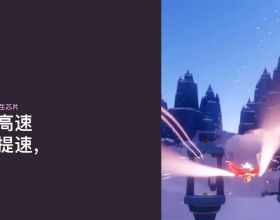有關兩個頭顱
文/馮積岐
在一個秋風漸緊的日子,大頭和小頭在縣城街道的大十字不期而遇。大頭從東向西走,小頭從西向東走;大頭高昂著他那大得有些過份的頭顱,對四周聚攏而來的好奇的目光不屑一顧,而小頭卻低下頭去,緊縮著脖子,顯然是在躲避眾人的目光。大頭老遠看見了小頭就老大老大地喊他。大頭問他家的老大,你怎麼也來了?小頭說,你不是也來了嗎?大頭說他是進城來買帽子的。小頭說他也是。小頭幾乎找遍了縣城裡的所有商店攤點,沒有一頂能和他的頭顱對上號的帽子。其實,大頭的遭遇和小頭一模一樣。小頭在他家的老二面前抱怨:一個縣城,咋賣的全是大號的帽子?大頭笑了:他說老大,不怪人家不賣合適的帽子,大概怪咱這個不合適。大頭在他的頭上摸著。小頭的眼睛左右一顧,也想伸手去頭頂上摸,他的手剛抬起來又疲軟地落下來了,他縮了縮脖子像是要把頭縮到腔子裡面去。
現在,大頭和小頭兄弟倆就站在縣城街道的大十字口商量著買帽子的事情。晚秋的風破麻袋片似的從大頭和小頭的頭頂上掠過,他們的頭頂上留下了梳子梳過般的絲絲涼意。大頭抬眼看了看被秋風掃蕩得有些生硬的天空,說老大,天涼了,好壞買一頂帽子算了。小頭垂下眼看著被人們踏起來的虛浮的塵土說,不合適,我就不買了。在街道上的喧囂聲中,大頭吊高嗓門和小頭說話,多餘的目光自然被這兄弟倆吸引過來了,小頭為他的頭顱而難為情,說話的語調儘量壓得很低很低。
小頭剛生下來的時候他的頭就小得和身材不能成正比。對此,小頭的娘並不悲觀,她給小頭的爹說,等娃長大了,頭也就跟著大了。女人將希望寄託在飽滿的時間上,時間催促著小頭長了個子長了臂膀,什麼都長了就是不見頭長。小頭到了五歲,頭顱好像剛從母胎裡帶出來那麼大,只是少了些血穢味兒。也就是在小頭五歲那年,大頭來到了人世間的同時用他那大得出奇的頭顱把懷了十個月的親孃一頭頂進了黃土之中。那是一個激烈而傲慢的夏天,晌午的太陽在屋外肆意作響;屋子裡,女人用疲憊而持久的呻吟渲染著難產的血腥,立生的大頭用雙腳蹬住了人世間,留在母體內的頭顱連同一個女人的生命在一起掙扎,接生婆操起一把老剪刀,咔嚓一聲,隨著女人的慘叫大頭掙脫了死亡,剪得慘不忍睹的陰道口化膿之後,敗血症順理成章地奪去了她的生命。大頭的爹捶胸頓足,抱起細聲啼哭的大頭要將他棄於荒野之中,接生婆口出善言:留他一條命吧,頭大有寶,這娃日後會大有出息的。大頭的爹像撂毛線團似的將大頭撂在了火熱的日子。
大頭進學校讀書的時候,小頭已經半路輟學了。小頭也是湊合著讀了兩年半書就將書包揹回來不再去學堂了。爹問小頭為啥不去讀書。小頭只是低聲細氣地哭著,一句話也不說。能認識幾個漢字的爹叫小頭把成績單拿來叫他看,他一看,小頭的學習成績並不差,就掂起一把老鱖頭將小頭向學校裡趕。小頭雙手護住他的頭跑出院門兩天沒有回家。如果說,小頭沒有再去讀書是他人生的災難和不幸,這災難和不幸是他自己造成的,也是我們大家一手造成的。從小頭踏進學校門檻的那天起,我們就為他的頭顱而驚詫,我們隨心所欲地嘲弄他輕視他;他坐在教室最後一排的角落裡,聽課的時候用雙手抱住頭,彷彿是為了給頭顱的四周增加一層厚度。下了課。他坐在教室裡不出門或者找地方呆站著。他的帽子四周襯著許多廢紙,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將小得可憐的頭顱固定在脖頸。他的學習成績的出色使我們都很嫉妒。終於有那麼一天,我們將小頭堵在廁所裡了,我們命令小頭脫下褲子,小頭不脫。我們幾個就齊上手硬是把他的褲子抹下來了。小頭要用手去捂他的那個東西,我們扭住了他的手,不叫他捂。
“你說你的頭大還是老二(那個東西)大?”小頭不說。
“你說不說?”有人要去摸他的那個東西。
“我說。”
“啥大?”
“老二大。
“哈哈!”
我們都開心地笑了。小頭哭了。小頭用雙手捂住他的頭顱。我們幾個就老二大老二大地喊叫。小頭在我們的喊叫聲中亂竄著,小頭從教室跑到院子裡,又從院子裡跑進教室,當他跑到一堆女學生那邊的時候,女學生們看著他的頭哧哧地笑了。小頭無處躲藏就鑽進了學校裡的小儲藏室,上了課,先生一點名,不見了小頭,就叫我們大家去找他。我們找到儲藏室,只見他雙手捂住頭,一隻狗似的蜷在角落裡顫抖著。
幾天以後,小頭就不來學校裡讀書了。
大頭來學校讀一年級的時候,我們幾個已開始讀五年級。我們都覺得大頭很好玩,也玩得動。大頭不像小頭那樣,他樂意叫我們玩。下了課,我們叫大頭來玩,大頭一叫就來了。我們說,大頭,叫我們摸摸你的頭。大頭說,你們摸,你們愛摸儘管去摸。大頭將頭伸過來,我們幾個輪流著在他的頭上摸。大頭頭頂的面積很寬闊,我們一摸,他不惱也不怒,只是嬉嬉地笑。於是,我們就在他的頭上用手拍,你拍一把,我拍一把,彷彿在拍一塊木頭。我們拍著問大頭疼不疼?大頭笑著說,不疼,舒服得很。
在一個十分溫和的日子,我們將大頭叫進了廁所。我們叫大頭脫褲子,大頭就順從地脫下了褲子。我們看看大頭的那個東西問大頭,你說你的頭大還是老二大?大頭說,你們說那個大就那個大。我們說,頭大。大頭說,你們說頭大就頭大。我們問大頭,你的頭咋那麼大?大頭說,是我爹給我用的料多。我們都笑了。我們問他,這話是誰說的。大頭說是東街的“講師”爺說的。講師爺不是大學裡的講師,講師是村裡人給他起的綽號。
下了課,我們故意不叫大頭和我們一塊兒站,我們命令他站在女學生那一邊去,大頭就搖晃著碩大的頭顱若無其事地向女學生那邊擠,女學生見他來了就躲。女學生們躲到哪兒他就攆到哪兒。女學生們哧哧地笑著,回過頭來噗兒噗兒地朝他唾唾沫,他毫不在乎,頂著一顆大頭晃來晃去。
大頭在一年級讀了兩年,在二年級讀了兩年還不能升級,爹就不叫他再讀書了。爹似乎覺得“頭大有寶”那句話不太靈,他不由嘆息:這娃的腦袋恐怕裝的不是寶,是一灘爛泥。
小頭要結婚了。小頭順著街道上的牆跟兒匆匆地向前走,街道上的女人們喊住了他。
“田家老大,你結婚的日子定在啥時候?”
“九月十六。”
“待客不待客?”
“待客。”
“你媳婦是哪裡人?”
“山裡的。”
“長的乖不乖?”
“不知道。”
小頭低眉垂眼地回答著女人們無休止的盤問。小頭結婚那天,滿院子裡似乎只是晃動著大頭的那顆頭顱,該是小頭倒茶敬酒的時候,小頭卻不見了蹤影,大頭就代替小頭應酬。新婚之夜,自然少不了鬧房的人。小頭躲著不見,鬧房的人只好去鬧新媳婦。我們當中一些和小頭年齡相仿的人就去和新媳婦親嘴摸奶子。大頭守在新房中,不叫我們和他的嫂嫂鬧。有人說很粗的話給新媳婦聽,甚至說出了我們小時候在廁所裡看小頭的老二的事,我們說出的毫不羞恥的話將新媳婦的臉羞得通紅。大頭一看有人鬧過了頭就罵我們,硬是將我們趕出了新房。等鬧房的人走後,小頭才回到了房間裡。小頭嗅了嗅,房間裡滿是山裡女子的氣味,他雙手抱住頭,愣怔地看著長明燈。
"你是不是頭痛?”新媳婦問他。
“不。”
“肚子餓了?”
“不。”
“你有啥病?”
“沒有,啥病也沒有。”
新媳婦畢竟是山裡的風吹大的,她野慣了,在她那個年齡上該做的事情她是知道的。因此,她很自然地向小頭跟前蹭。小頭不叫她蹭。新媳婦臉上有點熱,一熱就紅得不可收拾了。小頭偷眼一看新媳婦,說你把燈滅了吧。小頭躲進被窩裡,新媳婦偎過來一摸,他依然戴著帽子,新媳婦就去摘他的帽子,小頭去撥新媳婦的手,小頭說,你在哪裡摸都行,你不要在我的頭上摸。於是,新媳婦就在她想摸的地方去摸。小頭在新媳婦的撫摸中縮成了一團。
第二天,大頭走在街道上,街道上的女人們喊住了他。
“田老二,你嫂子乖不乖?”
“乖。”
“你想不想要個乖媳婦?”
“咋能不想?”
“過年就給你娶一個。”‘
大頭的手在頭上一拍,他說:“咱這東西長得不合格,誰看得上?”
女人們一聽,笑得前仰後合。她們說,男人的頭越大,女人越喜愛。她們說,頭大的男人那個大。她們說粗話就象張開嘴打呵欠一樣隨便,她們用粗話逗弄著大頭。大頭只是傻乎乎笑著。
生產隊裡推薦小頭到縣城裡去參加講用會,小頭不去。生產隊裡的幹部說小頭思想好,是活學活用的積極分子,一定要去的。小頭很為難,就去找大頭商量。大頭說,叫你去,你就去。小頭說叫他去縣城是丟人顯眼。大頭說,咋能是丟人?你去是你的光榮。小頭說,光榮?咱這模樣(指頭顱),還怕全縣人不知道?大頭說,咱的頭不標準也不算是瑕點,就算是個瑕點也不怪咱。你去是大家抬舉你。小頭說,我不去就是不去。大頭說,你不去,我就替你去。小頭說,你不嫌丟人就替我去。
大頭就自告奮勇地代替小頭去縣城裡參加講用會,他扮演的是小頭的角色。大頭一走上縣城裡的講臺,聽眾就在下面竊竊私語。站在講臺上的大頭向大家鞠了一躬,將面積額大的頭頂亮給了聽眾,他搖頭晃腦,講得眉飛色舞。他的講用和他那碩大無比的頭顱一起給人們留下了深劃的印象。
太頭和小頭第二次在縣城街道大十字相遇的時候,街道上的人稀朗得多了。大頭買了一頂華達呢帽子從北向南走來了,灰色的帽子頂在他的頭顱上,頭顱上如同臥著一隻可愛的灰色鳥兒。小頭也買了一項灰色華達呢帽子,他將帽子提在手裡從南向北走來了。
大頭說:“帽子買到了,老大?”
小頭說:“買了一頂。”
大頭說:“咱就是這頭了,好壞買一頂算了。”小頭說:“沒有合適的,走遍了四條街,就是沒有合適的。”
大頭說:“不是帽子不合適,是咱的頭不合適。"小頭說:“帽子太大了,不能戴。”
大頭說:“你戴上,我看能大多少?”小頭將提在手裡的帽子向頭上一按,帽子將他的眉毛和眼睛全裝進去了。大頭將小頭的帽子向後腦勺上掀了掀,他說不大不大。小頭說,半個臉都裝進去了,還說不大?小頭將帽子摘下來又提在了手裡。
兄弟倆,一個戴著帽子,一個提著帽子出了縣城。田野上浮動著殘秋的衰敗。大頭和小頭走到了村子外邊的雍河畔,雍河裡的秋水清冽而瘦弱,圓圓的石頭蹭出河面來供過河的人踩踏。大頭腳下一搓,身子歪了一下,頭頂上的帽子差一點掉進了河水中。小頭提著帽子走得很穩當。過了河,大頭將帽子使勁地向下按,帽子太小,頭太大,按是按不下去的。小頭自始至終將帽子死死地提在手裡,過了河,他一看,帽子上提出了一個手印兒,他拿舌頭在印漬上舔了舔,印漬還是沒有被舔去。
初冬的風是不饒人的。大頭戴著帽子去給麥地裡送糞,一路上,風將他的帽子摘去了好幾次,他不抱怨頭顱太大,也不抱怨帽子太小,他就想,無論如何要想個辦法,這樣來回拾帽子耽誤幹活兒。回到家,他叫女人用剪刀在帽簷上剪了幾個口子,這樣一來,帽子可以向下按去一點了,可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風一大,帽子還是戴不住的。 後來,他買了一條毛巾,用毛巾將帽子箍在了頭上,這樣做的結果,再惡的風也將帽摘不去了。
小頭先是給帽子四周墊上了紙,墊上紙也不行,帽子像車軸上的車輪子在風地裡轉動著,他只得用一隻手按住帽子。這樣一來,他只能用一隻手勞動,拉架子車還湊合著可以,向車裡裝糞時,一隻手就顯得不夠用。風將帽子一掠走,帽子中墊的黃草紙就隨風飄揚。一個晌午,他只拉了三回糞。回到家裡,他甩下帽子,看著帽子生氣。後來,他就學著他家老二的樣子,用毛巾箍住了帽子。帽子雖然固定住了,頭和身子比例卻很不相稱,因為帽子和毛巾的緣故。他想了辦法,叫他的女人將帽子四周用針線縫了許多縐折,帽子這才穩穩當當地固定在頭上了。只是頭頂的上半部圓鼓鼓地裝著空氣,看起來有點怪。
第二年暮春時節,大頭和小頭分別收到了表弟從蘭州寫來的信。表弟告訴兩位表兄,姨媽的病很重,想見一見大頭和小頭。大頭和小頭相約去了蘭州。
十天以後,他們回到了老家鳳山縣。走到村子外邊的雍河畔時,春汛從雍山裡漫下來了。雍河裡漲了大水,平日裡過人的浮橋離水面很低很低。還未過橋,大頭就給小頭說,這橋不太穩當了,你要小心點。果然,走到橋中心,小頭將一個朽了的木板踩掉了,他一顛簸,頭上的帽子就飛到水裡去了。小頭一驚,叫了一聲帽子,就撲進了河水中。水不太深,但很急,帽子隨著河水急速飄遊,小頭就攆著帽子而去。站在橋上的大頭放聲喊小頭。小頭為他的帽子還向下攆。站在橋上的大頭看見,小頭被一個漩渦漩了一下,水面上只浮著稀稀的頭髮,他什麼也不顧,一頭撲進水中去救小頭。
大頭一下去,頭上的帽子就被水拿掉了。小頭攆帽子,大頭攆小頭,兩個人一直被水捲到了下游的攔河水庫中。水面上只浮著兩頂灰色的華達呢帽子,大頭和小頭被捲進水庫裡去了。
我們去看被水淹死的大頭和小頭。兩個人的棺材都是黑顏色,都是一個樣式。村裡人不再叫他們大頭和小頭了,村裡人都說,田家的老大和老二死了。我們似乎才發現,大頭和小頭的頭顱在死後變得一樣大了,變得很合乎我們心中的標準了。人一死,什麼都一樣了,什麼都死了,大頭和小頭死了,帽子死了,只留著大小一樣的兩副棺材等著入土。
我們中的許多人只是默默地站在還未入殮的大頭和小頭面前,都覺得欠下了這兄弟倆什麼東西。他們的缺陷只不過在身體上,我們有什麼理由去作踐他們呢?我們一想到自己的缺陷當然就無話可說了。
原載1997年3期《牡丹》
岐山籍著名作家馮積岐出生於鳳鳴鎮陵頭村,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作家班,1983年開始發表小說,199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在《當代》《人民文學》《上海文學》《花城》等數十種報刊發表中短篇小說300多篇(部),作品多次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選刊選載,多次入選各種優秀作品選集。出版長篇小說《沉默的季節》《村子》《逃離》等14部,共出版各類文學作品40多部,近千萬字。作品曾多次獲獎。掛職擔任過中共鳳翔縣委副書記。曾任陝西省作家協會創作組組長,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