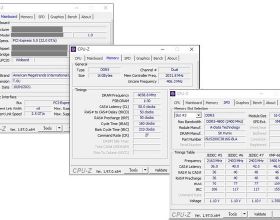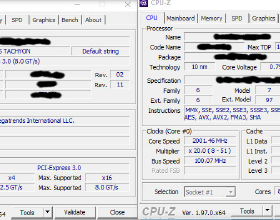天已過晌,德厚仍然弓著腰,在齊腰深的高粱地裡,用他那把磨得賊亮的大鋤鋤雜草。沒有一絲風,太陽在沒有云的有些發灰的天空中俯視著他。他早已禿頂,額頭和肩背一樣,曬得又黑又亮。汗珠從他的前額流到鼻頰,再流到下巴,再滴到乾巴巴的黃土地上。他直一下腰,口中罵道:這狗日的天氣!
老天並不在乎他的罵,依舊沒有一絲雲,和灼熱的大地相互幹烤著。
“長畛”果然有些長,他差不多鋤了半個小時,仍然沒有鋤到地頭。地頭有他的衣服,還有一條毛渠,毛渠裡還有今年春澆困剩的水。這時他無比相念起那些困水來。長畛,他太熟悉了。在他的記憶深處,還存著一個關於長畛、關於高粱地的秘密。
十八歲那年,因為他是家中老三,便被抽丁加入了閻錫三的九路軍——本地人稱為勾子軍。部隊還沒有開拔,就遭遇了掃蕩的日本軍。不用說,這支剛組建的農民性質的軍隊只能一路潰退,而還沒有來得及認識的兩個鄰村青年就被流彈打死了,連屍體都沒有人敢去找。睡在露營的乾草上,德厚滿眼是那兩個死人中彈時一抽一抽的樣子,不由渾身篩起糠來。部隊還沒有發槍,每人只配給了兩顆手擲彈。德厚摸著手擲彈,想著耳邊呼呼飛過的子彈的聲音,一陣陣尿急。他摸黑爬起來,踅到人群以外,撒尿。突然背後傳來哨兵的聲音:口令?他有些迷糊,口令是什麼來著?高粱?一下子竟回答不上來了。只聽哨兵又喊:再不回答開槍了。德厚突然明白過來,一邊繫腰帶一邊朝老家的方向狂奔起來。隱隱約約,後面也有雜亂的聲音尾隨而來。德厚拼了命的跑,一口氣跑到了這塊長畛的高粱地。聽得地塄上的追兵仍在不停叫喊,不知那兒來的勇氣,他甩出了一顆手擲彈。“轟”一聲,炸了。又聽追兵們停了腳步,大罵一通,才走了。德厚爬在高粱地裡,一動不敢動,大氣不敢出。直到確信他們走遠了,才慌不擇路地逃到了鄰村的姐姐家躲兵。
這塊高粱地曾經救過我的命,他想。
終於鋤到了盡頭。撥開草叢,他伏下身去,吹了吹困水上面的漂浮物,“呱唧呱唧”作標準驢飲狀,喝起了還在遊著小蝌蚪的水,十分過癮的樣子。喝足了,從衣服口袋裡摸出已經壓扁的那盒“公主”牌香菸,大口大口地吸起來。他篤信老人們講的“不乾不淨,吃了沒病”的話,雖然快七十了,也絕少吃藥,感覺自己就是鐵打的。去年老伴走了,雖然飢一頓飽一頓,愣是沒有犯什麼病。
正胡思亂想著,見地頭的樹蔭下正站著一個漢子,向他問話:“忙呀?”講的是普通話,白淨面皮,穿戴整整齊齊,腰帶上還彆著一把手機,一看就是個有工作的人。
“瞎忙咧。”德厚有些讒媚地看了看他。
那人見他搭話,竟有些喜出望外,支好腳踏車,亦步亦趨地從剛硬化過的村通公路的對側橫過來:來來來,老師傅,抽我一顆煙。隨手開出一支大紅盒的“國賓”煙來。
德厚知道他抽的是好煙,有些小激動,兩個人拉起話來。
原來,他是雲南人,說是在本縣山裡的煤礦上班。看到此地比他們老家富裕,就想把他妹子嫁到這裡,讓好一輩子過好日子。今天休息,所以騎車出來轉悠,看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家。
合適的人家?我家就再合適不過了,德厚心想。
德厚家在村裡可算得上有名。有名的原因不是有才,也不是有財,是因為他家有人。全家六口人,一共六個光棍漢。大兒子四十多了,腿殘;二兒子快四十了,智殘;三、四、五類似,村人喚作“不足秤”。春節時候的春聯最是有趣,麻老先生給編的,道是:鐵老元帥居中排程,五虎上將各把潼關。引得村人紛紛來看,成為美談。
天大的好事一下子砸中了德厚,著實讓他有些喜出望外。
德厚領著這個算是媒人的客人興致勃勃地回了家,到二寶家的鋪鋪裡牛肉豬肉好煙好酒的一通亂買。二寶覺得奇怪,問德厚是不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德厚臉漲得通紅,只一個勁兒的說:有好事了,有好事了。
也怪了,這客人見德厚家有五間大瓦房,雖然冷鍋冷灶的,家裡也很不衛生,竟然沒有一絲絲嫌棄,只是說:人就是財富,有人就會發展起來。還沒見未來的妹夫,倒像是已經中意了似的。德厚除了過年,平時從來舍不喝酒,今天卻和客人喝了個痛快。挨個兒把兒子們的年齡報了一遍,看人家願意哪一個。這客人喝著酒,口也沒閒著,說就老二吧,年齡接近些,他妹子也三十多了。這正好暗合了德厚的心思——老二的腦子最差,而且還吃不得苦。如果把老二的事解決了,其他的就相對好辦了。
好事快辦。隔了一天,那客人便把他妹子領了來。一身好打扮,長得那叫個俊。街坊鄰居知道了,三三兩兩的結群來看,都說全村也沒有一個這麼俊的姑娘,德厚家是託了十八輩子的福,時來運轉了。那姑娘也不打生,用一口大家聽來十分標準的普通話,挨個兒和大家打招呼,落落大方的樣子。不用說,德厚家所有人都是一百個願意。沒承想,姑娘的哥哥提出了一個難題。
“我妹子倒是願意,可是……”“
你說吧,只要能辦到的,什麼條件我家都答應。”
“我們老家窮,所以彩禮得高一些。”
“多少?”
“最少八千吧。”
德厚知道本地彩禮錢的行情是一千六,翻蓋這五間瓦房才花了不到八千,八千的彩禮錢對於土裡刨食的他,確實有些兒高。所以表面上坐在那裡不吭聲,實際上好久沒有用的腦子卻飛快地轉了起來。家裡六個勞力,口糧地和承包地一共種著十五畝,一年收入兩千多。除了供父子們吃飯抽菸,每年只剩一千多。現在存款有四千,差距有點兒大了呀。於是,他一邊撓頭皮,一邊想怎麼回答。忽然靈光一閃,想到一個理由,於是說道:“俺們這裡講究個順,六六大順,我看就六千吧。”
那姑娘的哥哥好像很為難的樣子,勉勉強強答應了。
喜慶的日子到了。德厚家四十年沒有慶典的院子熱鬧起來。鐵炮、鞭炮、二響炮響了個不亦樂乎。場面雖然比不上別人家宏大,卻用炮聲壯了不少聲威。
老二早早起來,滿臉紅光地上街。不安好心的小青年們問:“老二,夜來黑間和你老婆做那個來沒啦?”
“沒啦。她胸脯上還戴個鐵殼殼咧,不讓俺摸。”
大家鬨笑著散了。
院子裡,那雲南媳婦正一臉媚笑地和德厚說著話。說是她做茶打飯都沒問題,可是老家是山區,就沒有學會個騎腳踏車。德厚看著兒媳,越看越順眼。說是新車子給買下,不會騎可不行,要不就我教你吧。
三天了,新媳婦真笨,一跨上腳踏車就倒,逗得老德厚哈哈大笑。說乾脆到村外新開的“村村通”公路上騎吧,水泥的,不容易摔跤。
於是,翁媳二人推車到了公路上。
老德厚好有耐心,剛開始是扶著衣架教,到後來就偷偷放開了手:“你不要看輪子,要看前面,用勁兒蹬……”
卻見那雲南媳婦果然抬起頭來,一邊口中唸叨著什麼,一邊往前猛騎,直至沒有了蹤影。對著她的背影,德厚看呆了:一直想,她不是不會騎車的嗎?
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