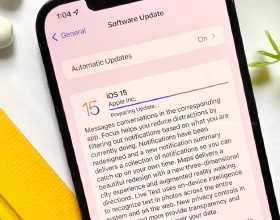五年多了。
整整五年多。
五年,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也許算不了什麼。
起床,吃飯,工作,睡覺。
日子無非週而復始,像是一直往前,其實就是不停地迴圈。
這樣迴圈著迴圈著,五年一個樣,十年還是一個樣。
全都可以不緊不慢、不知不覺地過去。
可這五年多,對王保平不一樣。
五年多來,他沒有一天不提心吊膽,沒有一天不夢見自己被抓起來。
這日子,真不是人過的日子。
終於,他下定決心,結束這一切。
坦坦蕩蕩地結束這一切。
一、歸程
本來王保平要坐大巴走的。
直到去了車站,他才改了主意。
售票員是個五十來歲的婦女,臉板著,像是一塊拒絕融化的冰。
“坐車要身份證嗎?”
王保平這樣問了一聲。
女售票員的聲音和她的臉一樣,都是冷冷的:
要!如果你是外逃的貪官怎麼辦?上車不查半道也要查!
多稀奇,坐大巴也要身份證了。
可是,只要他一拿出身份證,怕是就立刻有人把他請走吧?
五年多來,他的名字,早就在世間最不該掛號的地方掛著號吧?
他說自己叫王保平,可是身份證一拿出來,他說自己叫什麼有用嗎?
身份證不會騙人,如同他自己的心騙不了自己。
他哪裡姓什麼王,他真正的姓,身份證上可都寫得明明白白呢。
看來坐車這條路行不通。
別管坐什麼,都行不通。
大巴不行,火車更不行。
至於飛機,想都不用想。
可是從他現在的地方返回老家,全程整整三百六十公里。
這三百六十公里,指望兩條腿,猴年馬月能走得完?
保平決定買一輛腳踏車。
沒錯,就是腳踏車。
如果連買這玩意也要身份證,那他直接找塊豆腐撞上去算了。
當然誰都知道,買腳踏車和身份證沒有半毛錢的關係。
跨上車的那一瞬,保平突然有種強烈的錯覺。
時光突然就倒流回過去,倒流回他還是學生的那個點。
騎上車,他就是學生。
再過幾天即將面臨高考的學生。
二、禍起
王保平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學校裡有位姓姬的地理老師。
姬老師總是埋怨生錯了年代,說要是生在古代,就可以光明正大地遊山玩水。
看看滕王閣、岳陽樓、小石潭以及三月的揚州和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渭城,不玩兒,這些怎麼寫?
姬老師還說,人一輩子要有所寄,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就是這寄的區別。
寄情山水,比寄情金錢權力強一億倍。
就是這位姬老師,別看上課時天南地北到處吹——人家教地理課,可不就得天南地北到處吹——課上得真是好。
怎麼好呢,這麼說吧,逢到他上課的時候,學生就跟過節似的。
姬老師不僅課上得好,車也騎得好,可以把前輪一抬,只後輪著地。
這還不算,還能在腳踏車僅一輪著地的情況下,拐來拐去,做各種花式動作。
真要說像什麼,那就像馬戲團表演差不多吧。
可就是這位課上得好車又騎得好的姬老師,有一天晚上騎車從學校回家,卻連人帶車被一輛汽車撞飛了。
送進醫院的時候,很奇怪,人好好的,全身上下沒有一處地方流血。
值班醫生看了看,說沒事,開了消炎藥,說第二天再檢查。
當天夜裡姬老師就肚子疼到不行,還是那位值班醫生過來看了看,說沒關係,只是肌肉痙攣。
熬到第二天,哦,不,是沒有熬過第二天,原本好好的姬老師,就沒了。
原來他是內臟被撞到大出血,可是值班醫生竟然一次次忽略了這一點。
就是那個值班醫生,保平後來打了他,打到滿地都是血。
以為對方不行了,保平倉皇逃離。
沒錯,保平不姓王,他姓姬。
那位姬老師,那位課上得好車也騎得好的姬老師,那位課上得好車也騎得好卻依然沒熬過第二天的姬老師,是他爸爸。
尾聲
林那北的作品《前面是五鳳派出所》,核心事件是一起醫療糾紛。
主人公姬保平因為值班醫生的疏忽,導致爸爸離世而憤怒不已,起而狂揍了醫生。
出了人命,這位值班醫生因為理虧,也因為沒有料到只是中學生的保平會和他動手,竟然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滿地流血。
作品中沒有清楚交待值班老師的後續如何,但就算這位醫生活著,姬保平也難逃刑事責任。
這本是一場可以避免的悲劇。
拋開討論不斷的醫患關係不說,單就姬保平而言,他的憤怒我們相當能理解,年少氣盛,再加上親愛的爸爸突然離去,一時失去理智,似乎也很容易能說得通。
姬保平最終選擇自首,在最初的驚惶和悲傷過去之後,他終於跨越自己最艱難的一步。
五鳳派出所,就在前面。
姬保平一路單騎,終於走進去,從此天寬地寬。
世界是公平的嗎?
世界的公平正在於那些相信它公平並願意守護這公平的人,哪怕為此付上該付的代價,也在所不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