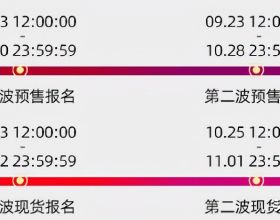提到換親這種操作,可能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漢武帝劉徹和大將軍衛青,劉徹的姐姐平陽公主三婚嫁給了衛青,雖然是三婚,可人家好歹還是下嫁,談不上辱沒衛青,劉徹娶了衛青的姐姐衛子夫為皇后,這樣下來,劉徹和衛青兩家就相當於換親,兩人互為對方的姐夫。
這種充滿佳話的古人軼事,因為涉及到了帝王將相而變得富有傳奇色彩,然而今天筆者帶給大家的是來自尋常百姓家的一段換親故事。
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們掙脫了十年浩劫的束縛,開始對外張開懷抱,擁抱一切新鮮空氣和溫暖陽光。那個時代既有佳麗柔情萬種的愛情故事,也有俠客仗劍天涯幹氣雲霄的江湖傳說。然而這些浪漫的東東對於尚處於貧瘠狀態的河南農村大地來說,似乎還是那麼遙不可及,人們還住著一下雨就擔憂屋頂會漏水的土坯房甚至茅草房,只有個別土豪才住得起磚瓦房,較為普遍的交通工具還停留在馬車、騾車或者架子車階段。
那個時候河南窮啊,豫東平原的農村更窮,按理說豫東平原位於三川交匯之處,一馬平川,土地肥沃,年年風調雨順,應該五穀豐登才是,可問題是風調雨順是有的,五穀豐登卻扯不上邊。
豫東平原某縣東南角15公里處有一個村莊,叫王家窪,以村名來看,這個村莊應該以王姓居多,其實該村是以王、李兩姓為主,聚落呈散狀乃牙形分佈,平原雖然寬闊,但交通閉塞,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是當時該村的真實寫照。80年代初期,村裡是窮得叮噹響,有句話形容得是十分貼切,“寧啃鹹菜渣,不嫁王家窪”,可見王家窪有多麼的貧窮不堪。
王家窪村南邊有一戶人家,戶主叫王文林,娶妻婁氏,膝下有三男三女,在之前鼓勵生育的年代,王文林有三男三女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當時人就是這樣奇怪,明明已經很窮了,卻要拼命地生,即便不鼓勵生育,但為了家族興旺也是拼了。王文林不懂其他營生也沒什麼手藝,再說在包產到戶之前,還沒有分地,和妻子婁氏一起掙著工分,含辛茹苦吃著大鍋飯硬是把六個孩子給拉扯大。好在婁氏也是個勤快的女人,在閒的時候去地裡拾點兒糧食,與其說拾,不如說是偷,那些年月實在是沒辦法才出此下策,人總是會想著活下來,日子雖然窮得叮噹響,飢一頓飽一頓的,孩子們總算是一個不落全活下來了。
轉眼間,王文林的大兒子王天喜就到了適婚的年齡,要娶媳婦兒了,這可愁懷了王文林兩口子,王文林他們靠著那點工分起早貪黑勞碌了半輩子,生活異常艱難地養大了兒女們,但談到娶媳婦兒,那可真的是一籌莫展,結婚所需彩禮的三大件:洋車、手錶、縫紉機,那是一樣也買不起,再說平日裡為了天喜兄妹幾個,也沒少欠親戚鄰居們的帳,他這個舅家的、那個姑家的,再說那年頭誰家都不富裕,在給王文林兒子娶親這件事上面,大家都是有心無力,能幫的只能是嘴忙,其他的委實愛莫能助。
經濟情況固然是一方面,可問題是王天喜是個駝背,也可能是之前生活勞累的緣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家裡姊妹多,沒上完小學就要幫著王文林夫婦掙工分,撿柴火,撿糞什麼的,積年累月的勞作使天喜看起來駝背比較明顯,當然也可能是天生的,總之是又窮又駝,再加上面相顯老,二十多歲的小夥子,愣是看起來像四十,這形象相親實在拿不出手。
可老王家又偏偏有以長子為先的傳統,當哥哥的不帶頭結婚,弟弟妹妹們不能搶了先,眼看兒子都二十五了,再不娶媳婦兒可能真的就過了槓了。二十五歲對於現在來說那還是一懵懂少年,但要著眼於當時的時代背景,於是王文林就託村裡有名的張媒婆給說媒提親。張媒婆生就的一張畫眉嘴,在那個年月成就了不少良緣美眷,當然也養活了她自己。
其實王天喜倒也不是一無是處,為人本分老實,街坊鄰居誰家有出力的活,一喊天喜準沒錯。而且為人豪爽,自己只要有口吃的,只要別人張張嘴,那肯定能夠分上半口。
玉花是王文林的二女兒,年方十八,如出水芙蓉,情竇初開的她等來了一場美麗的邂逅。她和鄰縣一家豫劇團的後生一見鍾情,一個溫文爾雅,一個貌美如花,郎才女貌,真是天造地設的一雙。倆人很快墜入愛河,如膠似漆,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愛情使玉花渾身散發著青春的活力。
滿面春風的張媒婆急匆匆地向王文林家奔去,大老遠看見婁氏就喊:“他嬸兒,喜事呀,喜事!”婁氏頓時一愣,“喜事?莫非是她給俺家天喜找到媳婦了?”就趕快把張媒婆讓進堂屋,讓其坐上座,拿出了炸豆根兒(一種類似麻花的食品,但上面飄著糖粉,逢年過節才捨得吃),沏好紅糖茶。張媒婆喝了口糖水氣喘吁吁地說:“他嬸兒,給天喜找著媳婦了。是離咱這五里多地的趙莊,女孩二十歲,我給人一說咱家天喜的條件,當然了我是費盡了唾沫星子,盡往好哩說,人家說只要踏實能幹,能賺錢就行,別的啥都不圖,你說,這好家哪找呀!”婁氏聽得心花怒放,兒子終於能娶上媳婦了,總算是日子有了盼頭。
隨後婁氏神情轉為憂傷地說:“女方的長相好孬咱都不挑,人家要多少彩禮,咱砸鍋賣鐵也湊齊了給!”“彩禮人家倒是沒要”,張媒婆頓了頓露出了難言之隱,婁氏說:“他大娘,你是俺家的大恩人,救苦救難的活菩薩,有啥話儘管說。”張媒婆嚅囁地說:“趙莊那家也有一個和咱天喜條件差不多的兒子,那家的意思是……意思就是換親。讓咱玉花嫁過去,把他家閨女嫁過來。”聽完張媒婆的話,婁氏陷入了沉思,久久不能平靜。
婁氏心想,其實換親這種事,按理說也不是什麼吃虧的事兒,既解決了雙方兒女的大問題,還親上加親,關鍵還不用操心彩禮,想通了這點兒,婁氏心裡漸漸豁然開朗起來,但問題是她那大閨女玉花正相好著那個豫劇團的後生,半個村子的人都知道,如果沒有出現換親這一提議,倒也是美事一樁,那個年代唱豫劇的吃香著呢,在河南人心目中,凡是和豫劇沾了邊,不管是拉弦的,還是敲鑼打鼓地位都堪比吃公家飯,這要是玉花和那唱戲的成了,全家人臉上都有光。
她要把這事兒說給了玉花,玉花指定死活不同意,她正處於熱戀當中,又因為那位唱戲的行當,潛移默化接觸了不少戲裡的愛情故事,什麼《大祭樁》、《春秋配》、《風雪配》之類的,愛情的意志愈加堅定,張媒婆也是知道這一層,可沒辦法,媒婆的本職還是促使她勸了勸婁氏:“她嬸兒,我知道,你不捨得,玉花這妮兒能遇上這緣分,可這……也沒姑娘願意嫁給咱天喜呀,你再想想,其實咱也不吃虧。”臉色蒼白的婁氏有氣無力地說:“他大娘,讓你費心了,我想想,好好想想。””
冬季鄉村的夜晚來得很早,寒冷和黑暗籠罩下的村莊格外寂靜。搖曳的煤油燈光映照出婁氏蒼白的臉,王文林坐在床邊不說話,吧唧吧唧地抽著旱菸袋,婁氏先開了腔:“老頭子,你也別光顧著搗鼓你那菸袋子。你也說說該怎麼辦呢,不換,咱家天喜娶不上媳婦;換,毀了玉花一生的幸福。你倒是給我出出主意呀。”說著說著,往日生活的苦楚歷歷在目,不禁失聲痛苦,婁氏越哭越悲慟,呼嘯的北風裹挾著哭聲,將這份靜謐揉得粉碎。
玉花讓永安帶去學唱戲了,永安就是那個豫劇團的相好的,原以為故事講不到他,還是寫上名字吧,順便逛了下縣城,以前都是穿舊衣服,現在戀愛了,哪能還穿舊的,得買一身新衣服。於是永安就帶著她買了身新衣服。
哼著豫劇的玉花穿著新買的帶花粉紅的鴨絨襖走進院子,“媽,這衣服好看嗎?”本來就白裡透紅的臉在粉紅色的映襯下,更加白皙、姣美。“好看。”婁氏興味索然地說。沉浸在喜悅中的她完全沒有注意到母親的反常。婁氏頓了頓,鼓足勇氣:“玉花,來,媽給你說件事。”
“啥事,你說吧。”
“你張大娘昨兒來了。”
“給哥找到媳婦了?”
“媽這是好事呀,你眼咋腫了?”
“是,是給你哥找到媳婦了,但是花兒,你哥娶那閨女,你必須嫁過去,這是人家的條件。”
“媽,我不嫁,我和安說好了,過完年,我們就結婚。”
“花兒,媽也沒辦法,你不嫁,你哥就娶不上媳婦,就要打光棍了!”
“那也不能把我推出去,這個是一輩子的大事,反正我不嫁,我倆情投意合,是自由戀愛,誰也別想把我們分開。”
“啥自由戀愛,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還輪不到你當家。”
“為了你哥,為了我們王家,你不嫁也得嫁。”
在那個重男輕女的時代和地方,相對於兒子的終身大事,女兒的幸福顯得無足輕重,閨女嫁誰不是嫁,加上那幾天張媒婆也是在婁氏的耳邊不斷吹風洗腦,婁氏更加硬起了心腸,她得為老王家著想,閨女嫁給別人就是親戚了。
張媒婆是這樣說的:玉花和那娃成不了,人家是外縣的,玉花嫁過去受氣,孃家人也照看不到,又是唱戲的,免不了到時候學陳世美,來個始亂終棄什麼的,人家到時候又是縣城的還好找物件,可我們玉花咋辦云云。
那個時候離婚還是羞於啟齒的話題,張媒婆雖然沒說得很徹底,但婁氏心裡也著實咯噔了一下,她大娘話糙理不糙。
婁氏也把這番言語,七七八八雲山霧罩地說給了玉花聽,可被愛情佔據整個心靈的玉花,聽不進去半句,母女兩個你尋思我覓活鬧了個不可開交。
婁氏作式要跳井,玉花依樣要喝藥,娘倆冷戰了好幾天。
最後玉花做出了一個讓全家人都氣憤不已的決定:離家出走。這個決定主導了她未來幾十年和家人的和睦關係。
“反正我不嫁!”玉花逃離了這個讓她傷心絕望的地方,婁氏如一根木樁戳在院中。
本來天喜娶妻這場戲,正在緊鑼密鼓地上演著,關鍵時候演員罷演了,人家趙莊那邊渾然不覺,依然和媒婆繼續交涉著,直到紙包不住火了,趙莊的開出的條件依然斬釘截鐵。不然就要考慮其他相親物件,王文林和婁氏是又急又氣,卻又無計可施。
咱們再說說趙莊這邊,趙莊離王家窪不到5里路,是王家窪東北角的一個小村莊,人口相對比較少,要和王文林家換親的是趙四輩兒家,趙四輩兒原來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聽說大兒子早年去了黃埔軍校,當然這是鄉下人的說法,也許只是去了廣州讀書,當時的資訊比較閉塞,鄉民們以訛傳訛也說不定,後來回來之後抑鬱上吊自殺了,死因成謎,這樣趙四輩兒所能指望的只有二兒子趙輝和閨女趙桂枝了。
趙輝人長相方面倒是沒什麼,關鍵是犯羊羔風,發作起來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牙關緊閉、時而發呆時而傻笑,這情形怪嚇人的,像是鬼神附體了一樣,趙四輩兒和媳婦找來了不少赤腳醫生和偏方均不見效,當然也找了巫醫神婆之類的來幫他驅魂,也都沒什麼卵用,據說是家族遺傳病,趙輝的哥哥的死是不是與這個有關,已經無法考證也無人考證了,老大沒了,老二趙輝又這副樣子,還有輝他娘又是一副病秧子,誰家的閨女還願意嫁過來啊,眼看著兒子都二十三了,趙四輩兒是一籌莫展。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趙四輩家的閨女趙花枝倒是一枝獨秀,聽聽這名兒,花枝花枝,真有點花枝招展的感覺,身材高挑,面板白皙,尤其是那雙丹鳳眼,讓男人們看了,自有一種無法抗拒的魅惑之力。
論趙花枝這條件,有模有樣,那就是以後要嫁個好人家,至少是吃公家飯的,當然花枝自己也想當然地這麼認為。
可畢竟趙四輩兒是這個家的家長,他更多地考慮的是兒子趙輝的婚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至於如果花枝嫁得好,那是錦上添花的事情,現在擺在趙家面前的是需要續上香火,是需要雪中送炭的。
於是乎有熱心之人就建議了,你家不是有花枝嗎,用她給輝兒換親不是很好的事情嗎?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趙四輩兒一想也是,輝兒他娘常年疾病纏身,自顧不暇,兒女大事只能靠他一個人來操持了。
透過張媒婆的牽線搭橋,趙家和王家這兩家本來不沾親不帶故的就被聯絡了起來,雙方的兒子都有毛病,大家半斤對八兩,誰也別嫌誰,就是委屈了各自的閨女,玉花是不樂意,人家花枝同樣也是一百個不樂意,但花枝不像玉花那樣反抗激烈,面對自己家的爛包家庭,她有些麻木了,哥哥死了,娘病了,弟弟也是時好時壞,只剩下老爹和自己這兩個囫圇人,如果自己反抗太過,尋死覓活的,老爹趙四輩再有個三長兩短,這個家也就隨之散了。
至於花枝和玉花誰漂亮,這個可能也是半斤對八兩,各有千秋,“梅須遜雪三分白,
雪卻輸梅一段香。”這麼形容吧,可問題是玉花逃跑了,這事兒不就沒下文了嗎?倒也不至於,前文咱說到,王文林有三個女兒,玉花是二女兒,大女兒玉蘭已經出嫁兩年了,嫁的同村李姓人家,小孩都一歲多了,三女兒玉紅倒也算得是一個選項,但年齡差著歲數呢,還不到16歲,而且面黃肌瘦、營養不良,樣貌看起來小孩似的,尤其冬天為了避寒把雙手插進了袖筒裡,看起來無精打采的,像霜打了的茄子。
眼看換親這事就算黃了,張媒婆再次開了腔:“”玉花一時半會找不回來,玉蘭已經有了人家,現在只能退而求其次了,玉紅年齡雖然小了點兒,可也就再過兩年的事兒,現在村裡她這個年齡的不都開始說媒定親了嗎?不如讓玉紅來代替姐姐吧,好歹還是一家人。”
和趙四輩兒一說,趙四輩兒沉默了一下,玉花玉紅都是玉,玉紅就玉紅吧,輝雖然還是期望玉蘭能夠回來,在家人親戚鄰居的聯合勸說下,輝也沒再堅持什麼,就一心等著娶媳婦了。
再說玉紅,年齡雖小,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恨嫁女,家裡窮,看不到希望,她從小就盼著早點嫁出去,至於什麼樣的人家,她也沒考慮過,總之只要和現在的家不一樣,她拔腿就走,至於什麼風花雪月類的愛情故事,那都是天書裡的東西,她似乎只知道二月二老鼠上燈臺嫁閨女,好盼望自己也早點嫁出去。
這麼一來,玉紅竟然成了最佛系的閨女,無公害免催婚達人,婁氏和她一說,她只是很平靜地問了句:“什麼時候?”把她媽婁氏都驚得張大了嘴巴,好一會才合上,繼而轉為心花怒放。
花枝這邊呢,雖然心下很反感很牴觸,但並沒有表現出太過激烈的情緒。那就意味著花枝也終於答應換親了。
換親不同於其他成親。有說不完的規矩,比如雙方的嫁妝完全一樣,出門同時。結婚證要四個人約好在結婚這天一起去領。雙方的迎親隊伍行走的速度都必須一致,大家都擔心對方反悔。那真的不是什麼喜事,只是一場交換。等到兩個新娘都娶回家了,婚禮也要同時舉行,當年鄉村還沒有電話,也不知道是怎樣統一起來的。但王家和趙家這兩對兒卻沒那麼講究,又都是窮人,彩禮免了,嫁妝也都商定不用來回拉,只是兩對新人舉行個儀式兒,這事兒也就算禮成了。
按村裡的風俗,閨女出嫁上轎之前要吃滿滿的一碗上轎飯,母親和閨女都要哭嫁。花枝她媽倒是哭得很傷心,不知道是捨不得女兒還是自己病情使然,花枝沒有流下一滴眼淚,甚至之後都沒見她哭過,只是恨恨的說了句:“這次我會讓你們滿意的”,似乎話中有話,人們都沉浸在喜悅中,沒人細細品味話中的含義。
玉紅倒是很平靜,不喜不悲的舉行完了儀式,彷彿那天不是她的婚禮,只是例行的一次太陽從東邊升起而已,然後她就悄無聲息和她的羊角風丈夫生活在了一起。不得不說,玉紅是挺旺夫的,她嫁過去之後,一天趙輝犯病,沒來由的痴痴傻笑,玉紅叫他,他不理,玉紅就上去搗了他一拳,這一拳頭搗過去不要緊,趙輝竟然奇蹟般清醒了過來,之後就再也沒有病發過,當然旺夫僅限於此,兩口子其實也並沒有大富大貴。
其實從花枝第一眼看到王天喜,就一臉的嫌棄和鄙夷,甚至於厭惡,和她期望的俊公子形象差了十萬八千里,尤其是看到他弓腰駝背的樣子,更是如同吃了蒼蠅般噁心,很難想象她將要和這個駝背一起生活一輩子。
花枝嫁過來那天,眼前的一幕讓她很是黯然,王天喜的房子是三間一層的土坯房,底座倒是有些舊青磚,因為時間久顯得斑駁而粗糙,大部分由土坯壘砌而成,牆皮已經開始脫落,窗欞和屋門是木製的,發黑發舊,倒是屋頂的瓦看起來還算有點房子的味道,
當鬧洞房的眾人陸續散去,花枝雖然既不期待又極度不情願把自己交出去,但並沒有哭也沒有鬧,王天喜雖然老實巴交,但碰上洞房花燭這種他人生第一件男女之事,倒也沒退縮,大著膽子爬上了花枝的身子,很不熟練的草草掠奪了花枝的初夜,然後便自顧自呼呼大睡起來。
但花枝暗地裡內心卻充滿了憤恨,她恨家人,恨老公,恨老公的家人,恨這個時代,恨自己的命運,甚至如果有可能,寧願她們之間不產生生命,當然和她被換親一樣,這又是她的一廂情願。她在心裡打定了主意,親她是換了,嫁也嫁了,娃也幫王家生,但她不遵守世俗婦道那一套,孝順公公婆婆?那是不可能的,是他們改變了她的命運,她本來可以嫁得很好,穿鳳冠帶霞帔也不是沒有可能,所以她對待王文林夫婦那是相當不好,基本上很少交流,很冷漠。後來家裡分了責任田,她也從來不下地幹活,東家逛西家玩,天天沒個正形。
幾十年來,都是王天喜一個人在操持著整個家,花枝從來不管不問,彷彿這個家不是她自己的,給王天喜倒是生了三個娃,2個女兒1個兒子,當然因為計劃生育也曾流產過,孩子們的教育她從來不管,在別人家的孩子都在上學堂的時候,她三個孩子全部輟學。
花枝有自己的生活法則,那就是到處沾花惹草,女人用這個詞不知道是否貼切,也許水性楊花更合適些,村裡的李屠夫李強是她勾引的第一個男人,李強是個瘸子,天生的跛腳,早年不知道跟著哪個殺豬匠學會了殺豬宰羊,日子過得雖然不盡如人意,但他天天有肉吃,他比王天喜要小上5-6歲,是家裡的老三,家裡老人給他兩個哥哥分別娶了媳婦,實在無力在幫他找物件,再說也很難找,他也渴望愛情,相信愛情,有人安慰他,天涯何處無芳草,妙齡少女多的是,讓他別灰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一邊殺豬,一邊等待著天涯的芳草,芳草他沒有等到,他等來了花枝,花枝好饞想吃肉,在那個白麵饅頭都啃不上的年代,豬肉的香味對於花枝有著不小的誘惑力。於是花枝想拿自己的身體和李強換肉吃,兩個人就這樣達成了不成文的交換協議:你吃我的,我也吃你的。從未沾過女人的李強如同久旱逢甘霖,一發不可收拾,不但給花枝肉吃,還送錢給花枝,鄰居們當時都私下議論,說花枝有兩個老漢。花枝也從不辯解,依然我行我素。花枝和李強不但在李強的住處行風雨翻滾之事,還把李強帶回家來。
王天喜後來也知道了這事,可他不敢和花枝鬧,換親之事本身他就愧疚,很怕花枝撇下三個娃娃離開這個家,但他畢竟是男人,也有男人的尊嚴,所以眼不見心不煩,他就常年出外打工了。
撕去了那層遮羞布,花枝開始變得肆無忌憚起來,李強是常客,她後來又勾引了村裡的其他男人,無論是鰥夫、光棍還是媳婦不在家的漢子,她照單全收,當然,她也換來了男人們的投桃報李,在物質匱乏的年代,很少見過她家斷過肉吃,她不但自己吃,也分給鄰居們。這樣嚼她舌根子的人們似乎少了許多。
幾十年過去了,花枝老了,姿色漸衰,但依然不改年輕時候的楊花之性,依然會有老男人光顧,經常有人見到她帶著大金鍊子招搖過市,那種環顧四周的自豪感優越感竟然一直都在。
她的子女由於花枝的玩世不恭,也近朱者赤,大女兒12-3歲的時候就和外縣的一個老男人相好生下了孩子,後來奉子成婚外嫁他鄉,小女兒輟學之後也是年紀不大就開啟了早戀,有過好幾個男朋友,後來在東莞打工時認識了一個工廠老闆,打了胎之後沒了生育能力被人拋棄,後來二婚嫁給了鄰村帶著兩個兒子的一個離婚男人,給人當起了後孃。最小的是兒子小三兒,也是天生的跛腳,而且智商不高,小的時候就經常被人稱作傻子,至於這孩子和李強有沒有關係,只有花枝知道,可能李強也不知道。因為花枝有太多男人了。
好在花枝的兒子小三兒最後娶上了媳婦,一個同樣智障的傻丫頭,嘰裡咕嚕竟然給小三兒生了三個兒子。
畫外音:這幾十年來,花枝和玉花、玉紅幾乎是老死不相往來 本來親上加親卻形同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