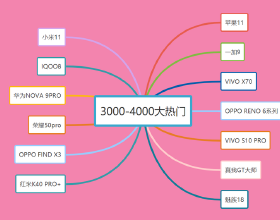村裡的老人有好些個,八十多歲了,小腳。拄著柺杖,一路的小碎步,走的飛快。
這些老人的上衣總是深藍色的,也有的是國畫上的灰與白,穿在身上給人感覺冷。上衣與新時代的很不同,捻襟,扣門子是用同樣顏色的布挽出來的。圓立領,一直從右下頜扣到右腋窩以下。
每次看到這些老人,我的眼神都放著光。她們的褲子總是黑色的,因為腿瘦因而顯得寬鬆。小腿與腳踝那一段總用白布裹著,如同現代人發明的小腳褲。
上了年歲的老人,用的是煤油燈,隨時都有油盡燈枯的時候。
沒人相信三更鬼,怪的是,村裡那幾個老人閉眼的時辰總在三更。
等雞把天叫亮了,老人的魂早被小鬼捆著去了天曹地府。
灰白的天空飄著細雨,烏鴉站在院裡的核桃樹上“呱呱呱”的叫著,像是看到了遊魂。
等兒子,兒媳發現時,老人的身子已經變硬了。摸著像塊冰,會粘手。花開一時,人活一世。時差再長,枯萎了,皺巴巴的,醜陋難看,散發著腐爛的氣息。無論是誰沒什麼區別,都一個樣。
生與死像無數個圓,一個在一個裡面,包含著。有前世,有今生,有來世。人們把它叫做輪迴。老人走完了今生,她還有來世。來世的尊榮起初就決定好了,馬虎不得。
絲綢緞面的白色內襯,紅綢子外衣,寬腰帶,小腳鞋,純棉花緞面軟衾。或許,她這一生活得苦不堪言,可走了,總得風風光光。階級不只存在於今生,閻王殿裡更加森嚴。去那邊怎能破衣爛衫,小鬼也是勢利眼。穿著綾羅綢緞,戴上金冠玉釵,口袋裡還得裝滿錢。
穿戴整齊了,入殮前,兒孫們再看她最後一眼。
搭好的靈棚上扎著柏樹葉,月白的,鵝黃的,桃紅的……各色紙花被柏樹葉襯著,格外亮眼。
老人在棺材裡睡著了,眉頭舒展,非常安然。棺材被一張席擋著,席子正中掛著她的黑白照片,照片兩邊貼著白紙黑字輓聯。大方桌緊挨著席子,上面擺滿供品。生前都沒能吃的水果,這時候全在那了。南方的,北方的,小孩瞅著那些水果忍不住嚥著口水。糕點也擺了整整一大桌子,甜的,鹹的,綠茶的,奶油的。我和那些孩子眼巴巴的瞅著,母親一再告誡我不許碰。
請來的號亮(吹手)在篷佈下吹著喇叭,鐃鈸拍出的聲音似乎是圓的,一圈一圈擴散開來,震得人耳朵發麻。敲鑼打鼓的人神情木木的,像是被震天響的聲音給聒傻了。
兩個戴著大頭面具,穿著長袍的人手裡端著托盤,托盤裡放著一塊點心,要麼兩根香蕉,一扭一扭,搖頭晃腦的,用扭秧歌的步調走過來又走過去。為了讓前來弔唁的人看熱鬧,他們總是迎面走來,背道而去。
主持喪事的道人算了時辰,停靈三天才能入土。這三天裡,院裡的人來來去去的從未間斷。大人們面色凝重,內心傷感。只有我們小孩子嬉笑怒罵毫不拘束,老人的親友在辦喪,我們只當熱鬧看。
三天過了,要起靈了。靈棚得拆了,柏樹葉子和紙花得一併帶到墳頭燒掉。我們站在靈棚一側,等著摘紙花。
墳冢較遠,送靈的隊伍很長。人們走的很慢,哭聲和號亮聲混在一起,越過重重樹梢,傳的很遠很遠。
我和那些夥伴拿著討來的紅紙花,尾隨著送靈隊伍。等鞭炮響過了,就亂成一窩蜂搶著拾鞭炮。誰在真哭,誰在假哭,那是大人的事情,與我們無關。
墓口封上了,一生的酸甜苦辣都成了前塵舊事。親戚們走了,村裡人散了。
墳前的紙灰像石灰,嶄新的,可以做染料。插在墓地的香燒了一半滅了,也是新的。黃昏時分,雨停了。晚風吹在身上就像蘆花在撫摸,天空出奇的藍,村子裡瀰漫著一股濃郁的花香。
太陽剛剛落下去,月亮就出來了。
晚飯之後,月光變得明亮了。一團黑影在墳前遊弋,並非有人看花了眼,的確是一團黑影。黑影過上一小會就變個樣子,圓的成了扁的,扁的越拉越長,長的又變成圓形。
有人說,那是老人的魂。她餓了,出來找吃的。
有人說,那是月光的影子。月光的影子,就是老人的魂。
——————————————————————
原創不易,期望讀者關注愛寫文文,閱讀更多文字。謝謝!
【圖片:來源於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