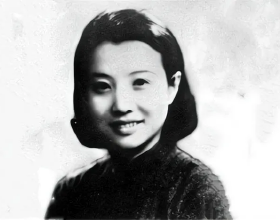清朝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1年2月13日),董福樣被清政府革職。作為抗擊八國聯軍入侵的“禍首”,他是清政府與八國聯軍議和期間爭議時間最長,也是最激烈的一個人物,(廖一中《<袁世凱與辛丑條約>的簽定》,《貴州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
中外勢力在他身上耗費了不少口舌,終究以悲劇而告終。其時正當庚子年(1900)與辛丑年(1901)之交。時序的交替,帶來了他人生的轉折。隨之,他經營數十年的甘軍被分化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消跡,卻孕育了西北馬家軍事集團,個人雖以悲劇收場,但作為歷史人物,已被收進《中國軍事知識辭典》,這也算是他留下的蛛絲馬跡。本文僅就董福樣革職後,即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01-1902)的一段歷史作以述論,這是他一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革職回甘
西太后、光緒帝自北京倉皇出逃,在流亡途中及駐蹕西安之後,為了早日求得列強的饒恕,公開出賣義和團,把一切罪責全部推在義和團和部分主戰的王公大臣身上。在如何處理“禍首”、“罪臣”問題上,迫於帝國主義和“洋務派”的壓力,清政府連續懲治過三次,其程度逐次加深。1901年2月13日第三次懲治,董福祥以“戧使臣、攻使館、殺教士,京中士大夫被其連累者無數”的罪名被革職,甘肅提督之職由四川重慶鎮總兵薑桂題取代,僅留莫太子少保銜。董革職後,旋即離開西安,返回甘肅。
據王伯祥先生的《董福祥史料》載,董福祥因不服革職,且聞同黨毓賢斬於蘭州,有自危之感。因而在返回甘肅途中,在舊屬的慫恿下,“滯留於平涼之崆峒山上,擬以陝、甘、新三省聯盟共抗外敵作號召,圖謀再起。”清廷聞之震驚,“急遣大員往轉致後意。”董福祥是否確有此舉,尚待考查。筆者以為此說欠妥。第一,目前還沒有其它史料能證實董福祥曾滯留崆峒山,第二,據董福祥光緒二十八年冬給榮祿的信札看,無有此事,也看不出有這方面的動機,第三,王先生《史料》所引:“近以國步艱難,時多掣肘,朝廷不得已之苦衷,諒爾自能曲體。現在朕方屈己以應變,爾亦當降志以待時,決不可以暫時屈仰,隳卻初心。他日國運中興,聽鼓鼙而思舊,不朽之功非爾又將屬誰也。”這些言語應是董福樣在西安革職前清政府對他的安慰之詞,並非董福祥滯留崆峒山後才說的。
當然,此時的董福祥確實憤懣填胸。與榮祿相比,覺得委曲太甚,怨氣無處排洩,曾致榮祿長信。“中堂閣下……手書慰問,感愧交併,然私懷無訴,不能不憤及仰天而痛哭也。”董福祥歷數過去的歷史,往事在目,事事直逼榮祿(軍機大臣,掌兵部)。戊戌政變,“中堂(榮祿)欲為非常之舉,電調董福祥入京;圍攻外國使館,“祥以事關重大,疑遲未決,承中堂驅策,故不敢不幸命惟謹。…..又承中堂論謂:‘力攜夷,福同之’。樣是武夫,無所知識,但恃中堂而為犬馬之奔走耳。”寫到這裡,董福祥已不能自己,遂以厲辭質問榮祿,“今中堂巍然執政,而祥被罪,雖愚弩,竊不解其故。福樣與中堂,其力不可謂不盡矣 ……而今獨歸罪於祥”。最後流露了他保留武裝的意圖,“麾下士卒解散,鹹不甘心”,同時亦逼榮祿予以支援,“祥以報國為心,自拼一死,將士鹹怨,祥不能彈壓,惟中堂圖之。”
董福祥此舉,不但發洩了怨氣,而且在實質上起了作用。首先,榮祿閱信,心理不安,良心有愧。“急送五十萬金”,為董部將士略表慰問。以表他的心意。其次,董福樣在一段時間之內,確實在暗中得到了榮祿的保護。如平羅下營子教案發生前後,關於董福祥的謠諑四起,一些清政府大員很不以為然,陝甘總督崧藩數次上折榮祿,給董福祥施加壓力,都想致董福樣於死地。其結果均未能奏效。如果沒有榮祿暗中保護,眾人之口,明槍暗箭,董福祥是防不勝防的。
(一)回駐固原
董福祥由西安返回甘肅,最初是駐在他的故鄉固原城的,其間約一年時間,直到光緒二十八(1902)年春。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陝西固原提督鄧增(字錦亭,廣東新會人,時任陝西提督駐節固原)在河北正定告別了隨扈返京的慈禧與光緒帝,於次年三月抵固原。當鄧增行抵平涼時,董福祥已不願繼續呆在固原,遂退駐距固原城北六十里處的楊老莊(今周原縣楊郎鄉)。究其故,董福祥與鄧增有著雙重關係。鄧增即是董福祥的門生,光緒二十一年,董福樣鎮壓河湟起義時,鄧為其部下。河湟之役結束後,董曾極力舉薦鄧,並蒙董褒獎;同時,鄧增與董交識三十餘年",又是老朋友。或許正由於此,董福祥不願見鄧增,而鄧增又想盡門生和老朋友之情誼。其目的還是想勸說董福祥及早解除武裝,以減少對他的威脅。遂輕騎前往楊老莊相會。據鄧增給榮祿的書札所載,鄧增勸董"冀其省悟”。既已革職,就不必再行帶兵,應退隱偏僻。而“彼(董)不聽逆耳之言”,談及它事,董“似無他心”;問及獲罪情況,“卻有不受”。兩人談話不多,卻反映出了三方面問題:一、不願解除武裝,二、已無心於他事;三、對革職仍憤憤不平。董福祥要帶兵,而且要多帶兵,“以為自衛之計”。對此,鄧增很不以為然,認為董“何其愚也”。兩人很難談得投機。但鄧增只能規勸,而不敢施加任何壓力。鄧增的規勸,其目的是要消除董對他的威脅。當然這裡還有榮祿的意思。鄧增在給榮祿的另一信札中說:“此番到固,定當宣佈中堂德意。”不是很明瞭嗎?
(二)平羅下營子教案與董福祥謠傳
董福祥雖被清政府革職,但清政府並未從此對他置之不問。在一度時期之內,他依舊是中外所關注的人物。早在他革職之前,清政府就告誡中外,董福祥“本應重懲,姑念在甘肅素著勞績,回漢悅服,格外從寬。”正由於“回漢悅服”,所以董福祥回甘以後,他的舉動、言行更容易引起中外的注目。平羅下營子教案發生之前,中外就有關於董福祥的不少謠傳。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1901年5月11日),西安軍機處急電:德國瓦帥聞有董福樣率兵進攻直隸(北京)之說,兼以宣大(山西)境內“土匪”與“教民”為難。經查純系謠傳。四月,法國使者送來譯文,傳寧夏教民男女多人被阿拉善王及圖克王殺死。又傳小橋畔地方已被董福祥佔據。小橋畔、三道河等處教民均有危險。五月初八日(6月23日),赫德(英國人,1901年支援列強脅迫清政府簽定《辛丑條約》,在中國任海關總稅務司達四十八年之久,是英國駐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致倫敦函:據傳董福祥即將帶著大隊人馬回來,三星期前他在內蒙兩部屠殺許多比利時教士,重演仇外行動的事。(《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22頁)此雖均系謠傳,但外人更加關注董福樣的活動。六月七日(7月22日),英國使臣函稱,英上議院參贊詢問端王、董福洋下落,並要求清政府以確信示知。十一月二十八日,又傳言甘肅寧夏府平羅縣“土匪”誅洋夷教民。好事者便將這些傳言附會在董福樣身上。“土匪作亂,安知非被遣王(聞端郡載漪逃入賀蘭)、大臣(聞董大帥福祥聚兵寧夏)籍端起事平?"其實,董福樣此時正在固原。當謠傳正盛其間,清政府於六月初九日(7月25日),“予前甘肅提督董福祥為其父母建訪”,並贊其“遵守命捐,疊助善舉”。
(《請實錄》卷485,第400頁)對董福樣進行安慰。十二月初三日夜,平羅縣民龍佔海、馬躍川等襲攻本縣下營子教堂,殺比籍神甫梅教士及教民男女三人,砍傷荷籍神甫彭壽年。這就是驚動一時的平羅縣下營子教案。在當時,清政府與八國聯軍議和不久,敢與教民為難者,不但清政府要問罪,外國人也自然會施加壓力。平羅教案何人所為?董福樣成了懷疑物件。甚者,有人肯定是董福祥所為。就連當時陝甘總督崧藩在給榮祿的信禮裡也認為,“又云身穿有號衣,定是甘軍。"
下營子教案發生之後,紛紛傳言寧夏、甘肅、平涼等地民變日甚一日,州縣官吏被殺者不少。清政府遂命山西巡撫岑春煊帶兵抵甘,會同陝甘總督崧蕃剿殺。同時,清廷接連電令陝甘總督崧蕃,勒令儘快結案,並要“設法妥辦”。崧蕃為設法訪緝兇手,短期內結案,遂致函董福洋,“囑其於遣散之軍設法訪緝”,想透過董來了結此案。在崧蕃看來,發案即黃福祥部,“於遣散之軍設法緝訪”不過外交辭令而已。董回函崧蕃,“亦稍露機關”。董福祥這一招,反拖住了崧蕃。因為下營子教案緝查的快慢,關係到崧蕃的前程。朝廷降下罪來,崧蕃自知是吃不消的。他決定請董福祥到省城議解此案。同時,崧蕃也向榮祿暗暗流露了對董福樣的起用之意,並以此作為條件。“此事若以‘永遠’二字了結,方對得他(董)過。特未知是否外人又申前議?抑全權預為地步?”@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可能的,崧藩之所以有此想法,除上述原因外,也不是他有憐憫之情,而是耽心董福樣擁兵甘肅,怕有不測之事。崧蕃最慮者,董福樣“部下渾人太多,難免不借端生事。"出於這種心態,才希望董能夠重新起用。
董福祥是否去省城參予了結下營子教案,暫未見詳載。不過崧藩的目的尚未達到。崧蕃見董福祥起用無望,便又想辦法解除董的武裝,以控制董福祥,從根本上排除隱患。
光緒二十八年春,陝甘總督"諸事棘手”,且與陝西巡撫升吉甫、陝西提督鄧增不合,氣悶而告病假。但早在光緒二十七年冬即奏明令陝西補用道王世相(曾為甘軍營務處)接管董的餘部,董福樣仍暗中照料。“餉章報銷一切,有非他人所能代替者,故裁併甘軍及收繳軍裝,均由其妥為料理。而升吉甫、鄧增則不滿,同時又據謠傳“以入告”。董福祥“亦有所聞,頗懷惴懼”。他深知憂讒畏譏,人言可畏。遂遣王世相往省城見陝甘總督崧蕃。崧蕃透過王世相寄語董福祥,"囑其交替三營以免謠諑”,要董福祥解除僅有的三營兵權,以“逍遙田裡”,當“一部民耳”。據崧藩給榮祿的信札,“彼亦以為然。”董福樣表面也同意裁掉所有軍隊。崧蕃想透過軟的一手來達到限制董福祥的目的;董福祥亦深知其用意,也就將計就計,格蕃自然信以為真。
(三)繼續剪除童福樣的實力
在解除董福祥兵柄的問題上,陝甘總督崧蕃用盡惱汁,軟硬兼施,也未能達到目的。他原以為董福祥是會順著他畫的圈來的,“欲俟星五(董福祥字)之事辦理稍有頭緒”,結果是“久不得其(董)回信”。崧蕃“深恐夜長夢多”,其實,根本不是夜長夢多的問題,董福祥早有他的老主意。董福祥回函崧蕃,其信札言辭多有迴護,意在若即若離之間,一反前態。崧蕃給榮祿的信中說:“前函允許甚堅,不為遁詞…亦見其矛盾之大矣”。而崧蕃將董福樣態度的改變又看在了安維峻(1854-1925年,字曉峰,號盤阿道人,甘肅秦安人。1880年進士,官至都察院福建道監察御史。因彈劾李鴻章等的專權誤國而被革職。時人稱隴上鐵漢御使)身上。安維峻因坦蕩無私、不畏權貴而遭貶謫,所以對董福祥的革職深表同情與理解。當時安維峻是否為董福祥出謀劃策,暫未見有史料能予以證實。但陝甘總督崧蕃在給榮祿的信札裡說,“所可惡者,安維峻在彼肆其簧鼓,為之飾非逢惡…而語語為大局計,為甘肅計,實則為身家性命計耳。”由此可見,董福樣與安維峻的關係是密切的。崧藩說董福祥拒兵不解,是“為身家性命計”,也確是事實。
董福樣革職回甘,在當時一些清政府大員的眼裡,不免有縱虎歸山之憂,總是在時刻留神設法消除後患。陝甘總督崧蕃在逼董福祥交出僅有兵權的過程中,董開始用軟的辦法拖,答應在光緒二十八“秋以為期”。而在崧蕃看來倒成為“緩兵之計”,未免小題大作。“身家性命計”有情有理,為“緩兵之計”就屬無稽之談了。作為崧蕃,煞費苦心。一方面想急於使董歸耕田間,一方面又不敢對董在言辭與行動上有任何過頭的表示,仍怕“激成變”。在給上方的報告中,也只能是“惟有鎮靜,急脈緩爰”。
當對董福祥無可奈何時,陝甘總督崧蕃又從董福祥的部下開刀,試圖以調離分散的方式來達到分化的目的。首先在馬福壽(馬千齡之子)身上打注意。河湟事平後,其見馬福祿隨董福祥開赴京畿,其弟馬福祥亦隨軍前往,獨留馬福壽暫留鄉經營田產。董福樣回甘後,與馬福壽往來頻繁。時其弟馬福祥因隨董護駕有功,深得慈禧的信任,而馬福壽在地方上亦很得勢。崧蕃為切斷馬、董之間的往來關係,一方面透過馬福壽“囑星五散營”,一方面又與馬福壽以“委缺”,“令其到任”。雙管齊下,以表示他將剪除董福祥“羽翼之意”。但馬福壽“藉詞推諉”,也不願往省城聽職。這樣一來,崧蕃越發覺得董福祥樹大根深,難以駕御。同時認為在董福祥周圍“鼓惑者”,不獨安維峻一人。據崧蕃給榮祿信札裡稱,“此人毫無知識,素仗董勢,其居心惟恐無事,固較安為尤甚”。比安維峻還勝一籌,也沒有史料能說明是誰。但有一點說明,儘管董福祥革職待罪,一時要分化他,確也不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