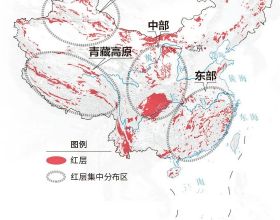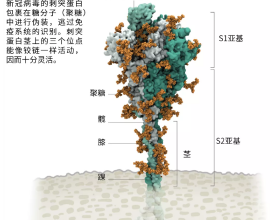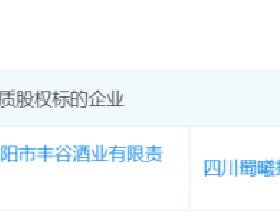歷史灰塵注:前面我更新完了曾昭掄博士的《滇康旅行記》,下面我們一起去看看大涼山的人文與風光。1941年7月1日,跟隨民國曾昭掄博士和他的“川康科學考察團”出發,看民國時的大涼山人文與風光。本文摘自曾昭掄博士《大涼山夷區考察記》。
如果你喜歡有趣的、不常見的歷史資料,請關注我,我會每天堅持發掘出那些快要淹沒在時間煙塵中的歷史文章。如果你喜歡本文,請點贊、評論、轉發。
夷人在西昌
西昌逼近夷區,向來夷人在北城來往趕街者,為數甚多。抗戰以來,此城逐漸走上近代化都市的途徑。外省人士,大批湧入。裝束摩登的到處皆是。但是漢夷交錯這種舊日特點,迄今猶存,這也就是西昌街頭景饒有興趣的一點。摩登人物中間,常會看見仍作原始裝束,赤腳披氈的高大倮夷男女。有時候最摩登的飯館前面,圍成一圈,蹲著一堆夷人。當他們彼此間以夷話談笑的時候,一群摩登女郎走過,也許會指著他們大笑,
白天在街上,夷人不敢放肆,對此無可如何。要是在山裡,情形就要反過來了。
師範前面的小廣場上,每天可以看見大批夷人,在此趕街。在這裡擠滿是人的地方,他們來回地徘徊,買賣東西,喝喝酒,看看他們認為稀奇的物品,自得其樂。同時漢人對於他們,雖說見慣了,好奇心卻始終沒有消滅。他們那種魁梧的身材,粗黑的面孔,奇異的服裝,永遠是一種好奇心的物件。
和漢人比起來,夷人長得高大得多,尤以女子為甚。男子的身材,倒不一定比我們中間的北方人高。然而我們站在他們旁邊總顯得瘦小,因為他們胸部很寬的緣故。夷人衣服的顏色,彷彿是以黑為貴。無論男女,外面都披上一件黑色羊毛的披氈或“擦耳窩”,底下一律赤腳。頭上大半用藍布纏頭(這種習慣,也許是從漢人學去的)。耳朵上面,大都戴有耳墜。男子只在左耳上戴此物,女子兩耳均有。男子戴的,不是一顆大的黃色蜜蠟珠,便是一短節銀鏈。女子的耳飾,珊瑚珠、玉器、銅環、銀錢、銀環、等等均有,往往以幾種不同的東西,綴成一串戴上。婦女所著衣服,外面一律是黑色披氈或“擦耳窩”,裡面則貧富之間,頗有區別。窮人穿的不過是布衫黑裙(裙子用粗的黑呢裁成,形式為一種百褶裙,頗有點像西洋中古時代女子所著裙的模樣,大都長得拖到地上)。闊人裡面,有些極力模仿清末漢族貴婦的裝束,上面寬袖大襟衣(衣袖及衣襟上各滾有一道或幾道繡花邊)。下面繡花裙子,有時甚至衣裙的顏色是觸目的粉紅色。
不過無論穿得如何漂亮,終年難洗一次澡的倮夷男女,總是顯得很髒。他們疲倦或是喝醉了,隨時隨地,倒在街上,便呼呼地睡去。提起酒來,他們最高興不過,西昌街上,常常會看見倮夷男女,抱著一罈酒,大杯倒出狂飲一番,西門外汽車站附近,有一片大草坪。迄今夷人仍然常在那裡跑馬,據說每年有幾次比賽。
為防夷人滋事起見,以前西昌等逼近夷區的各縣縣城,夜間向來不許夷人住在城裡。一到天黑,假如有逗留在後面的,不管他們是否情願,一齊要轟出去。近來西昌城內,軍委會辦有邊民訓練所。該所學員(本地人都叫他們“屯委會的蠻兵”),住在會中所備宿舍,總算破了慣例。受訓以後,當然變得文明些。但是新徵來的,許多仍然野心未改。我們到西昌的第二天,就聽見夜間其中一位,挖洞走進一家布店,搶去一些紗布,並將店主劈死。夷人慾望很簡單,所要東西不多。不過棉布對他們是一種必需品,所以布店和染店,最有被光顧的可能。
西昌城內,至今還有一座“夷卡”(現已改名為“西康省寧屬屯墾委員會夷務管理處”)。這種中前清時代留下來的制度,似乎有點過時了。清代夷卡的目的,主要是拘留各支夷人送來的人質,以免他們造反。附帶地還用來禁押拿獲的叛夷。現在總算文明些。在西昌將人質辦法取消;所謂夷卡,完全變成一種專關夷犯的監獄。來此後我們特去參觀法庭。當時被拘的,一共只有十人,八男二女。
據說以前要多得多。近來都先後開釋了。現拘十人當中,九個是黑夷。只有一名是娃子。這位樣子最滑稽,頭上還戴著一頂舊軍帽。中間還有兩位小孩,乃是以前西會道上有名巨匪劉呷呷的子女蔡麼老虎(亦系西會道上有名的夷匪首領蔡三老虎的兄弟)的女兒。不久以前,還在此處。新近因蔡已投誠,所以放走了。
二十八年屯委會接受卡後,本擬大加改良。對於犯人,在卡內任其自由。每天讓他們上四點鐘的功課(黨義等);其餘的時候,指定做一些勞作。這種辦法,未始不好。只因夷匪類多兇悍異常,不易管束。近來經費縮減,本卡衛兵由十人減至六人,尤屬無從防範。某日清晨四時,犯人四名,挖牆而逃。嗣後遂改變辦法,除女犯及小孩,任聽其自由而外,男犯一律恢復手銬腳鐐的舊時待遇,課則根本不上。如此暫時誠可無事。但恐放出以後,他們對漢人的仇恨,更將深刻。最幽默的,是卡中牆上,還有以前所貼標語,如“漢人是哥哥,倮倮是弟弟”等話。
夷人喜歡行劫,誠然不好。但是一般無知識的漢人,恃勢凌人,也是常有的事。比方有一次我們上館子去吃飯,正碰見一位夷人,走進來買包子。他的漢話說得不大好,一進來問包子多少錢一個。原來定價是兩毛錢一個,堂倌卻對他說四角。後來又說四角錢買一個送一個,明明是存心嘲弄他。過去漢、夷兩族間的猜疑與仇恨,許多是從語言不通以及不能以忠恕之道待人而起,現在仍然是這樣。
寧屬夷務問題
寧屬兩大問題,就是夷務與禁菸;而這兩種問題,彼此間又有關聯性,此點在前文中已經提及。漢人說,寧屬煙苗之所以未能根絕,是因為夷區裡面,黑夷包庇種煙,漢官勢力一時不能達到,所以沒有辦法。這話固有相當理由,但非全部事實。漢人聚居的地域,比較僻靜地段迄今多少不免仍有煙土。同時兇悍夷人,不服政府法令,視種煙為發財要道者,誠然不少;明白事理者,亦復有之。若干黑夷,現在業已覺悟,種煙對他們也沒有多少好處;因為種煙的結果,使娃子(奴隸階級)財富日增,在經濟上大有奪取黑夷(統治階級)地位的危險。
走過涼山夷區以後,後來一位熟識的黑夷告訴我們說,他們本來不喜歡種煙;不過因為漢人需要此物,常常來買,所以就種起來。只要漢人不買,夷區禁絕,不成問題。最壞的是許多官方的人,也來收買。如果官方把握得住,他們還願意合作,將進去買菸的漢人,一律綁起來當娃子。
寧屬八縣,究竟一共有多少夷人,迄今還是種值得研究的問題。據今所知,此區所謂夷人,絕大部分全是倮夷(倮)。他們和雲南境內的倮,頗有區別;因為在他們當中,顯然有黑夷和娃子兩個階級(這種制度,除滇北一小部分地區而外,在雲南倮族當中,似乎是不存在的)。據屯委會估計,寧屬漢人,一共不過八十餘萬,夷人則有百多萬,超出漢人總數,川康建設期成會,亦謂涼山區域,共有夷人二百萬,內寧屬佔八十餘萬。
鄧秀廷司令當面相告,說是川省雷馬蛾屏區以及寧屬昭覺、冕寧、西昌、會理、寧南、越西六縣(此即包括擴大的涼山區全部範圍),現共有夷人五十萬戶,漢人二十五萬戶;而且夷人一戶,連娃子約有八九人,漢人一戶則不過三四人。此等數目,皆嫌過於誇大。研究涼山夷區的專家常隆慶先生,對此問題,曾有較為科學的研究。常君在其親身走過的地區,將所見房舍數目計下,由之推算,認為昭覺、雷波、馬邊、峨邊(後三縣迄今仍屬四川省管,惟昭覺則屬西康,為寧屬八縣之一)四縣,由彼調查部分一共黑夷不過一萬,娃子不過四萬。然彼所調查的地方,已佔涼山區域的大半。剩下的小半區域,即令亦有同樣多的人口;涼山全區的夷人總數,亦不能超過十萬,又謂會理東區夷人甚少,大部分乃是漢人世界,與普通人所信者不同。
寧屬境內,據彼所知,夷人所佔地區,面積實在漢人所佔者之下;平常掛在一般談夷務者嘴上的所謂“一線相通”,實與事實不符。況且漢人所佔,大部分為肥沃的河谷;而夷人居住之處,則主要地不過是些高山地帶。所以夷人總數,決無超過漢人之理。如此看來,寧屬八縣夷人總數恐怕一共也不過十萬左右。後來我們走到雷波,一位熟悉漢情的夷人李仕安先生對我們說,據他估計,寧屬西昌、昭覺兩縣,約有夷人三十萬。川省雷馬峨屏(雷波、馬邊、峨邊、屏山)四縣,每縣兩三萬至四五萬不等(中以雷波為最多),總計不過十萬上下,分作六十支黑夷。他本人曾在涼山旅行多次。一共前後所遇黑夷,總數尚不到三百人。平心而論,常、李兩先生所作估計,比較可靠。這就是說,一般所傳說的未免太高。
過高估計的一種結果,就是這種錯誤的估計,影響到公路工程的進行。比方此次修築樂西公路,徵用本地民工,當初以為夷人如此之多,不難徵到幾萬。結果發現,連鄧秀廷所轄夷兵湊在一起,一共還到不了一萬。最後實際工作的五萬民工當中,夷人不過佔去兩千。至於過去傳說之何以會如此誇大,頗有幾種理由。一因夷人兇悍善戰,而且行動敏捷;每當襲擊漢人,常會自遠處蜂聚而來。一般平民無知受害之餘,既缺精確統計,遂誤以為夷人多得了不得。二因若干地區(例如會理東區),土豪勢力甚張。因恐他人侵入尤懼政府取締。乃故意揚言該處為夷區,以資抵制。最後在地方上掌軍政權者,難免不挾夷(或者甚至養夷)以自重。清末以來寧屬地方,凡對夷務有辦法者勢力即不可侮。文人武人靠夷務吃飯者,為數不少。因此對於夷區情形,愈加渲染失實;而政治軍事上的明爭暗鬥,亦往往由此而生。
清代對於涼山倮夷,素採羈縻安撫政策,設立夷官,予以包山保路的權利,並以作質當差等辦法將其拉住7.同時在夷區四周到處屯兵。以資防堵。數百年來,多數時候,尚能相安無事。然而夷人竄出為害,仍然常見。邊地武官,以剿夷立功者,不乏其人。如瀘山劉公祠所祀之劉延珍,即是一例。
清末民初,夷防漸弛。民國八年,涼山夷人,傾巢而出。夷區大為擴張;雷波、峨邊、西昌各縣城,均瀕於危。涼山漢人數萬戶,非殺即逃。剩下極少數(一共不過幾十家),亦不得不求黑夷保護,地位幾淪於娃子。此時幸有鄧秀廷出,在西會道上及冕寧縣境,剿御夷匪,極為得力。西昌及其南北交通線,幸得儲存。本地漢人,對之感激不盡。鄧氏不但勇敢善戰,且在駐營地區,不對漢人抽稅;專賴抽夷人的稅,及沒收叛夷產業,以維持軍費。因此漢人對之,更加愛戴。但一部分夷人,則恨之刺骨。鄧氏除依賴武力外,並極力運用分化夷人的策略,以求獲得成功。其所採方略,一方面挑起娃子對黑夷革命,另一方面則設法使黑夷中間自己衝突。此種辦法,收效不少。
屯委會成立後,對鄧氏純粹採“剿”的辦法,不以為然,主張以招撫感化為主要策略。其所提口號有:(一)“不收見面禮”,(二)“不取投誠費”,(三)“不準打冤家”,(四)“不輕用武力”,(五)“漢倮平等”,(六)“黑白(指黑夷及白夷)平等”。所採方案,除對叛夷仍不免一剿外,盡力鼓勵投誠;並在夷民漸已就範的區域內,設定政治指導區,同時在西昌設立邊民訓練所。就中最後一事,為一種值得特別提及的新政。該處於廿八年十二月起開辦。其目的及辦法,為調訓各支黑夷頭目及其子弟,以及一部分娃子,予以短期訓練,教以漢語及黨義等。每期訓練一兩月。至三十年夏季已共有五期學員畢業。此種方法,不失為一種治本辦法。開辦以來,已稍有成績可言。
整個地說,屯委會處理夷務,疵瑕並見。近來黑夷投誠者不少,降而復叛者亦復有之。為防夷人叛變起見,該會在重要地點,設有夷務指揮部,由二十四軍派兵駐紮,以資震懾。目下由西昌到昭覺的路,政府勢力,已能再度控制。在不久的將來,該會擬將漢人幾百家,移民進去。同時設法將沿途交通經濟大權,拿在手裡。此外現歸屯委會支配的兵士,在樂西公路上作養路工作者,計有一千人,將來工作完竣以後,擬將其調到昭覺屯墾,並鼓勵其與白夷通婚;如此把握著白夷,黑夷即不成問題。這件事並不難辦;據說現在昭覺的駐軍,業已有一些和白夷女子發生戀愛了。
鄧秀廷在名義上也是隸屬二十四軍。不過久當一面,自然不肯甘居人下。同時因對夷務問題,與屯委會意見差池,有時不免摩擦。他部下所轄夷兵,與屯委會的學員成為一種對峙的局面,甚至發生過武裝衝突。機關的重複,事權的不統一,不免是處理寧屬夷務問題的一大障礙。倮夷因缺乏教育,貪詐狡黠成性,目以偷竊搶劫為榮。漢人對之,不懷好感。一直到現在,“夷性犬羊”,“夷人畏威不懷德”,這類口頭禪,常掛在談夷務者的嘴邊。許多去過涼山的朋友們,也以為黑夷非剿不可。實則許多問題,出於誤會。要是好好的由教育方面入手,未始是一件沒有辦法對付的事情。
鄧司令的會見
久仰鄧秀廷的大名,到了西昌不久,恰巧他也來了,經過一位朋友介紹,我們特地去拜訪這位歷史上的人物。鄧先生是冕寧縣靖遠營的人,有人說他有夷人的血。無論如何,他對黑夷是痛恨的。擔任剿夷工作一事,他已有二十年的歷史。十八歲就從軍,任四川省第二路漢軍前伍營第四營營長。後以家鄉夷匪猖獗,請假回籍,任“總團”,從事防剿。後來任川邊陸軍第三混成旅第二團團長兼寧屬夷務指揮。二十二年,升任二十四軍步兵第二十旅旅長,後又加靖邊司令銜。平常多半長住在他的故鄉(冕寧縣瀘沽附近的甘相營地方)。近來因與屯委會不和,越發不大上城來。這次來完全是湊巧,因為莫柳忱先生正在努力調解他和屯委會間的意見,特別把他拉來了。
鄧司令在西昌住的,是一座大公館。因為他和屯委會弄得不好,住宅附近,戒備甚嚴。他的部下,一部分是夷兵。他們仍作夷人裝束;不過每人胸前,掛上一個“鄧”字的大塊布條。據說他最多疑。約好以後,我們便馬上趕到他那裡去。他所住的公館,是一幢很大的舊式房子。從裡到外,佈置有好幾層崗位。站崗兵士,一部分穿的是全套漢式軍裝;客人來了,一齊敬禮。副官將我們引到最裡面一間長房裡,鄧氏著軍裝出見。
鄧司令的印象,和我們當初所期望的不同。雖則兩目奕奕有神,並不怎樣威武。他的面貌很清癯,身材相當高,看樣子似乎煙癮不輕。見了我們,便拿茶和瓜子相款待。據他自己說,本人現年五十二歲,手下共有三團兵,其中一團是“蠻兵”(由夷人組織而成的部隊),兩團漢兵,每團計有一千二百人。關於治夷方案,他說,夷人當中,十分之九是白夷(娃子),十分之一為黑夷。黑夷最不可信。一支黑夷只有二三十家的,有時依附漢人;像他的“蠻兵”當中,便有此等事例。凡是有幾百家人,一兩千家娃子者,則均不服漢人,非剿不可。黑白比例,既系如此懸殊;聯白夷以制黑夷,實屬輕而易舉。他向來主張領導白夷革命,剿平黑夷,或令其“歸漢”。本來這件事並不難做,可惜屯委會人不如此想。事權不統一,他以為是目前治夷所遭遇最大的困難。
歷史灰塵注:鄧秀廷,漢族,原名鄧文富,彝名“木呷克底”,涼山彝族一般稱其為“漢呷丁家惹”或“丁家阿呷”。國民黨軍中將,在動盪的民國時期,鄧秀廷鐵血掃蕩大涼山奴隸主,推行保甲制度,鄧採取的策略是“打黑護白”: 黑彝,是奴隸主,必須無情打擊。鄧的口頭禪:“與其敬蠻一尺,不如打蠻一丈”;白彝,是平民和奴隸,必須寬待和團結。因此,鄧的部隊有很多白彝士兵。同時,鄧在部分地區透過武力瓦解奴隸制度,推行保甲制度(民國時期基層戶籍管理辦法)。設“四十八甲”,共管轄彝民三萬多戶。在“四十八甲”境內,鄧規定不準搶劫、不準綁架人口、不準打冤家、不準抽人頭稅、服從徵調、開辦邊民小學等,社會秩序比較安定,曾一度為彝漢人民稱道。
1939年初,國民黨中央在西昌設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昌行轅。”5月,劉文輝到西昌,針鋒相對,在西昌設立“西康省寧屬屯墾委員會”,不讓大權旁落。行轅主任張篤倫要鄧先修樂西公路,說這是抗戰大事,劉文輝要鄧先打西會道上宿行搶劫的大奴隸主“蔡三老虎(彝名阿俄長髮)”,說這是社會治安問題。鄧堅持應先修公路為抗戰大局服務使國際援助物資能夠運抵重慶,劉文輝大為不滿。1940年春,劉文輝以軍長、省主席名義命令,以靖邊部為主力,向會理岔河蔡家住地進攻。屯委會秘書長杜履謙即去雅安向劉建議,以增援為名,派24軍斷鄧歸路,迫其無路可走,逃向雲南。劉默許。杜回昌後,即與寧屬保安司令唐福珠、24軍411旅駐昌團長張青巖、寧屬行營上校副官長張懷猷密商,將部隊擺到德昌一帶,堵住鄧的歸路。一面放出風去,使蔡家有所準備。鄧受令,調集彝漢兵三千多人,於端午節前先到錦川,後又推進至蔡家住地前沿——岔河。7月10日晨,兵分兩路,直取豬圈門和倒懸樑子。三天以後,正面發起攻擊,以煙火為號,槍炮齊發,前後夾攻,值冰雹驟降,鄧兵突然出現在洞前,只抓得一個煙鬼師爺和幾個彝人,“三老虎”早已遁去。部隊跟蹤至黑坪子,戰火激烈時,蔡家又派人在山頭喊話,請允許投誠,當攻擊緩了下來,“蔡三老虎”和“么老虎”又跑了。鄧自知上當,臉色陰沉,一言不發。事有湊巧,就在這時,營長鄧天朗來報,說煙館裡有個姓陳的漢人,自稱和蔡金萬、蔡銀萬很熟,可以勸他倆來投誠。鄧立刻將姓陳的請到司令部,盛情款待,給予重賞,發給一面“靖邊部投誠旗”,派營長羅拉哈陪陳去勸降。數日後,果然蔡金萬舉起白旗到來,鄧委為營長,叫去勸蔡銀萬也來投誠。又過了幾天,蔡氏兄弟一齊到岔河司令部來,鄧令軟禁起來,不數日,將兩人就地槍殺。兵士縱火燒房,任意擄掠,將俘捉彝民,部分由帶兵官就地出賣,部分帶回甘相營強派黑彝購買,部分安插在“四十八甲”境內,由其統治。進兵蔡三老虎住地一事,西昌《建寧報》(1940年)九月三十報導:“二十四軍靖邊司令鄧文富氏,此次奉命進剿為害兩會大道之逆夷蔡三老虎,自進兵以來,迄今三月有餘.先後攻破蔡匪老巢,擊殺附逆為惡之匪眾,槍斃助紂為虐之羽翼,蕩平不服政令之夷支,使殘匪心驚膽懾……鄧氏近以返建(西昌)向上峰述職,併兼顧督修樂西公路……已於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到建城,全市各界機關、法團、士紳、學校、部隊,均整隊前往外西郊迎……民眾沿途燃放鞭炮,夾道歡迎,盛況空前……鄧部凱旋時,沿途各地均送有德政旗十餘面。”
1944年7月19日鄧秀廷病死於甘相營,時年56歲。國民黨元首蔣中正及黨政軍首腦張群、黃炎培、莫德惠、鄧錫侯、劉文輝、張篤倫、李萬華等均送有輓聯或墓碑題詞,由書法家陳佐周恭錄刻石鑲嵌鄧墓(按:實為衣官冢,鄧氏真塋不樹不封,外人莫能覓其蹤),墓形莊嚴宏大。鄧墓正中石柱上刻蔣中正拜題:鞏固若長城方欣澤被邛瀘佈德揚威名;飄零悲大樹緬懷功隆輔弼眾生慰龠功。墓額由黃炎培敬題:大漢長城。
總之,鄧秀廷是一個複雜的軍閥。對其評價者,有黑有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