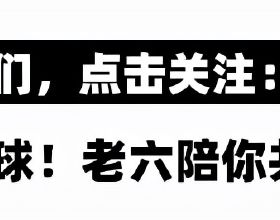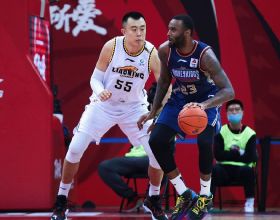上了小學,雖然我不是十分的用功,但成績一直非常好,在班裡一直是第一。但是,也是特別愛鬧騰的主兒,經常找事,父親就經常被找到學校去。
在村裡,我是一個出了名的“壞事大王”。左鄰右舍,只要孩子間出了點什麼事,或者瓜田菜園裡少了什麼東西,犯科的孩子中,一定有我在,而且大多情況下,都是由我指揮著大家乾的。誰家孩子捱了打,他的母親就會拉著孩子,罵到我家來。我母親不比父親,性子特別爆,被人家罵上門來,自然要找我算賬,我自然也就少不了要挨一頓打,所以,常常我在外邊組織小夥伴揍人家一頓時候,回家我母親就要揍我一頓。但是,當我要組織別人揍某一個與我為敵的小夥伴的時候,我就一點都想不起母親揍我的情景了。所以,小學階段,我基本上就是在我揍了別家小夥伴後,回家再挨母親揍的反覆中,成長壯大的。
乾的壞事不僅是揍別家的孩子,還經常組織小夥伴偷別人家的桃啊、瓜啊什麼的,只要誰家房前屋後、菜園的地裡,有什麼東西成熟了,且可生吃,那一定會成為我們獵取的物件,一般情況下,只要成為我們的目標,我們都會得手,他們看是看不住的。我總能想出辦法來讓他們看不住。
只要別人家一種什麼東西不見了,在不知道是誰弄走了的情況下,他們第一懷疑的就是與我有關。所以他們就會到我們家的旁邊不指名道姓地罵大街,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我母親聽得出來就是在罵我:有人生沒人養、挨千刀的、早晚遭雷劈、不是吃槍子也要蹲監獄……要多難聽,有多難聽。母親被罵得滿肚子的氣,但無法發洩,因為別人沒有指名道姓,不能跟人家對罵,只有找我撒氣,狠狠地揍我一頓。我捱揍也不虧,因為那十之八九都是我乾的,當然不一定是我親自幹的。一般情況下,我不會親自幹,我會組織指揮我手下的小夥伴們幹。
上小學五年級,快要畢業的時候,有一次,我把事情給鬧大很了。一個鄰村的同學,在老師面前告我的狀,讓我在老師的辦公室裡罰站一節課。我氣壞了,他居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我決定要報仇,要修理他。中午放學的路上,我發動我的小夥伴,飯後上學來的時候,每人拿一根木棍,然後埋伏他上學必經的路口的麥田裡,當他走到路口的時候,我一聲令下,六七個小夥伴一躍而上,六七根木棍同時落在了他身上,他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被我們給打懵了。當他在地上哭爹喊孃的時候,我們揚長而去。
沒想到,其中一個小夥伴,也不知道是誰,沒有留住手,木棍打在了他的鼻樑骨上,鼻樑骨給震裂了。老師知道後,全部的後果自然就找到了我的身上。停了我的課,還要家長包人家的醫療費。我也被嚇懵了,不知道該怎麼辦。
母親更是氣壞了,指著我,對父親說:“把他丟了吧,咱不要他了。惹不完的事,你說說,咱家哪天消停過,可都是他惹的事?還死懶,人家的孩子地裡的活幹得有模有樣的,他呢?趕都趕不到地裡去,啥活也不幹。你說,他可是個禍害精?留著他早晚會鬧出大事來。”
父親說:“別這樣說他。別光看他鬧騰、惹事的一面,哪個小男孩在這樣的年齡不鬧騰、不惹事?只是三兒鬧得比別人家的孩子厲害點罷了。要看到他上學的成績別人比不了的一面。人家不都說嗎?‘有力的吃力,有智的吃智。’人家的孩子會幹活,咱家三兒會上學。說不定,將來就咱家的三兒有出息呢?你彆氣了。我去借錢,把人家的醫療費送過去,再去學校給老師賠個不是,還得讓他去上學。”
轉身對我說:“三兒,不能再鬧騰了,再鬧騰,就真把自己給鬧騰毀了。”我狠狠地點了點頭。
從此,我消停了,再也沒幹過壞事。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集中到了上學上,順利地考上了初中,考上了高中,直至考上大學。同村與我年齡相仿的二十多人人中,我是唯一,父親的預言沒有落空。
“‘力與智’理論”裡的教育要義
看待孩子一定要一分為二,父母眼中的好孩子,身上不一定沒有不足,父母眼中的“壞孩子”,身上不一定沒有優點。當家長的,當老師的一定要善於發現孩子的“另一面”,發現之後,找到恰當的時機,用恰當的方式,告訴孩子,讓孩子也知道他的“另一面”。這,對於孩子來說,無論他是好孩子,還是壞孩子,都是非常重要的。
父親的那句“有力的吃力,有智的吃智”的話,之所以直到今天我還記得,就是因為我惹了大禍後,自己都感到自己是一個一無是處的人的時候,父親指出的我的優點,給了我無比的自信,我憑著這點自信,憑著一定不再讓父親失望的想法,後來才在學業上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