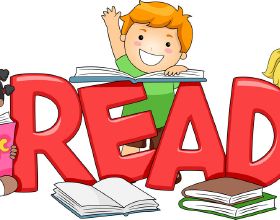當白天最後一絲光亮變成黑夜的流星時,重刑犯區域屋頂上那兩盞昏黃的大探照燈,就準時亮了起來,它們灑下來的光,幾乎能照亮所有的鐵籠子,但卻照不到每個鐵籠子靠牆的那一面。
每個鐵籠子都有三分之一的陰暗面,似乎是專門為女犯人們留了一個黑暗的地方睡覺。有的女犯人會緊貼著牆壁而睡,猛地一看,她那個籠子彷彿是空的,再仔細一看,便能發現蜷在黑暗裡的軀體。
有的女犯人則非要靠在燈光強的明亮處,整個身體都倚在鐵管子上,睡得極其安祥。大多數女犯人則不管是有燈光還是有陰影,身體一半在燈光裡,一半在陰影裡。
鐵籠子裡的女犯人們睡姿各異、鼾聲四起,看得見頭的看不見腳,看得見腳的看不見頭,看得見胳膊的看不見腿,看得見腿的看不見胳膊。
十幾年後,火爆全球的美國大片《加勒比海盜》裡那些一半人身、一半骷髏的海盜們,也比不上這重刑犯區域夜間活體們的場景。
每天晚上如同我這樣保持清醒狀態的女犯人,遠遠不止我一個,有我、有管心、有李鳳平和另外兩個我叫不出名字的老犯人,我們五個人可以說是重刑犯區域鐵籠子裡的貓頭鷹,安靜地待在黑暗處,觀察著黑夜裡的一切動靜。
長年的夜間偷摸習慣,讓我保持了夜間的清醒和敏銳,幾乎每天的子時到卯時,我都是睜著那又大又亮烏黑烏黑的眼睛,洞查著整個重刑犯區域的動靜。
只要李鳳平的手銬腳鐐有輕微的響聲,我便會走出籠子的陰影處,站在有昏暗光線的明亮處,讓李鳳平幾乎找不到夜間對我下手的機會,也讓自己見證了夜間詭異的事情。
鐵籠子外面一般會有五個穿黃馬甲的值班女犯人,警察們是讓她們保持絕對清醒狀態的,但據我觀察,她們五個人都會有打瞌睡的情況,但誰也不說破。
五人鐵籠子裡的女犯人,和五個鐵籠子外面的女犯人,一起過著黑白顛倒的日子,我們這十個人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卻又似乎是在暗中較量著什麼。
重刑犯區域裡關著的女犯人們,幾乎都不怎麼交流,可慢慢的大家還是能摸清每個鐵籠子的故事,和每個鐵籠子曾關過的某人的故事。
某一天上廁所的時間,我發現廁所旁邊的那個鐵籠子空著,一開始也沒想多,以為是沒有那麼多需要關押的人,所以空著。
後來一連幾天上廁所,發現那裡一直空著,仔細觀察後,發現那地上有一層厚厚的灰塵,看樣子許久沒有人“住”過了。
我曾試圖問管心,管心只是瑟瑟發抖不理我,我已經認為管心得了失心瘋,可當我不經意間對上她那雙眼睛時,我又覺得她只是在刻意地躲著我,我很想知道管心到底遭遇了什麼。
儘管這裡空氣混濁、氣氛壓抑,但那些可憐的女警察們還是每天白天和晚上都來巡查,負責任一點的女警察,一天巡查兩三次,不太負責任的女警察,也至少白天一次晚上一次巡查,其餘的時間,都是那四五個穿黃馬甲的女犯人看管著我們。
我的“神偷”技術在這裡幫不上我任何忙,無數個夜深人靜的時候,藉著屋頂上那兩盞昏黃的探照燈,我想鑽出牢籠都沒有成功,我的身體還沒有瘦弱到可以從兩根鐵柱間擠出去,我也沒有學會開鎖的技能,只能苦苦地煎熬,力求不惹事,好好表現,等待政府將我調出去。
一個我睡醒後的下午,來給我們分發饅頭的黃馬甲換人了,我看看管心,管心也在看那個陌生的黃馬甲,她的眼神充滿了驚恐。我看看另外兩個抬饅頭的黃馬甲,她們的臉上看不出任何的異樣。
我們不知道之前的那個黃馬甲怎麼了、去哪兒了,我接饅頭的手有些發抖,那個新來的黃馬甲很不耐煩地大聲訓斥了我一句,我退回到陰暗的牆角,默默地吞著我的饅頭。
一般我吃過饅頭後會接著再睡,直到四周有了均勻的呼吸聲,我才會徹底清醒過來。可那天晚上,我吃了饅頭後卻久久不能入睡,我總在回憶那個給我分發饅頭的新面孔、加上管心看到她時那驚恐的眼神。
我站了起來,走進光亮的區域,整個面部緊貼在鐵柱子上,用又大又亮烏黑烏黑的眼睛搜尋著那個陌生的新面孔。我看到那個新來的黃馬甲極其負責地巡查每個鐵籠子,不時還會發出低沉、嚴厲的聲音“睡覺,快睡覺!”
她每巡查一圈後,或在她的椅子上坐著休息一會,或跟其他的黃馬甲低低地交談幾句,然後又開始她的巡查,一點都不像其它四個黃馬甲那樣,聽到聲音或者有人報告才懶懶地起身。
不知過了多久,另外四個黃馬夾都歪在椅子上睡著了,唯有那個新來的還是認真負責地、一次又一次地、從我們的鐵籠子外面走過,我的眼睛便一直盯著她。
小吏原創小說,版權所有,違者必究。小說內容為藝術加工,若有雷同,純屬巧合。